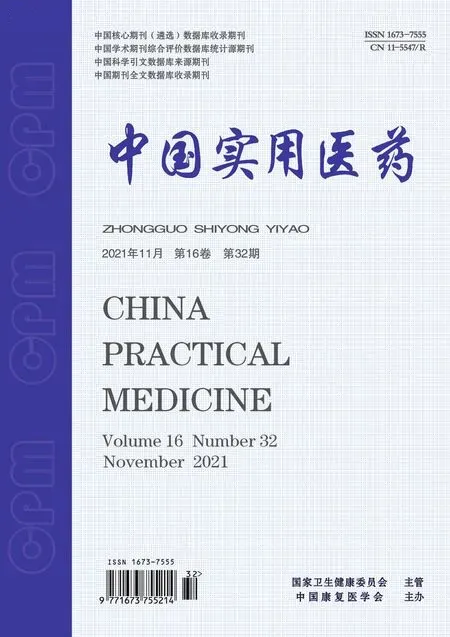早發急性冠脈綜合征的研究進展
董瀟玲 潘甜 彭學軍
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一組急性心肌缺血臨床綜合征,包含急性非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不穩定型心絞痛(UA)和一部分心源性猝死[1]。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劃成人治療組第三次會議(NECP-ATPⅢ)[2]制定的早發冠心病(premature coronary herat disease,PCHD)定義:男性患者初發CHD年齡<55 歲、女性患者初發CHD 年齡<65 歲。早發急性冠脈綜合征(prematur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PACS)占PCHD 住院患者的大部分,該年齡段人群基數大,是社會發展的中間力量,因此早期的識別與干預具有重大意義。
1 流行病學特點
據最新數據統計,我國心血管疾病患者達3.3 億,其中CHD 患者已>1100 萬,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呈現出年輕化趨勢,相關危險因素控制情況并不樂觀[3]。同一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發病率、死亡率不同,近年來農村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率持續高于城市,在我國蒙古族、藏族患病率較同地區漢族高,貴州苗族明顯低于同地區漢族。2021 年美國心臟協會(AHA)發布的最新版心臟及卒中數據文件CHD 的全球疾病負擔呈上升趨勢,已成為全球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美國、芬蘭等CHD 發病率高,日本、希臘為低發國,中青年人群CHD 發病率逐年增加[4]。
2 病理生理學機制
ACS 的病理生理機制比較復雜,傳統觀點認為動脈粥樣硬化易損斑塊破裂是ACS 發生發展的最重要始動因素。破裂斑塊通常表面具有較大的脂質核心,纖維帽薄,覆蓋少量的平滑肌細胞和基質,且有豐富的T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的浸潤,炎癥反應可導致斑塊表面分泌大量蛋白水解酶,從而逐漸降解斑塊的細胞外基質,并將膠原蛋白和許多脂質核心以及其他易致血栓形成的底物暴露于血液中,從而引發冠脈內急性血栓形成。但近年來研究發現易損斑塊破裂并非是形成血栓的必要條件,血栓可在纖維帽相對完整、不破裂的情況下形成,這類病變稱為斑塊侵蝕[5]。侵蝕斑塊缺乏脂質核心且存在于斑塊根部,纖維帽厚,僅少量的巨噬細胞或T 淋巴細胞浸潤。光學相關斷層掃描(OCT)及血管內超聲(IVUS)等技術的發展,更加證實了斑塊侵蝕是急性冠脈綜合征的主要潛在機制,Jia 等[6]應用OCT 技術對ACS 患者斑塊性質進行對比觀察,斑塊侵蝕和破裂斑塊兩者均參與ACS 的病理過程,比率分別為31%和44%。研究認為斑塊侵蝕介導的血栓形成從而引發的冠脈事件主要病理機制包括透明質酸代謝異常,透明質酸是細胞外基質的重要成分之一,主要由白細胞、血小板、平滑肌細胞等多種血管壁細胞合成,透明質酸可與CD44 結合參與內皮中斷過程,增生性內膜中透明質酸的積累和中性粒細胞的聚集促進了炎癥的發生和細胞的死亡,除此之外還可與纖維蛋白原等相互作用,誘導血栓形成[7]。Toll2 樣受體(TLR2)是Toll 受體其中之一,TLR2 激活可導致泡沫細胞生成及炎癥反應,促進內皮細胞損傷,激活血小板聚集,進一步形成血栓,有實驗表明,TLR2 在血流紊亂區域高表達[8]。綜上所述,炎癥反應、內皮損傷、血流紊亂等促進了ACS 的發展。
3 危險因素
3.1 常見危險因素 影響PACS 的發生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年齡、性別、脂質代謝異常、吸煙、高血壓、飲酒、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等已得到了廣泛的共識。年齡是ACS 發病的獨立因素,動脈粥樣硬化從兒童便開始,隨著年齡增長,存在危險因素疊加,導致ACS 患病率增加,死亡率增高。王海軍等[9]進行的臨床研究得出結論男性患者的年齡顯著低于女性,≤55 歲比例顯著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考慮是因為女性絕經前雌激素水平偏高,對心血管具有保護作用。高血壓會損害動脈壁,導致冠脈痙攣,血管壁在高壓血流的長期沖擊和壓力作用下,引起動脈內膜的機械損傷,易形成附壁血栓,所以合并高血壓的患者發生PACS 的幾率更大。有研究顯示[10],確診為ACS 患者的吸煙率為39%,其中年齡<40 歲的患者中,有吸煙史的發病率明顯升高。Ying 等[11]認為過量飲酒可導致血壓升高,增加了高血壓病在中青年群體的發病率,過量飲酒也可致血脂含量升高,血壓、血脂升高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過程。糖尿病更與ACS 的發生密切相關,高血糖狀態能夠激發大小血管病變及炎癥反應,此外糖尿病對其預后具有重大影響,Shehab 等[12]一項前瞻性觀察性隊列研究,3576 例ACS 患者中,1906 例患者(53.3%)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平均住院周期、再入院率及在院期間的死亡率均明顯高于非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紅蛋白(HbA1c)是影響和預測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重要指標,特別在45~54 歲年齡組中HbA1c 每增加1%,發生惡性心血管事件的風險增加28%[13]。有CHD 家族史的患者初發ACS 的時間要比無CHD 家族史提前數十年,陽性家族史的患者更應注意其他危險因素的管理控制。
3.2 少見危險因素 除了常見危險因素,近年來的觀點認為一些少見的危險因素也加速了PACS 的進程,其中包括:①基因因素: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是一種易導致PCHD 的基因遺傳性疾病,在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約為1∶313[14]。②高尿酸血癥:ACS 患者血尿酸水平升高導致結晶及沉積物質增加,進而加重斑塊鈣化程度及冠脈狹窄程度,并且尿酸對預后也起著一定的影響,往往合并高尿酸血癥者在接受經皮冠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后發生冠脈無復流及冠脈慢血流的風險增加[15]。③甲狀腺激素:對心血管系統具有調節作用,一方面甲狀腺功能亢進癥(甲亢)誘發的冠脈超敏反應可能導致血管痙攣,從而引起ACS,此外甲狀腺激素易導致體內高凝狀態,促進急性血栓形成,從而導致心肌的缺血缺氧。Abdulaziz[16]在一項前瞻性研究中選取400 例排除服用甲狀腺激素制劑的患者,23.3%的CHD 患者有甲狀腺功能障礙,甲狀腺功能減退患病率為7.8%,而亞臨床甲狀腺功能亢進為2.7%。④血小板增多癥:考慮是由于血小板增多增加血液粘度、活化加速炎癥反應,從而致冠脈粥樣硬化進程提前。⑤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癥作用加速動脈粥樣硬化和內皮功能障礙,患者導致心血管疾病的過早發病和死亡。⑥焦慮抑郁:Liu 等[17]一項研究中,女性PACS 患抑郁或焦慮占比16.63%,提示心理疾病也是導致ACS 提前發生的重要因素,隨著對雙心模式管理的重視,這也成為了一大研究熱點。目前關于少見因素的報道尚不多,其致病機制有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
4 治療進展與預后
PACS 患者的發病時間、疾病分型、病變嚴重程度均是影響選擇治療方式的重要因素,針對不同個體需要制定個性化方案,總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藥物治療(MT)、手術治療以及心臟康復治療。PACS 治療的基石是抗血小板,抗凝治療亦是基本治療,目前臨床上應用最多的抗血小板藥物:環氧化酶抑制劑阿司匹林、P2Y12受體拮抗劑氯吡格雷等,而常見的抗凝藥物包括普通肝素、低分子量肝素、磺達肝癸鈉等,及早使用抗血小板、抗凝藥物可提高救治率。急診早期再灌注在PACS 治療中也十分重要,主要手術方式包括經靜脈溶栓治療、PCI 及冠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對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一般在到達醫院半小時內開始溶栓,或者90 min 內開始介入治療,若發病>6 h,溶栓的再通率很低。除藥物及介入治療外心臟康復在減少再入院次數、提高救治率等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近期有國內外學者針對PACS 患者不同治療方式進行研究,PCI、CABG 和單純MT 三種方式對患者長期生存影響的差異,PCI 組與CABG 組的全因死亡率、心源性死亡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均顯著低于MT 組[18,19]。目前,對于PACS 預后研究尚未得到一致觀點。既往認為PACS 患者預后相對較好,相較于老年組ACS,PACS 患者的心功能相對好,由年齡引起的其他的系統性改變較少,往往PACS 患者急診PCI 率更高,術后合并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并發癥更少[20,21]。但近年來有文獻指出PACS 患者短期預后良好,而長期預后明顯惡化,PACS 患者第一次心臟事件后存活率高,但復發事件控制不佳[22]。總體來說,針對PACS 治療并無明確的指南,仍需更深入的研究以給出更多的循證學依據。
5 小結
隨著飲食、生活習慣、環境問題等多因素的疊加,PACS 患病率和發病率逐年增加,我國在防治心血管疾病方面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目前這些相關危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釋PACS 發病機制,遺傳及精神心理因素在早發人群中影響也尤為重要,但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盡早識別高危人群、控制PACS 的危險因素很關鍵,這是未來研究的重要領域。而且目前尚缺乏針對PACS患者治療的具體方案,對于PACS 的診治需要科學化、規范化和個體化,未來的研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