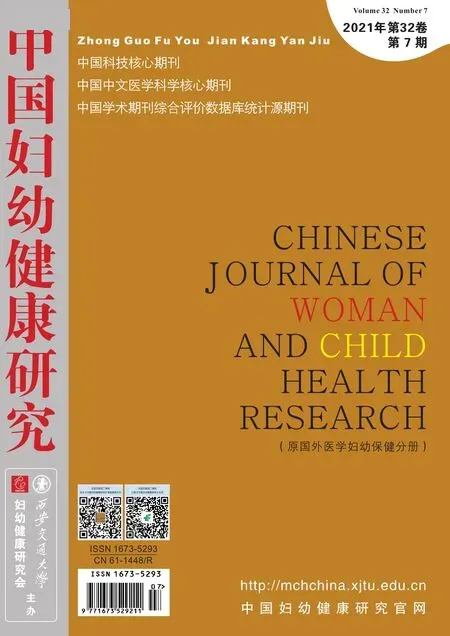乙型肝炎病毒母嬰傳播機制及阻斷技術的研究進展
黃志琴,李 艷,夏建紅
(廣東省婦幼保健院 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廣東省婦兒醫院婦女保健科,廣東 廣州 511442)
全球約有2.57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占68%,每年約有88.7萬人死于HBV感染所致的肝硬化和原發性肝癌[1]。據估計,目前我國慢性HBV感染者約有7 000萬[2],易為等(2014年)報道育齡女性中約8%為慢性HBV感染者,其中1/3已經成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可經血液、母嬰及性接觸等途徑進行傳播,在中國、東南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流行地區,母嬰傳播是重要的傳播途徑[3]。如果不采取干預措施,HBV母嬰傳播的發生率可高達40%~90%,在圍產期發生HBV感染的嬰兒中,多達90%將發展為慢性HBV感染者,其中15%~25%最終會進展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3]。為消除慢性HBV感染給全社會帶來的負擔,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消除HBV母嬰傳播目標,即到2030年實現5歲以下兒童HBsAg陽性率低于0.1%[4]。全面落實有效的母嬰阻斷策略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所在。本文通過檢索近10年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了HBV母嬰傳播機制及阻斷干預技術最新進展,以期為預防HBV母嬰傳播及其圍產期保健管理提供參考。
1 HBV母嬰傳播機制
HBV母嬰傳播是指HBsAg陽性孕產婦將HBV傳播給子代,其可發生于產前、產時及產后3個時期。約90%的HBV母嬰傳播發生在產時或產后。
目前產時和產后傳播機制相對較為明確。分娩過程中的器質性損傷、母體和胎兒血液的微輸血、新生兒與陰道液或上皮細胞的接觸等均可造成HBV的產時傳播[5]。無論是經陰道分娩或經剖宮產分娩,在分娩過程中胎兒或新生兒暴露于母體含HBV的血液或其他體液中,病毒都可能侵入新生兒體內導致HBV感染。產后傳播的本質為水平傳播,是指嬰兒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母乳喂養和其他親密接觸而引起的感染[6]。
產前傳播即宮內感染,僅3%~8%的HBV母嬰傳播是通過宮內感染途徑發生的[7]。現有的針對產時和產后傳播的聯合免疫預防措施并不能完全阻斷HBV的宮內感染[8]。至今,宮內感染的機制尚不明確,且對宮內感染的概念仍存在較多的爭議。
HBsAg雖不能直接通過胎盤屏障,但可通過胎盤滲漏、胎盤感染、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生殖細胞等途徑進行傳播[5]。HBV的宮內感染機制較為復雜,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1.1經胎盤途徑
①胎盤滲漏學說:雖然HBsAg和HBV不能直接通過胎盤屏障,但由于先兆流產、先兆早產、胎盤早剝等造成胎盤損傷或胎盤毛細血管破裂,母血中高載量HBV DNA可經胎盤屏障進入胎兒血循環;②胎盤感染學說:無論胎盤屏障是否損傷,目前HBsAg陽性、HBeAg陽性和高載量HBV DNA狀態可使胎盤組織發育不良,導致胎盤滋養細胞失去屏障作用,受感染的胎盤組織經各層細胞感染至絨毛毛細血管內皮細胞,最終使胎兒發生宮內感染[7,9]。
1.2經PBMC途徑
有研究表明,HBsAg陽性母親中受HBV感染的PBMC可進入胎兒血液循環,造成HBV宮內感染[8]。經PBMC途徑造成的宮內感染在HBV母嬰傳播中占重要地位[8,10]。據一項病例對照研究顯示,PBMC中HBV DNA陽性母親所生嬰兒發生HBV感染的風險顯著高于(約5倍)PBMC中HBV DNA陰性母親所生的嬰兒;相反,血清中HBV DNA陽性但PBMC中HBV DNA陰性的母親所生的嬰兒發生HBV感染的風險僅較血清中HBV DNA陰性且PBMC中HBV DNA陰性的母親所生的嬰兒高2倍[10],表明母體PBMC中HBV DNA陽性是導致HBV母嬰傳播的重要因素,并且PBMC中的HBV DNA可能作為診斷HBV宮內感染的關鍵標志物,提示可通過降低孕婦PBMC中的HBV DNA載量或抑制PBMC從母體向嬰兒的轉運阻斷HBV宮內感染,為控制和預防HBV宮內感染提供新的策略。
盡管國內外研究均表明HBV可感染PBMC,但有關HBV與PBMC的研究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闡明,如HBV侵入和感染PBMC的具體機制及HBV能否在PBMC中進行復制等。
1.3經生殖細胞途徑
經生殖細胞傳播即HBV通過感染卵細胞、精子、受精卵等造成胎兒感染,這是一種尚有爭議且機制不明的傳播方式。Kong等[11]利用免疫組化和原位雜交技術方法檢測出HBV可在卵巢和卵子內感染及復制,同時指出母體HBeAg狀態和HBV DNA水平是重要影響因素。但Jin等[12]在一項長期隨訪研究中發現HBV陽性卵母細胞和/或胚胎的夫婦所生嬰兒都未感染HBV,表明HBsAg在卵母細胞和胚胎中的存在可能不會導致HBV攜帶者子代的HBV垂直傳播。盡管有證據表明,HBV已經存在于許多肝外組織中,包括睪丸、卵母細胞和卵泡液等,且具有垂直傳播的潛在風險[13],但由于目前針對生殖細胞傳播HBV的研究文獻有限,而以上研究也存在樣本量少,其結果缺乏準確性和可靠性,因此尚需大樣本研究來闡明這一傳播機制。
2預防HBV母嬰傳播的干預技術和策略
HBV母嬰傳播是造成慢性感染的主要原因,有效預防HBV母嬰傳播是減輕全球慢性感染負擔的重要手段。預防HBV母嬰傳播需要從產前、產時及產后各個階段進行干預,以確保母嬰安全、減少及消除HBV母嬰傳播。
2.1預防產時母嬰傳播的干預技術
預防產時傳播的措施主要包括分娩方式的選擇及對新生兒的干預措施。
2.1.1分娩方式的選擇
理論上陰道分娩過程中,因產程延長、擠壓、損傷和污染等因素容易造成新生兒HBV感染,而擇期剖宮產因未進入產程而避免了強烈子宮收縮和胎盤屏障的破壞,可以減少產時感染HBV感染的機會。對HBeAg陽性、病毒載量高的母親選擇剖宮產分娩,可降低母嬰傳播的風險,通過對其風險效益進行評價,有可能成為預防HBV母嬰傳播的新措施[14]。但目前我國、美國及加拿大的有關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均指出,在推薦的聯合免疫策略下,剖宮產分娩并不能減少HBV母嬰傳播率,故不推薦以阻斷HBV母嬰傳播為目的而選擇剖宮產分娩。
2.1.2新生兒的干預
首先,分娩過程中需減少新生兒產傷及羊水吸入、盡量縮短分娩時間、保證胎盤的完整性、嚴格無菌操作等。新生兒出生時需立即移至復蘇臺,離開母血污染的環境,徹底清除體表血液、黏液和羊水;處理臍帶前,需再次清理、擦凈臍帶表面血液等污染物,按操作規程安全斷臍,使其盡可能少的暴露于母親血清、羊水及其他母體分泌物中,以減少產時感染。其次,新生兒出生后盡早進行聯合免疫預防是阻斷HBV母嬰傳播的最重要的措施。有研究表明,新生兒出生1h內注射乙型肝炎疫苗及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聯合免疫的HBV母嬰阻斷率可達到97%,且安全性良好[15]。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學分會產科學組和中華醫學會圍產醫學分會的《乙型肝炎病毒母嬰傳播預防臨床指南(2020)》中指出,新生兒應在出生后12h內(越快越好,最好在出生數分鐘內)肌內注射HBIG,同時在不同部位肌內注射第1針乙型肝炎疫苗;并于1月齡和6月齡時分別接種第2針和第3針乙型肝炎疫苗。最后,HBsAg陽性孕婦的嬰幼兒在完成了聯合免疫預防,需在接種完第3針后的第1~6個月隨訪乙型肝炎血清學指標,以明確免疫預防效果,確定有無HBV感染。對于HBsAg和抗-HBs均陰性的嬰幼兒,則盡快再次按“0、1、6個月”方案接種3針乙型肝炎疫苗加強免疫。
2.2預防產后母嬰傳播的干預技術
產后母嬰傳播的本質為水平傳播,主要涉及母乳喂養問題。在免疫預防策略普及以前,人們對HBV感染母親哺乳持有懷疑態度。有研究顯示,母乳中可檢測到HBV DNA和HBsAg[16],但隨著擴大免疫計劃的全面實施,研究表明HBsAg陽性產婦進行母乳喂養并不會增加母嬰傳播概率[9]。國內中華醫學會婦產科學分會產科學組和中華醫學會圍產醫學分會的《乙型肝炎病毒母嬰傳播預防臨床指南(2020)》中指出,無論孕婦HBeAg陰性或陽性,無論新生兒口腔有無損傷,均可進行母乳喂養。
2.3預防宮內感染的干預技術
目前針對產時、產后傳播的干預措施只能阻斷90%的HBV母嬰傳播。近年來,預防宮內感染的干預技術成為研究的熱點。預防宮內感染需針對可能引起的機制及危險因素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有研究表明,宮內感染主要與孕婦血清中HBeAg陽性、HBV DNA高載量呈正相關[17-18]。
2.3.1避免產前的侵入性操作
產前的侵入性操作包括絨毛穿刺取樣術、羊膜腔穿刺術和臍靜脈穿刺術等侵入性產前診斷技術,另外還有胎兒宮內的治療手段。有研究顯示,對HBsAg陽性和HBeAg陰性孕婦行羊膜腔穿刺術不增加母嬰傳播發生率,且各項研究的結果一致[19-20]。但對于HBeAg陽性或高病毒載量的孕婦,研究結果顯示羊膜腔穿刺術后的宮內感染率會顯著增加[19],需盡量避免產前侵入性操作。對于妊娠期行絨毛穿刺取樣術、臍靜脈穿刺術和胎兒宮內的治療等操作,是否引起胎兒HBV宮內感染,尚未檢索到相關報道,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因此,對HBsAg陽性孕婦,如果確實有侵入性產前診斷或宮內治療的適應征,需權衡利弊后再決定。
2.3.2孕期抗病毒治療
近年來,抗病毒治療作為免疫預防的補充阻斷措施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表明,孕婦血清HBV DNA水平與宮內感染風險呈正相關[18]。隨著孕婦的HBV DNA水平越高,圍產期傳播發生率逐漸增加,高病毒載量產婦分娩的新生兒經聯合免疫后仍有5%~10%的免疫失敗率[21]。韓國榮(2019年)研究顯示,孕期抗病毒治療既可以降低孕婦分娩前血清HBV DNA水平,也能進一步阻斷HBV母嬰傳播,從而降低嬰兒慢性感染率,另外可防止孕期肝功能波動,尤其是乙型肝炎家族史陽性或曾有小孩感染者。
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的王貴強等2019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亞太肝病學會、歐洲肝病學會和美國肝病學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均提出建議,對于高病毒載量的HBV感染母親,在妊娠中晚期進行合適的抗病毒治療可作為預防HBV母嬰傳播的有效措施[22-24]。國內最新有關指南(王貴強等2019年)推薦以HBV DNA水平≥2×105IU/mL為口服抗病毒藥物預防母嬰傳播的閾值[9]。妊娠期用藥必須同時考慮其對母體及胎兒的影響。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使用的抗病毒藥物共5種,其中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替比夫定(telbivudine,LdT)、替諾福韋酯(tenofovir,TDF)3種被認定為妊娠B類藥物,用于妊娠晚期孕婦進行母嬰阻斷治療。LAM臨床用藥時間長,安全性數據多,有哺乳期用藥的安全性數據,但相較于另外兩種藥物,其抗病毒有效性最弱,耐藥發生率高,因此市面上已較少使用。LdT于2007年上市,抗病毒效果比LAM強,耐藥率也較之更低,LdT的腎毒性小并有腎臟保護作用[25],但長期使用可能導致肌炎、橫紋肌溶解、乳酸中毒,盡管服用LdT的孕婦短期和長期隨訪研究均未觀察到嚴重的不良反應[15,26-27],但其用藥后的不良反應及病毒耐藥的發生率隨治療時間的延長而增加[28]。TDF抗病毒作用最強,母嬰阻斷效果好,與LAM和LdT無交叉耐藥性,TDF應用至今,無論是用于初治還是經治患者,均未發現耐藥病例[29-30],其是目前妊娠合并乙型肝炎的一線用藥,但長期應用TDF對骨密度及腎功能有影響[31],且有研究報告了暴露于TDF的嬰兒出現骨密度的輕微變化[32]。對于孕期抗病毒治療是否會對母嬰產生不良影響,不同研究報道的結果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更多嚴謹可靠的隨機對照、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進一步證實,而長期隨訪研究是評價各抗病毒藥物安全性、耐藥性及遠期預后影響的關鍵。此外,富馬酸丙酚替諾福韋(tenofovir alafenamide,TAF)是2016年11月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準上市治療成人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的新藥。有研究證實,TAF的靶向性更強,耐受性良好,服藥劑量僅為TDF的1/10即能達到同樣的治療效果,TAF作為核苷類藥物與其他藥物相比,使用劑量低,抗病毒療效高,安全性好,有改善腎功能和骨骼安全參數等優點[31]。鑒于TAF更高的安全性,其在預防母嬰傳播方面的應用也備受期待。目前缺乏TAF阻斷母嬰傳播的有效性、安全性相關臨床證據支持,因此需要開展大樣本、多中心、前瞻性的臨床研究,為TAF在HBV母嬰阻斷方面的應用提供科學的依據。
2.4圍產期的干預管理
我國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5歲以下人群HBsAg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67%降至2014年的0.32%[33],但相較于實現世界衛生組織2030年消除乙型肝炎目標而言仍有距離,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母嬰傳播預防措施落實不當,國家乙型肝炎防控工作目標與實際落實情況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34],這突出了充分落實圍產期HBV母嬰阻斷策略對消除母嬰傳播的重要性。
合理預防HBV母嬰傳播需要掌握正確的知識。劉佳妮(2019年)研究顯示,在臨床工作中,孕婦對HBV母嬰傳播防治措施及相應知識了解不充分,且相關醫護人員并不能準確掌握相關的治療和阻斷方法,這些對乙型肝炎相關知識的認知現狀不僅影響著孕產婦治療的依從性、醫護人員的重視程度,還大大影響了預防母嬰傳播的實際效果,因此提醒從事圍產保健的醫護人員重視HBV母嬰阻斷知識的培訓,提高相關意識,為所有育齡女性提供乙型肝炎相關知識的宣教,以提高接受圍產期HBV干預治療的依從性。另外,由于醫療衛生資源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區的HBV母嬰阻斷臨床實施效果不同。梁穎等(2020年)研究顯示,在偏遠、農村或少數民族地區,公共衛生教育不足,相關醫療機構管理系統不完善,從事圍產保健相關醫務人員缺乏,還存在孕婦HBV篩查覆蓋率低、暴露新生兒出生后首劑乙型肝炎疫苗接種率不達標、部分機構無法滿足檢測HBV DNA的需求、孕期抗病毒治療率低、助產機構缺乏治療的能力和基礎設施等問題[35],導致預防HBV母嬰傳播措施無法切實落地,極大地影響了母嬰阻斷的效果。
為進一步落實母嬰阻斷措施,對慢性HBV感染育齡期婦女人群開展定期監測,對有生育要求者進行感染程度評估,給予積極的健康指導、干預隨訪,尋求減少醫療衛生資源不平衡的措施,積極采取圍產期干預手段有助于更準確地評估HBV母嬰阻斷的效果,同時提高治療依從性,最大限度地減少HBV母嬰傳播,最終實現消除HBV母嬰傳播的目標。
3總結與展望
全球范圍內普及安全有效的免疫預防措施,使HBV感染率顯著下降。目前,HBV的宮內感染成為引起新生兒感染的最主要的方式。越來越多的研究集中于HBV宮內感染的相關機制,但研究結果尚存爭議。因此研究HBV宮內感染機制,探索新的乙型肝炎血清學標志物,可為進一步阻斷HBV母嬰傳播提供新思路,對探索更安全有效的綜合母嬰阻斷策略具有重大的臨床意義。
隨著孕期抗病毒治療的應用,HBV母嬰阻斷工作有了開拓性的成效與進展。大量的臨床研究證實,孕期抗病毒治療聯合新生兒主被動免疫預防,可有效降低孕婦體內的HBV DNA水平,降低胎兒宮內感染和產時感染的風險[29,36]。但孕期用藥既要考慮其有效性、對母嬰的安全性,又要考慮治療的相關風險、耐藥性和經濟負擔等因素,因此需要更有說服力且可靠的臨床研究,以積累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
我國過去30年的乙型肝炎防控工作中,實施了以免疫預防為主、防治兼顧的綜合防控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我國一般人群的HBV感染率顯著下降,但與2030年的消除乙型肝炎目標仍存在明顯的差距。我國從出臺一系列HBV感染防控相關的法律條例和政策、制訂并逐年修訂的指南,再到明確的具體工作指標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實際的乙型肝炎防控工作中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圍產期規范化管理干預措施,以進一步提高HBV母嬰阻斷效率。對農村、偏遠及少數民族等醫療資源相對薄弱地區,政府可加大投入力度,完善醫療服務,減輕患者經濟負擔;將阻斷HBV母嬰傳播的措施融入其他衛生服務工作,提高阻斷措施的可接受性、效率和覆蓋率,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分級診療模式;尋求可替代的實驗室檢測指標以明確治療指征,盡力彌補資源不平衡引起的差距。在保證母嬰安全的前提下,優化并落實HBV母嬰阻斷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減少HBV母嬰傳播的發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