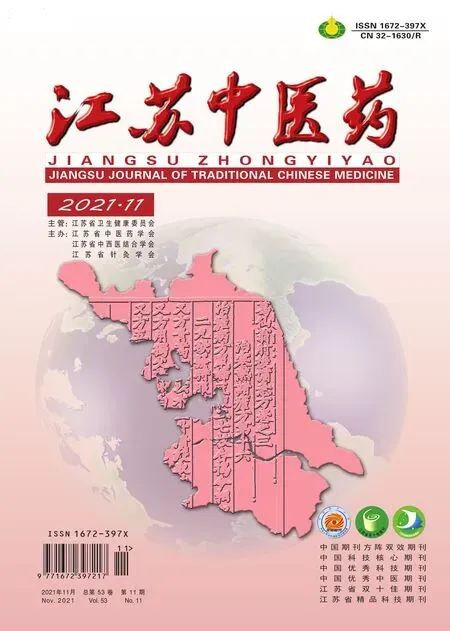《臨證指南醫(yī)案》眩暈證治特色探析
李志鵬 于麗雅
(長春中醫(yī)藥大學(xué)基礎(chǔ)醫(yī)學(xué)院,吉林長春 130117)
《素問·風(fēng)論》曰:“故風(fēng)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認(rèn)為風(fēng)為百病之長,眩暈發(fā)病,風(fēng)居其首,提出“無風(fēng)不作眩”。《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風(fēng)掉眩,皆屬于肝”,指出眩暈與肝之間關(guān)系密切。《靈樞·海論》曰:“髓海不足,則腦轉(zhuǎn)耳鳴,脛酸眩冒”,為后世“無虛不作眩”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東漢醫(yī)家張仲景以六經(jīng)論傷寒,以臟腑辨雜病,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和《金匱要略》中多次提及眩暈的診治,開啟經(jīng)方辨治眩暈的先河。至金元時(shí)期,人們對眩暈有了更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劉完素倡導(dǎo)“六氣皆能化火”“五志過極皆為熱甚”,主張眩暈的病機(jī)應(yīng)從“風(fēng)火”立論,創(chuàng)立“火證眩暈”說。朱丹溪?jiǎng)t認(rèn)為眩暈病因并非肝木之風(fēng)、外中之風(fēng)而致,乃為痰挾氣虛并火,強(qiáng)調(diào)“無痰不作眩”。明代醫(yī)家張介賓則認(rèn)為“陽非有余,陰本不足”,強(qiáng)調(diào)“無虛不作眩,當(dāng)以治虛為主”[1]。
葉天士總結(jié)前賢辨治眩暈的經(jīng)驗(yàn),不拘于風(fēng)、火、痰、虛等學(xué)說,立足于中醫(yī)辨證論治的指導(dǎo)思想,博采眾家之長,兼收并蓄,針對不同病因采用不同的治療方法。《臨證指南醫(yī)案·眩暈》中辨眩暈病因?yàn)樘怠L(fēng)、火、熱、虛,涉及肝、膽、脾、胃、腎等多個(gè)臟腑,病因之間常相互兼夾、轉(zhuǎn)化,形成虛實(shí)夾雜的證候。本文基于《臨證指南醫(yī)案》,將葉天士辨治眩暈的證治規(guī)律總結(jié)如下。
1 審證求因,癥因相宜
1.1 痰濁中阻,風(fēng)火挾痰 朱丹溪強(qiáng)調(diào)痰飲是眩暈的重要致病因素,提出“無痰不作眩”理論[2]。葉天士繼承其思想,認(rèn)為中焦脾胃虛弱,運(yùn)化功能減退,水濕停聚中焦,煉化為痰,痰性黏膩,易阻滯氣機(jī),見脘中不爽、胸痹窒塞,若氣機(jī)閉塞,郁而化火,火乘風(fēng)勢,挾痰上蒙清竅,可致眩暈。葉天士指出痰飲常挾火并風(fēng)上蒙清竅,如《臨證指南醫(yī)案》所言:“痰多,脘中不爽,煩則火升眩暈”,“痰多作眩”,“酒客中虛,痰暈”等[3]29。
1.2 肝風(fēng)內(nèi)動(dòng),化熱傷津 風(fēng)作為六淫邪氣之首,百病之長,常挾其他邪氣上擾清竅。《素問·至真要大論》言:“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fēng)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可見,外感風(fēng)邪為引起眩暈的重要誘因。肝為風(fēng)木之臟,將軍之官,體陰而用陽,主升主動(dòng),其病機(jī)變化易動(dòng)風(fēng)化風(fēng),“風(fēng)氣通于肝”,“風(fēng)勝則動(dòng)”,因此,肝風(fēng)內(nèi)動(dòng)是引起眩暈的病因基礎(chǔ)。葉天士在此基礎(chǔ)上總結(jié)肝風(fēng)致眩理論,結(jié)合臨證經(jīng)驗(yàn)指出肝喜條達(dá)而惡抑郁,可調(diào)節(jié)全身氣機(jī),升發(fā)陽氣,若情志不遂或憂郁惱怒太過,則氣機(jī)郁結(jié),郁而化火,風(fēng)助火勢,氣火上逆,劫爍津液,使人頭暈、喉舌干涸等[4]。若脾土被肝木所克,陽明失降,則易發(fā)嘔吐,如《臨證指南醫(yī)案》中記載:“肝風(fēng)動(dòng)逆不熄,頭暈”,“氣火上升,頭眩甚則欲嘔吐”[3]30。
1.3 氣血虧虛,陰不制陽 張介賓認(rèn)為眩暈一證,因虛而致者十居八九,因痰因火而致者不過一二,強(qiáng)調(diào)體虛乃眩暈的主要病因[5]。葉天士領(lǐng)悟其精髓,認(rèn)為年老體衰或久患虛勞之人,必氣血虧虛,肝主藏血,血虧不能滋養(yǎng)肝木,易引發(fā)肝陽化風(fēng)鼓動(dòng)內(nèi)逆,此肝陰不能制陽之故。葉氏秉承“陽非有余,陰本不足”之思想,亦注重陰陽之間的平衡制化關(guān)系,指出陰虛陽升,化風(fēng)上冒可引發(fā)眩暈,如《臨證指南醫(yī)案》中記載的“煩勞,陽氣大動(dòng),變化內(nèi)風(fēng),直冒清空,遂為眩暈”等[3]31。
1.4 腎精不足,水不涵木 葉氏在總結(jié)張介賓“下虛致眩”理論的基礎(chǔ)上,指出腎氣衰竭之人病眩暈,當(dāng)為標(biāo)實(shí)本虛之候。腎為先天之本,若腎陰虧虛,水不涵木,肝陽上亢,熱化內(nèi)風(fēng),漸蒙清竅,可發(fā)眩暈。葉天士強(qiáng)調(diào),“下虛致眩”乃本虛于下、陽熱化風(fēng)于上之上實(shí)下虛之證,如《臨證指南醫(yī)案》中記載:“此上實(shí)下虛,腎氣衰,不主攝納,肝風(fēng)動(dòng),清竅漸蒙”,“此絡(luò)脈中熱,陽氣變現(xiàn),內(nèi)風(fēng)上冒,是根本虛在下,熱化內(nèi)風(fēng)在上”等[3]31。
2 從因論治,方隨法出
2.1 上熱治膽——化痰清熱,息風(fēng)緩暈 怪病皆由痰作祟,痰飲既是機(jī)體水液代謝的病理產(chǎn)物,也是眩暈的致病因素,《臨證指南醫(yī)案·眩暈》中涉及痰飲為病共有6處,且多夾雜其他病理因素。若痰、火、風(fēng)相兼,宜以羚羊角、山梔、連翹、天花粉、菊花清瀉上焦竅絡(luò)之熱,此為“上熱治膽”之法,再配以半夏曲、橘紅、茯苓、陳皮、薏苡仁健脾化痰祛濕,以天麻、鉤藤、白蒺藜息風(fēng)寧暈。中焦脾胃為生痰之源,痰多者當(dāng)理陽明,宜二陳湯加白術(shù)或外臺(tái)茯苓飲加姜汁、竹瀝消痰和中。痰飲致病廣泛,癥狀百出,若痰飲合并內(nèi)風(fēng),可阻滯經(jīng)絡(luò),加之春時(shí)地氣上升,助風(fēng)內(nèi)沸,則可見言語不利、下肢痿軟之“風(fēng)痱”。
2.2 痰多理中——平肝潛陽,滋陰健脾 肝木屬風(fēng),風(fēng)性善行而數(shù)變,葉天士秉承《內(nèi)經(jīng)》之意,認(rèn)為頭為六陽之首,耳目口鼻皆清空之竅,若肝陽上亢,氣火上升,則有暈冒跌仆之虞,治宜平肝[6]。若肝風(fēng)內(nèi)沸,灼傷陰津,當(dāng)以生地黃、天冬、麥冬、牡丹皮、生白芍、阿膠滋其陰血;若內(nèi)風(fēng)動(dòng)逆不息,則以牡蠣、紫石英、霜桑葉、甘菊花平肝潛陽;肝體陰而用陽,治療肝陽上亢除平肝潛陽外,還需兼顧肝陰,當(dāng)用山萸肉、首烏、桑椹、黑芝麻、牛膝之品;葉氏還指出,肝木上逆,易克伐脾土,使脾胃運(yùn)化功能失司,痰濁內(nèi)生,若因肝陽上亢所致眩暈而兼有痰多者,治當(dāng)兼顧脾胃,當(dāng)以橘紅、南棗、茯神等健中補(bǔ)土,此為葉氏“痰多理中”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治痰須健中,熄風(fēng)可緩暈”[3]30。
2.3 調(diào)和陰陽——補(bǔ)益氣血,育陰斂陽 氣血是生命活動(dòng)的重要物質(zhì)基礎(chǔ),機(jī)體四肢百骸均賴氣血的濡養(yǎng)才能發(fā)揮正常的功能,年高體弱或久病之人氣血虛弱,易發(fā)煩躁,煩則陽動(dòng)于內(nèi),變化為風(fēng),致生眩暈。葉氏認(rèn)為治療當(dāng)以補(bǔ)益氣血為要,以熟地黃、淡菜膠、阿膠、龜甲膠、山藥漿丸、柏子仁、三角胡麻等滋陰養(yǎng)血;陰虛不能斂陽,陽氣浮動(dòng)易化風(fēng)上冒,治以五味子、遠(yuǎn)志、靈磁石、生牡蠣等平肝潛陽。葉氏既重視氣血的重要性,亦不忘陰陽之間平衡互制,補(bǔ)益氣血之時(shí),佐以介類沉潛真陽,咸酸之味育陰斂陽[7],為張氏“無虛不作眩”理論作了進(jìn)一步補(bǔ)充說明,豐富了臨證辨治眩暈的理論。
2.4 下虛補(bǔ)肝——補(bǔ)腎益精,滋水涵木 腎與肝的關(guān)系猶如水與木,肝木之所以能生長條達(dá),疏泄有度,皆賴腎水的滋養(yǎng),若腎精虧虛,肝木無滋,則疏泄失度,肝風(fēng)躁動(dòng),上沖清竅,致生眩暈。葉天士認(rèn)為此為上實(shí)下虛之證,治宜滋補(bǔ)肝腎、育陰潛陽,又因腎宜溫之,肝宜涼之,故當(dāng)以溫納佐涼,方選附子都?xì)馔杓榆嚽白印⒌於U鐝埥橘e所云:“善補(bǔ)陰者,必于陽中求陰”,也體現(xiàn)了葉氏“下虛補(bǔ)肝”的辨治理念。
3 觸類引伸,立法鮮明
3.1 臨證施藥,四時(shí)有別 葉天士臨證施藥,非常重視四時(shí)與用藥之間的關(guān)系。如春日地氣上升,萬物復(fù)蘇,肝木隨之升發(fā)暢達(dá),最易引發(fā)肝陽上亢,克伐脾土,使內(nèi)風(fēng)挾痰上擾而發(fā)眩暈,故春時(shí)辨治當(dāng)先安未受邪之地,后佐平肝之品,如江五十案中,葉氏以半夏、橘紅、茯苓、薏苡仁、炙甘草健中補(bǔ)脾,佐以天麻、白蒺藜平抑肝陽[3]29。夏季多熱盛,易耗傷陰津,當(dāng)以生地黃、天冬、麥冬、白芍、黃菊花等生津益氣清熱為主。秋令多燥,可傷津化火,當(dāng)以羚羊角、玄參心、連翹心清熱涼血,鮮生地、石菖蒲、天花粉、川貝母滋陰潤燥。隆冬大寒,陽氣不藏,腎不攝納,內(nèi)風(fēng)旋動(dòng),漸蒙清竅,當(dāng)以附子、熟地黃、山藥、山萸肉、五味子、石斛等滋補(bǔ)肝腎為要。
3.2 不嫌立異,病久入絡(luò) 葉天士提出“久病入絡(luò)”,辨治頑固性眩暈也從“絡(luò)脈中熱,陽氣變現(xiàn)”入手。在王六三醫(yī)案中,葉氏認(rèn)為用辛、甘、寒性藥物治療眩暈后,雖然癥狀得以緩解,然而病久入絡(luò),熱留絡(luò)脈,可引發(fā)陽氣變動(dòng),化風(fēng)上冒,治療以羚羊角、玄參心、連翹心等清絡(luò)脈郁熱為主[3]31;又如某二四案中,患者素有暈厥,煩勞即發(fā),據(jù)述幼年即然,可見病久入絡(luò),當(dāng)以緩圖,藥用熟地黃、龜甲、牡蠣、天冬、山萸肉等滋養(yǎng)肝腎、益精填髓為主[3]31。葉天士注重病久入絡(luò)理論,對臨床辨治頑固性眩暈有很高的指導(dǎo)價(jià)值,特別是熱郁于絡(luò),“化風(fēng)上冒”的辨治思想,值得后人仔細(xì)揣摩。
3.3 標(biāo)本分治,緩急分明 眩暈病因復(fù)雜,涉及風(fēng)、火、痰、虛等多種病理因素,且病性虛實(shí)兩端,若為虛證當(dāng)宜緩補(bǔ),若為實(shí)邪則必先去其實(shí),若為先天腎氣衰竭,必當(dāng)回陽固脫。葉天士對于眩暈急癥,重視標(biāo)本分治,緩急分明,如:某案,患者肝陽上亢,氣火上升,頭眩甚則欲嘔吐,治當(dāng)先鎮(zhèn)肝陽,后安陽明[3]30;王六三案,患者熱留絡(luò)脈,陽氣變現(xiàn),內(nèi)風(fēng)上冒,上實(shí)下虛,治宜先清標(biāo)恙,后補(bǔ)下虛[3]31;李七三案,患者年高腎衰,頭暈跗腫,不能健步,治當(dāng)以附子、五味子溫固其陽,后宜平肝息風(fēng)[3]31。
4 結(jié)語
通過對葉天士《臨證指南醫(yī)案·眩暈》病案的分析,發(fā)現(xiàn)葉氏熟知前賢治眩理論,蘊(yùn)蓄于胸中而活用于臨床,足以上紹軒岐,下開來者。眩暈一證,病因多途,葉氏宗前賢而參己見,提出“陽化內(nèi)風(fēng)”理論,與痰、火、虛理論錯(cuò)綜融貫,相輔相成。治療上巧辨病機(jī),洞悉原委,其“上熱治膽”“痰多理中”“下虛補(bǔ)肝”之法為臨床治療眩暈一大特色。葉氏臨證施藥,亦注重時(shí)令節(jié)氣對人體的影響,根據(jù)不同的氣候靈活用藥,處方調(diào)劑,無不奏效。“久病入絡(luò)”是葉天士著名論點(diǎn)之一,為臨證辨治眩暈另辟蹊徑,獨(dú)樹一幟。若遇復(fù)雜病癥,當(dāng)秉承“急則治其標(biāo),緩則治其本”的思想,切不可本末倒置,致生他患。葉天士辨治眩暈理念對后世影響深遠(yuǎn),如:近代醫(yī)家周筱齋認(rèn)為眩暈當(dāng)以補(bǔ)虛瀉實(shí)、調(diào)整陰陽為主;陳玉峰主張審證求因,分清虛實(shí);于己百、李壽山則認(rèn)為眩暈病性為本虛標(biāo)實(shí);當(dāng)代醫(yī)家孔伯華、程門雪、任繼學(xué)等,基于葉氏“久病入絡(luò)”的思想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使之形成完整的科學(xué)理論體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