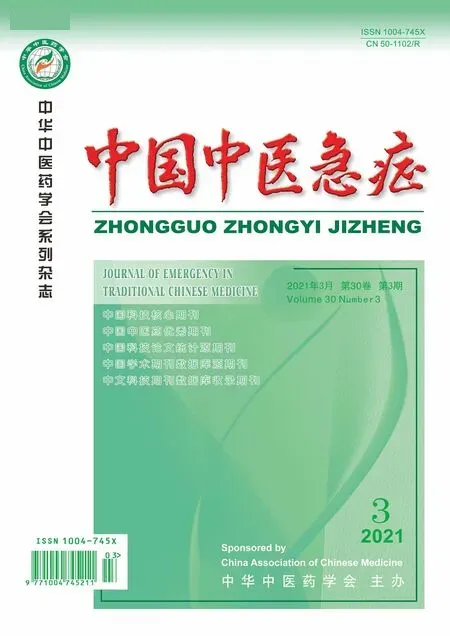《醫學衷中參西錄》張錫純論治心病理論探析*
陳會君 趙御凱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張錫純為清末民初貫通中西醫學的最具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師古而不拘泥于古,參西而不背中,著作《醫學衷中參西錄》堪稱理論結合實踐的經典之作。其在心病領域,立足于中醫經典理論,展望西人之學,詮釋心之神明、君相二火、不歸原及樞機等原理,為后世醫者在領悟中西醫學心病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筆者深受張氏醫術渲染,多次拜讀其作,感悟深刻,于記之。
1 心與神明詮
張氏在神明論中曾駁西人“神明在腦”的時間起源,曰“自神明在腦之說倡于西人,近今講科學者鮮不謂其說至精至奧……吾中華醫學早先西人數千百年而發明之”,并且張氏認為,中醫學的“神明在腦之說”早于西人千年之久[1-2]。張氏認為神明并非只發充于腦,腦只是神明的所藏之處,而將之展現出來的為心,即發露于心,故有“蓋言神明雖藏于腦,而用時實發露于心”之說,這更加詮釋了心在機體中的重要地位。《素問·脈要精微論》曰“頭者,精明之府”,頭顱只為腦的外殼,腦為外殼內的中心點,為神明所藏之處,而腦者,無思無慮,自然虛靈,用時必須經過心表達出來。《丹經》認為憂思及心,而憂思就是通過心腦貫通才以成形。又如《六書精蘊》云“元神何宅,心為之宅,元神何門,囟為之門”。進一步印證了張氏學說的神明發于心,藏于腦,其又認為神明為純陽之物,腦藏之,腦不畏寒,心發之,因此心恒溫,心與神明是有直接的關系,而上升至現代中醫心病的理論實踐中[3]。腦藏之,心不發之,多因心陽不振、陰寒凝結所致,故而神明與心斷隔,病證多見胸痹、心痛等癥,病因多雜,但寒邪、陽虛為重中之重,臨癥其人心胸憋悶,四肢厥冷,多伴神志不寧,舌淡胖,脈多澀沉細。治法首以溫心陽不振之法,心之得暢,神明才能展現,病情預后則會較好。若上升至現代醫學的角度而言,其病多見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室上性早搏或室性早搏)等癥,但總體不外乎強心、擴管、復律、穩心等治法[4]。無論中醫學還是現代醫學,對于此種疾病的預后都是以神明得暢為主[5]。張氏更以心與神明理論領悟養生之道,云“凡人之享大年者,下元必常溫暖,氣血必常充足,人之神明固可由腦至心”[2],長壽者,下焦多溫暖,氣血多充足,氣血充足則可上灌注于心,心之氣血充足,則神明自然明亮,真氣也就凝聚,即神氣充足,丹田溫暖,壽命之根自然壯固。可見人體精神之氣的旺盛,是與心的溫煦功能分不開,故在診治心病方面,應多倡導穩固心陽之法[6]。
2 論人身君火、相火有先后之分
張氏在談及君、相二火,以道家學說、《黃帝內經》入手,避開先后,只論及兩者的微妙關系。又云“道家以丹田元陽為君火……是以《內經》論六氣,止有少陽之火,而未嘗言命門之火”[2],故道家以“丹田之火”作為心之火,而《黃帝內經》以膽中之火作為相火,說法不同,但其出發點、落腳點卻為一致。《黃帝內經》論六氣,君、相二火只作少陽,以足少陽膽經為主,心在上,膽在下,心陽臨照中焦脾土,中焦熏蒸上元君水,故此張氏將上中焦失衡病機引入臨床,用實踐說明兩者關系,其將經典方“《金匱》苓桂術甘湯”加減應用于上元不足,飲食不化病證中,下元不足,上元失去溫煦,久致寒痰凌心,君相二火不通,故而脾土虧虛,飲食不化,辨證配伍巧妙細微,又不傷及上下元氣,可謂理、法、方、藥展現得淋漓盡致。曰“蓋心為太陽之火,如日麗中天,臨照下土……至胃中之食,則又賴上焦之心火,中焦之火化之”[2],提出應溫煦上元,下照中焦,脾氣充足,既能熏蒸上元,又化飲食。因此,張氏未提及君、相先后之分,只談臨證兩者的相關性,更加體現出人、自然、陰陽、五行之間的整體性。而在中醫心病的臨證論治方面,將君相二火巧妙地運用實踐,以脾土不運,相火虧損,上元不足,則君火虛弱,作為兩者失衡的重要病因,脾土得暢,上元得暢,心病自安,病機相互夾雜,相互轉換,更加體現出張氏所說的君相之火未有先后之分的道理,因此,診治心病應多整體辨治,深思心與五臟的密切聯系,重視并發癥,才可能全面認知心病[7]。
3 論火不歸原治法
首先,張氏批評方書中將“下焦之火”命為“陰分之火”或者為“龍雷之火”的概述,曰“謂下焦之火生于命門,名為陰分之火,又謂之龍雷之火,實膚淺之論也……下焦之火為先天之元陽,氣海之形,如倒懸雞冠花,純系脂膜護繞搏結而成”[2]。認為“下焦之火”起源氣海,為先天元陽,可以縈繞周身之氣,因其在下焦,故其比喻為“倒懸雞冠花”。火不歸原,即氣海元陽浮越,多夾雜中醫心病的臨床表現,治法各有所宜,張氏一一羅列[1]:1)其病,頭暈目眩,面目潮紅,心悸怔忡兼見氣息鼻賁,則為氣海虛,無從固攝下焦氣化,導致元陽浮越,脈象浮大無根,治法多予山藥、山茱萸肉、人參溫補,赭石力專下行,佐龍骨、牡蠣潛陽,補而斂之,鎮而安之;2)其病,口苦舌干,咳喘不斷,心間時有灼熱,多為下焦真陰虧損,元陽無所戀,上浮之;3)其病,上熱下涼,為上陽分微弱,下陰分既虛,兩者無交集,治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多用下焦滋補之藥,藥效平和,且不傷中氣;4)或其病,上部燥熱,心中不安,時有時無,下部自覺涼意濃濃,甚至作瀉,因元陽大虛,下焦積寒日久,脈多弦遲細弱,或兩寸浮而看似有力。治法多用芍藥,解上焦之熱,結合山藥、人參斂元陽之氣,下歸其宅;5)其病,胸部滿悶不適,時時作呃,多吐痰涎,為沖氣或胃氣上逆,元陽浮越,胃火夾痰火,癥似心病疾病,治以沖胃之氣下降,諸病自除;6)其病,憂心忡忡,心中煩躁,易怒疑人,自覺熱于肋下,散在周身,脈多滑數之象,兼寸關有力,為傷心后生熱,引動少陽之火,多數上越,因此以心病癥狀多見,治以芒硝、臭剝(溴化鉀)解心經,化熱痰,山藥健脾胃,滋周身,取寒涼之藥節制相火上浮,重用山藥加以滋補周身,防止元氣大傷,故為取濟相顧之道;7)其病,頭暈耳鳴,周身發熱,短氣咳喘兼心前區悶熱,只思食水果,但食后腹脹不適,脈多弦遲細弱,此為上中二焦陽虛之病,多有寒飲停滯中焦,溢于膈上,迫使心肺脾胃之陽上越,從臨床癥狀來看,兼有外越之嫌,治以張氏“理飲湯加減”,干姜、桂枝助心陽,生白術、茯苓、甘草理脾胃濕氣,兼杭芍、橘紅、厚樸等藥加減,助君臣之藥降虛火、平肝膽、利痰飲。
上述陳列不歸原之證,張氏追其病原皆不同,但均為內傷之證,癥似心病,或兼有心病表現,但究其根源,不外乎虛、實之證。張氏在臨床辨病中,辨證根源,配方加減,為治療心病、心病夾雜病及相關鑒別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論思想,同時也為后世醫者在中醫心病臨證辨治方面打下堅實的臨床基礎。
4 論樞機亢進
心,血脈循環樞機也,動一發,周身皆動之。張氏論治心病首先以心機的亢進為切入點,多從陽明胃腑及三焦、元神及氣血等方面的相互關聯性來論證,因此,本文從以上兩點深度剖析。
4.1 由陽明胃腑引病三焦論治心病 論及心病,張氏先談心機亢進之證。有外感熱邪導致陽明胃腑上蒸以致亢進,有燥糞內留不通而致心機亢進,總歸多以陽明胃腑談論之,但實則病因為下焦陰分損傷,上下無法維系。譬如,心病不寐門中,一人年愈六十,多食易饑,暗傷中焦胃腑,訴其心中自覺發熱,胃脘發脹,導致夜不能寐,輾轉反側。張氏認為中焦得熱,火升心神則無法平降,加之病患年愈六十,病而久之腎精、腎氣自損,以致陰陽無法交融,故而不寐。在本病的治則及方藥配伍上,其多采用滋腎潛陽,降胃鎮肝,用藥多以大劑量山藥滋補下焦,加之大甘枸杞、玄參、北沙參共補肝腎之氣陰,降心間虛火,重用赭石,其色赤、質重,治療陽明胃腑燥熱,從而使心陽得降,佐龍骨、牡蠣、酸棗仁收斂之品,保護神魂安定,方可穩睡[8]。
張氏的心機亢進陽明胃腑思想其涉及中焦,但理論是以陽明為證候,從下焦引至上焦,病機的關鍵在于下焦,而治療的根本在于消除本證,本證消除標證自安,在配伍用藥方面,簡潔明了,看似以陽明論治,但實以補腎之精氣,再重降陽明,收斂并用。
4.2 由元神、氣血雙損論治心病 元神藏于腦,發于心,思慮過多其心必熱,熱則亢進,故病患多迷惑,也就是西人常說的注意力不集中,張氏認為思慮所生之熱多與痰涎相關,但最終的結局是損傷周身氣血。故曰“心機亢進之甚者,其鼓血上行之力大,能使腦部血管破裂,氣與血并走上而大厥也”[2]。所以說,由于思慮過多而導致的心機亢進,首先是以元神受損,其初始癥狀多見頭腦作響,間覺暈眩,肢體無力等癥,其病機愈久涉及氣血,會產生心悸,心中跳動不安為多見[9]。治法上,張氏以自擬名方“建瓴湯”引血下行如建瓴之水,醍醐灌頂,及時止損,使元神得安,元神安定方可重補氣血,以山茱萸肉、酸棗仁、山藥諸藥保其氣,龍眼肉、熟地黃、柏子仁養其血,朱砂、龍骨、牡蠣安神定志,倘若心房狹小者,多考慮瘀滯,去朱砂、龍骨、牡蠣加菖蒲、遠志開竅化滯,遠志含有稀鹽酸,兩藥合用可以調節心臟功能,后用紅糖水送服,助其血脈通暢。
張氏在心機亢進中表達的元神、氣血思想是以神損牽致氣血雙損,心主血脈,若單單只補氣血,導致氣血不受元神控制,血脈逆亂,勢必心病頻發,重者逆于上充血破裂,治療原則以安定元神,再補行氣血,主次分明,辨證加減。
5 論樞機麻痹
如有心機亢進者久而不愈,多以病因、病機標本失治,延至日久,則為心機麻痹。心機麻痹病因多端、治法各異,有素體陽虛,以致寒邪叨擾,心臟之陽麻痹更甚者,故曰“至心臟麻痹之原因,亦有多端,而究其原因,實亦心體虛弱所致”[2],因此,張氏衷中參西,自擬名方理飲湯以復心臟之陽的同時,還首次提出可服西藥斯獨落仿斯(毒毛花苷)及實答里斯(洋地黃),可謂強壯心臟之良藥。如有邪毒侵擾,充塞六脈以致心神不寧,心機麻痹者,其自擬急救回生丹、衛生防疫寶丹掃毒菌、利心臟,同時投以西藥臭剝(溴化鉀)等,可救一時之困,故曰“有心臟為傳染之毒菌充塞以至于麻痹者,霍亂證之六脈皆閉者是也,自當與掃除毒菌之藥并用”[2]。因此,本文從本體陽弱、邪毒驚擾神明這兩方面展開深度挖掘。
5.1 本體陽弱 素體陽虛者,心臟之陽本身薄弱,加之胃部寒邪凌逼膈上,以致心臟陽虛與寒邪交滯,為重癥,其心肺脾胃皆為陽虛,脈象異常微弱,曰“心臟本體之陽薄弱,多兼胃中積有寒飲溢于膈上,凌逼心臟之陽,不能用事”[2]。而臨床癥狀則以心、肺尤為突出,多見喘氣、滿悶、咳吐痰涎等癥。張氏認為此種心臟麻痹者,主治心肺,心肺得暢,周身之氣才可通利,以致脾胃功能正常運行,可解心臟之寒陽,其自擬名方理飲湯,以干姜、桂枝為主,助心肺之陽宣通,再以白術、茯苓、甘草淡滲脾胃濕氣,厚樸、橘紅、生杭芍破氣利痰,潛熱斂潤。若有素體陽虛者,受外感之邪,多由表入里,轉至陽明,心臟為熱所傷,最終成為麻痹重癥。張氏認為此證應以大劑量人參湯破心脈,激活心臟搏動功能,再給予毒毛花苷,其性質溫和,可改善心肌炎癥,從而中西醫結合診治,療效顯著,曰“至西藥斯獨落仿斯為強壯心臟之良藥,而其性又和平易用,誠為至良之藥”[2]。
張氏對心病素體陽虛之人的診治,從表、里兩方面致病因素著手。表證者,心臟受熱邪損傷,多中西結合,補氣以激活心臟舒張及收縮功能,再以西藥強心劑改善炎癥。里證者,所有寒邪均在機體內部,加之陽虛寒邪交滯,心臟受寒邪損傷,多以溫熱之藥,通上焦心、肺之陽,再利脾胃,通達周身,以緩心臟麻痹。
5.2 邪毒驚擾神明 外感病癥多有邪毒,體質虧虛者,毒菌侵襲六脈,以致心臟麻痹。張氏在本病治療原則上主要以興奮心臟、清掃毒邪為主,自擬名方急救回生丹、衛生防疫寶丹,其中樟腦、冰片為激活心臟功能之品,朱砂、薄荷冰均為清掃邪毒之品,方藥配伍簡單,治則治法明了,且兩方對涼熱邪毒均有效果。而對本病的繼發癥狀,張氏另辟新境,如麻痹者,六脈皆閉,神明不安,常出現驚悸癥狀,并且這種癥狀恰好與邪毒所致心臟麻痹癥相反,病機多虛實夾雜,故曰“心中神明不得寧靜,有若失其憑依,而常驚悸者,此象多雜,與麻痹相反”[2],而對于此癥狀者的虛實辨證及用藥上,靈活加減,治本換標。虛者,脈微弱無力,多以黃芪、白術、黨參重補氣為主,生地黃、玄參滋陰,以防重補太過生熱,佐以酸棗仁、山茱萸肉凝神收斂之功。實者,脈數兼滑,多以生地黃、玄參瀉熱為主,龍眼肉、熟地黃補虛,以防瀉其太過,佐以龍骨、牡蠣保神鎮魄。張氏認為此癥狀如若服用溴化鉀,只能緩解一時之效。因此,西藥在處理心臟麻痹并發癥上效果并不突出,應當四診合參、整體論治,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作用。
若基于現代醫學的構架,張氏認為的傳染毒菌使心臟麻痹之證,可與病毒性心肌炎相互貫通,而對于后續治療上出現的驚悸等癥,他也給出了新的治療方案。對后續醫者在中西醫領域診治心臟麻痹癥或者病毒性心肌炎,甚至預防繼發疾病,如驚悸、不寐等癥,提供了新思路、新療法,真可謂融貫中西。
6 結 語
品味張錫純的醫學思想,不僅是研讀古今文化的碰撞,更是中醫學領域的一次大升華。能立足中醫,不改其道,對中醫所倡導的整體觀念,能巧妙地結合五臟六腑,形神氣血,詳細闡明了外在的“真象”與“假象”臨床表現,對于現代中醫心病學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創新[10-11]。其在心病領域,辨證論治,方藥考究,具有自己獨特的領會,在中藥的運用上能夠抓住藥物的藥理學屬性,師古而不沉拘于古,中西合用,相得益彰,西藥用在局部,緩其標,中藥求因,重其本,給后世醫者展現了一次真正的中西醫實踐與理論的大結合[12]。并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帶給我們的首要啟示就是要立足中醫,以中醫為本,辨證看待醫學臨床中遇到的問題[13-14]。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臨床診療,我們都必須時刻保持中醫思維,結合現代醫學觀,這一點對提高臨床療效很重要。
自西醫東漸,錫純先生在面對西醫學的廣泛興起中,能衷中參西,匯通新舊,追求醫學界的盡善盡美,無偏私之見存于心,實為清末民初中醫學的大家[15]。其次,成書《醫學衷中參西錄》記錄了張錫純在論治心病方面,細審病機,辨證施治,見解精進獨到,方藥靈巧多變[16],為臨床診治心病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實為中華醫學之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