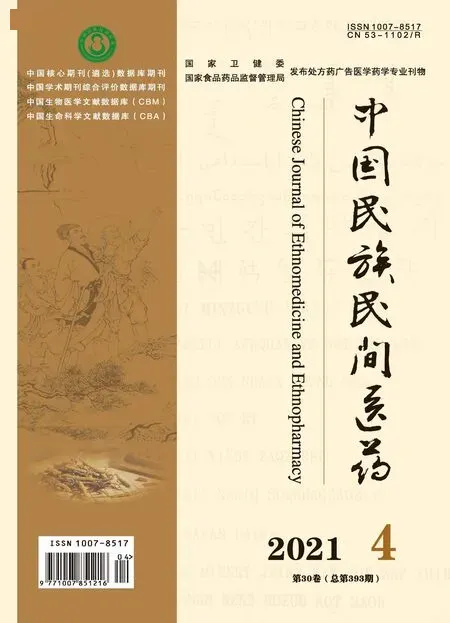傣族傳統文化對傣醫外治法發展之影響
謝昌松 李 媛 陳 普 李瓊超
云南中醫藥大學,云南 昆明 650500
傣醫外治法是傣醫最具特色的治療方法,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點。在數千年積累、沉淀的過程中,受到傣族傳統文化,如宗教信仰、自然環境、生活習俗等的影響,傣族傳統文化與傣醫外治法交融甚廣,聯系密切,傣族傳統文化是傣醫外治法萌生、發展的土壤。
1 傣醫外治法的形成與原始宗教密切相關
1.1 巫醫同源 傣醫學與原始宗教同一起源[1-2]。在“萬物有靈,靈靈相通”觀念的支配下,傣族認為神創造醫藥,必須聽從神的旨意,求神送鬼的巫師應運而生。錢古訓所著《百夷傳》中記載:“病不知服藥,以姜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側,病虐者多愈,病熱者多死”[3]。由此可見,在古代傣族民間已有外治療法,但并不排斥巫術,而是采用巫醫并用的方式治療疾病,很好地佐證了巫醫同源并用的史實。紋身是傣族圖騰崇拜的一種表現形式[5]。在紋身過程中意外發現針刺身體某些部位可以緩解疼痛,治療疾病,由此產生了“沙雅”療法(刺藥療法)[4]。此外,口功療法的產生與原始宗教有著深厚的淵源,是“神藥兩解”的典型代表,是一種以念口訣為主,用口吹、手摸患處治療疾病的外治方法。目前該方法在民間廣為流傳,尤其被廣泛用于骨傷科疾病[6]。
1.2 天人合一整體觀的形成與原始宗教密切相關 原始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觀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影響傣醫外治法天人合一整體觀的形成。傣醫十分注重季節氣候及地理環境對人體的影響,并將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與自然界的變化融為一體,遵循自然界的變化規律,運用與大自然息息相關的天人合一觀診治疾病。《檔哈雅》中記載不同季節服用的防病處方和外治療法,如冷季寒冷,多用辣味藥,運用暖雅(睡藥療法)、烘雅(熏蒸療法);熱季炎熱,多用苦味藥物,并運用沙雅(刺藥療法)、達雅(搽藥療法);雨季潮濕,多用香澀味藥物,運用阿雅(洗藥療法)、剔痧(除痧療法)[7]。在藥物的采集、使用上,也非常強調應順應自然界對藥物生長的特定影響,認為不同時令、不同季節、不同時間、不同地理、不同環境中藥物作用不同,藥效強弱有異。《嘎比迪沙迪巴尼》中記載:5、6月份采花、枝、葉、種子(果);清早采果(種子);正午采花;下午采樹心;傍晚采樹干、根莖;黃昏至凌晨藥效在嫩尖;正午至下午藥效在樹心;正午至黃昏在樹皮;下午至黃昏藥效在根部[8]。順應自然的藥物采收規律為傣醫外治法喜用鮮藥、善用鮮藥提供理論依據。
1.3 生命觀的形成與原始宗教密切相關 傣族創世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記載地球是英叭天神用水混合其他物質造成的,水是孕育萬物之源[1]。傣族對水的崇拜影響著傣醫生命觀的形成。傣醫認為:“沒有水,萬物可以枯死,人體沒有水,生命就難于存續”,水是人體生命活動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質,水可消除九十九種疾病。水被用于解釋生理變化、闡釋疾病、治療疾病。《嘎牙山哈雅》中指出人體內有12種水,若發生病變可從水塔論治[1]。傣族民間傳說筍塔與金掌“圣跡”故事中也描述了水可治療癭瘤、眼疾[3]。此外,口功療法、睡藥療法、熏蒸療法、洗藥療法、拖擦藥物療法等特色外治療法的主要介質就是水,這些與水有關的外治方法至今仍被廣泛應用。
2 南傳佛教促進傣醫外治法發展完善
2.1 為傣醫外治法提供理論構架支撐 據大量史料考證,傣醫學的四塔(風、火、水、土)、五蘊(色、識、受、想、行)理論廣泛記述于《巴臘麻他坦》、《維蘇提瑪嘎》、《嘎牙山哈雅》等文獻中,與南傳上座部佛教《解脫道論》、“觀四大”、《大象跡喻經》等經典中所記載的“四大種”“五蘊”有相似之處[3]。傣醫在積累和總結醫療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借鑒佛教的“四大”“五蘊”概念,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形成自己的四塔五蘊理論。傣醫將四塔五蘊理論運用于外治之中,為闡釋病因病機、疾病發展變化、法立組方提供理論依據,是外治法的核心理論。如用入水塔的旱蓮草外擦身體治療火塔偏盛,水塔不足引起的發熱,用睡藥療法治療火塔不足的病癥,用洗藥療法治療水塔過盛的疾病。
2.2 充實傣醫外治法內涵 隨著佛教的傳入,大量的醫學內容也隨之傳入。論藏“阿皮達馬”中記載人的生理、病理和醫藥知識,如人的皮、肉、血、骨等生理現象。并認為不同的屬相,不同的出生月、日具有不一樣的皮肉和血骨,月份決定皮肉,日期決定血骨[3]。傣醫吸收其所長,在診治病時要詳細詢問病人的屬相、皮肉和血骨,以判斷人的生理現象與自然界環境的關系,綜合歸納各種病因,以便診斷,采取相應措施治療疾病。此外,傣藥中有不少來源于印度的傳統藥物,隨著佛教的傳入成為傣族民間藥物,如兒茶、檳榔、姜黃等,豐富、充實傣醫藥,如姜黃被廣泛運用于包藥療法、睡藥療法、熏蒸療法、搽藥療法之中。
2.3 促進傣醫外治法的傳承及發展 佛教的傳入,促進了傣文的創制和應用,為傣外治法的記錄、學習、交流、傳播提供了工具和條件,促進傣醫外治法的應用與發展。有傳說在八萬四千冊的佛經中,醫學經典就有四萬二千冊[3]。同時,佛教傳入后,幾乎每個傣族村寨都建立佛寺,傣族男性青年在佛寺中接受教育,學習各種文化知識,其中包括醫學理論和醫藥知識。佛寺成為培養傣醫藥人才的學校,為傣醫外治法的學習、交流、普及、繼承、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是承載傣醫外治法的搖籃。
3 貝葉文化推動傣醫外治法文獻整理
貝葉文字載體的產生和發展,加速了傣醫外治法知識的收集、整理、保存、應用,涌現出眾多傣醫著作,如《嘎牙山哈雅》、《檔哈雅龍》、《桑比打嘎》等[3],書籍中記載大量醫學知識及外治療法。《嘎牙山哈雅》記載人體基本組織及臟腑功能為傣醫外治法提供解剖基礎及治療機理。此外,書中論述人與氣候、居處環境與疾病發生的關系,各季發病特點及預防措施、常用方藥,三個不同年齡階段生理變化、好發疾病及防治方法,這對傣醫外治法臨床運用具有較高的指導價值[7]。
4 雨林滋養傣醫外治法
4.1 提供豐富獨特的藥用資源 傣族先民認為,雨林曾是他們的諾亞方舟,使傣族躲避了滅項之災,保存了種族。因此傣族認為有雨林,才會有生命,至今都保留有樹崇拜的習俗。傣族諺語說“狩獵不要進神林,撒網不要進龍潭”。傣族人民對雨林充滿崇敬、敬畏、保護的情感觀念及價值體系,成就了西雙版納“植物王國”“天然藥物寶庫”和“傣藥王國”的美譽。豐富的藥用資源為傣醫藥及其外治法的發展創造了優越的條件,垂手而得的新鮮藥物使傣族喜用鮮品,善用鮮品,無論是外洗、外包、外擦、坐藥、睡藥、熏蒸或是刺藥,傣醫推崇鮮品為佳。此外,驅避劑、煙熏劑、佩掛劑的應用,也與熱帶雨林豐富的藥用資源息息相關。
4.2 創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療方法及理論 在雨林這座“天然藥物寶庫”中,傣族先民不斷探索、發現、總結和積累著醫藥知識,創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療方法及理論。據《阿尼松桑順細點》《登達格》等史料記述,傣族先民在“天然寶庫中”以野生動植物充饑的過程中,獲得大量外治法。如“光冒呆”(鹿不死之藥)包敷患處治療骨折,重樓外包治療毒蛇咬傷,雞矢藤熏蒸治療頭痛,生藤編制帽子預防感冒[10],大揚草外擦、外洗治療牛皮蘚[5],睡藥療法治療風濕病。這些外治方法及藥物的發現,都離不開熱帶雨林的饋贈。此外,富有地方特色的傣醫藥理論也源于雨林,如四塔五蘊理論、雅解理論、風病論。傣醫對四塔及四塔之間的關系闡釋,來源于對熱帶雨林的長期觀察及體悟,雅解理論的起源來自于解毒藥物文尚海的發現與應用,風病論來源于對自然界風的啟發與感悟。
5 酒文化豐富傣醫外治法
5.1 酒炙 傣族的酒文化歷史悠久。在傣族傳說中,酒來源于野果。明·錢古訓《百夷傳》記載在元、明之際,在傣族地區,“其地有樹,狀若棕,樹之梢有如竿者八九莖,人以刀去其尖,縛瓢于上,過一霄則有酒一瓢,香而且甘,飲之輒醉。”[3]酒,傣語稱“勞”。傣族人民在長期的造酒、飲酒的過程中對酒的特性有了認識并加以利用,如酒炙被廣泛運用于外治療法中,治療風濕麻木、肢體疼痛各癥時,先將傣藥切碎加水煎煮或炒或蒸,再拌入酒或炒熱之酒糟,患者趁熱睡于藥床上。接骨或治療跌打扭傷、風濕麻木疼痛、頭痛、腰腿疼痛等癥時將鮮藥,切碎搗爛加入酒置于火上炒熱,趁熱包敷于患處。《傣族傳統醫藥方劑》載治療肢體關節疼痛時用藥粉加酒炒熱外敷[9]。
5.2 藥酒 傣醫認為酒是良好的有機溶媒,藥物的多種成分均易溶于酒中,故創制了大量的外用藥酒方。如西雙版納州傣醫院制劑勞雅打攏梅蘭申(外用追風鎮痛酒)用大劑量白酒浸泡飛龍掌血、魚子蘭、姜黃等藥物,通過外擦或睡藥或拖擦或熏蒸等方式治療中風偏癱后遺癥、風濕病、痛風引起的周身肢體、肌肉、筋骨酸麻脹痛或痙攣劇痛[9]。治肢體關節、肌肉、筋骨酸麻脹痛,活動不靈,屈伸不利,取飛龍掌血、黑皮跌打、大葉鉤藤(懷咪王)、樹菠蘿樹心等藥物泡酒外擦患處[9]。治小兒高熱不退,取木奶果鮮葉適量,用火烘烤后放入酒中浸泡,取藥酒擦患兒雙上肢[9]。
5.3 以酒入方劑 傣醫喜用酒,善用酒。傣醫認為酒為甘辛大熱之品,具有補火散寒,祛風活血,消腫止痛,通行血脈,引藥勢行全身之功。酒可以增強藥力,改變藥性,因而無論是丸劑、散劑、水浸劑、磨劑還是酊劑中,多將酒配合其它藥物用于臨床,具有獨特的療效與保健作用,睡藥、刺藥、搽藥、拖擦等方劑中多用到酒。
6 小結
特定地區的特定生活、生產環境形成了特定的醫藥,傣醫外治法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傣族特有文化的滋養,深受傣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傣族傳統文化與傣醫外治法交融甚廣、聯系密切,傣醫外治法吸收、融合了傣族原始宗教、南傳佛教、貝葉文化、雨林文化、酒文化的內涵,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及區域特點的治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