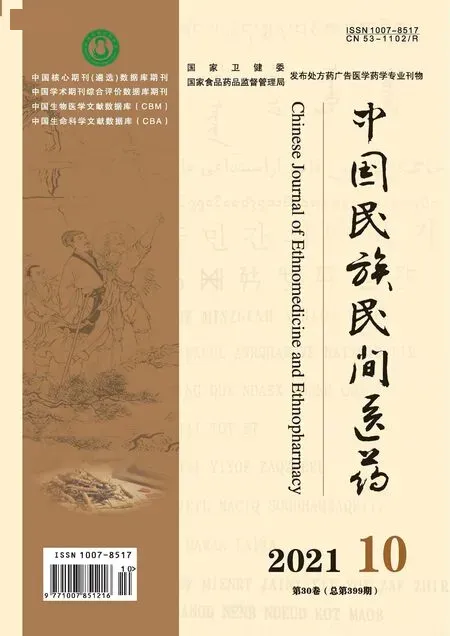牛陽教授從脾胃調治乳腺癌術后臨證經驗
馬飛云 牛 陽,2 △ 馬文英
1.寧夏醫科大學,寧夏 銀川 750004;2.寧夏醫科大學回醫藥現代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寧夏 銀川 750004
近年來,全球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水平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 并且乳腺癌全球女性惡性腫瘤發病、死亡的占比也在有所增加[1]。在我國,乳腺癌發病率位居城鄉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率的首位,是危害居民生命健康最主要的惡性腫瘤之一。但是相對于其他的惡性腫瘤而言,乳腺癌的預后較好,生存率相對較高,5年觀察生存率為72.7%[2]。嚴華[3]收集了60例女性乳腺癌術后病例,探討中醫綜合療法對乳腺癌術后生活質量的影晌,結果顯示中醫綜合療法可以有效地提高乳腺癌患者術后的生活質量,包括減低其臨床癥狀、増強其社會適用能力等,為中醫綜合療法能夠減低乳腺癌復發轉移提供了臨床依據。牛陽教授從事臨床工作多年,善于化裁經方,在臨床辨證用藥時,重視顧護脾胃。對于乳腺癌術后的調治很有見解,且療效確切。筆者有幸跟隨牛陽教授學習,受益頗多。現將跟診心得總結如下。
1 中醫病名及術后病因病機
乳腺癌,中醫病名為“乳巖”,是發生在乳房部位的質地堅硬如巖石的腫塊。宋朝陳明在《婦人大全良方》中首次提出“乳巖”病名,把乳巖描述為“若初起,內結小核,或如鱉、棋子,不赤不痛。積之歲月漸大,崢巖崩破如熟石榴,或內潰深洞……名曰乳巖”。元代著名醫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曰:“婦人憂郁秋遏,時日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如鱉棋子,不痛不癢,十數年后方為瘡陷,名曰乳巖”。明朝陳實功在《外科正宗》中記載:“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初如豆大,漸若棋子,半年一年,二載三載,不痛不癢,漸漸而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曰后腫如堆粟,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若泛蓮,疼痛連心,出血則臭,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巖,凡犯此者,百人百必死”,對乳腺癌發展變化的臨床表現以及它的不良預后進行了詳細描述。我國古代醫學對乳腺癌的認識較早,而且對它的臨床表現、發病特點、病因病機等都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也已經認識到該病轉移的情況、不良預后以及它的難治性。
正虛邪實是腫瘤發生的基本病機,而乳腺癌手術本身又會對機體造成損傷。正氣不足,氣血不充,營衛不周,最容易導致邪氣的趁虛而入,研究[4]表明乳腺癌術后出現體虛乏力、食欲減退,甚至短期內出現術后復發或者腫瘤轉移,都與手術損傷正氣、耗傷氣血有關。究其原因,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全身氣血及水谷精微都有賴于脾的運化和輸布,乳腺癌術后正氣損傷、脾胃虛弱,氣血生化乏源、運化無力,以至于全身得不到水谷精微的滋養和補充。牛陽教授非常強調脾胃在乳腺癌術后調理中的重要性。
2 辨證論治
現代醫家對乳腺癌術后已經有比較系統深入的研究。孫貽安等[5]根據乳腺癌正虛邪實的特點,通過多年的臨床實踐,以扶正固本、化痰散瘀、解毒散結為原則治療乳癌術后患者,獲得了很好的臨床療效。陳麗珠[6]按照八綱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臟腑辨證辨別單證的方法,218例乳腺癌術后的患者共得到了402個單證證候,其中虛證證候為256個(占63.68%),虛癥以氣虛為最多。曾玉珠[7]選取了200例到廣安門醫院求診的乳腺癌患者進行調查, 在乳腺癌的中醫證型分布方面,調查結果顯示:患者剛手術后的中醫證型分布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氣血虧虛型(占54.6%),肝郁氣滯型(占26.2%),肝腎陰虛型(占13.1%),沖任失調型(占3.8%),脾虛痰濕型(占2.2%),氣陰兩虛型(占1.1%),血瘀癥(占0.5%)。楊格娟[8]選擇了2006年1月至2013年1月在新疆自治區腫瘤醫院的住院患者132例,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結果顯示術后乳腺癌中醫分型中脾虛痰濕證40例(占30.3%),氣虛血瘀證26例(占19.7%),氣血兩虛證36例(占27.3%),肝郁氣滯證30例(占22.7%)。
牛陽教授認為乳房為脾胃所司,足陽明胃經經過乳房,脾胃在乳腺癌的發生發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乳腺癌術后的病理變化多為脾胃失調的證候,術后脾胃虛弱,能影響津液的輸布,再加上肌膚絡脈損傷,局部氣血不暢,組織充血水腫,水液滯留,易發皮下積液及上肢水腫。乳腺癌腫瘤常侵蝕臟腑,臟氣虧虛,而欲生氣血則需要依賴脾胃受水谷、化氣血、布精微,脾胃調和,才能滋養其他臟腑。牛陽教授特別重視脾胃對元氣的滋養,在乳腺癌術后的治療上尤其強調脾胃后天之本的作用,以益氣健脾為基本原則,注意顧護術后病人的胃氣,從而達到恢復脾胃健運、人體正氣的目的。對于乳腺癌術后,牛陽教授主張在健脾扶正的基礎上隨癥加減,以減輕患者的臨床癥狀,增強其抗病能力,防止乳腺癌的復發轉移。
3 病案舉隅
3.1 病案1 張某,女,61歲,2018年12月14日初診。患者訴3月前于寧夏醫科大總院行左乳腺非特殊型浸潤性癌改良根治術,右乳腺纖維腺瘤術,子宮切除術,既往有甲狀腺右側葉結節,左腎囊腫。刻下患者神清,精神不佳,面色黑黯,惡心,乏力,睡眠差,入睡困難且易醒,二便正常。舌暗苔白膩,脈細略數。辨證為氣血瘀滯,脾失健運。治以補氣健脾,活血化滯為法。方以參苓白術散合保和丸加減。藥用:陳皮15 g,厚樸12 g,焦麥芽12 g,焦山楂12 g,焦神曲12 g,茯苓20 g,炒白術15 g,法半夏10 g,連翹10 g,萊菔子12 g,黨參12 g,炒山藥12 g,生薏苡仁30 g,炒扁豆12 g,當歸15 g,赤芍12 g,白芍12 g,川芎12 g,生甘草6 g。共7劑,每日1劑,水煎400 mL,分早晚服用。囑患者服藥期間清淡飲食,調暢情志,忌勞累,避風寒。
2018年12月20日二診,訴服藥后惡心、乏力較前明顯減輕,食欲尚可,睡眠尚可,二便正常。舌質紫暗,苔薄白,脈滑數。故沿用補氣健脾,活血化滯的治療法則,在原方基礎上減去生薏苡仁、炒扁豆,增加桃仁12 g,紅花10 g,香附12 g,郁金12 g,加強活血化瘀的力量。繼服7劑,服藥方法同前。
2019年1月10日三診:訴服藥后惡心、乏力明顯好轉,納可,睡中易醒,偶有口干、口苦,二便正常。舌質有瘀斑,苔薄白,脈弦滑。辨證為脾虛生濕,血瘀氣滯,治以健脾化濕,活血行氣為法。效不更方,在原方基礎上減去白芍、香附、郁金,增加藿香15 g,佩蘭15 g,茵陳12 g以芳香藥醒脾化濕濁,兼清濕濁郁積所生之熱邪。繼服7劑,服藥方法同前。
三診后患者繼續于門診圍繞著健脾益氣的核心間斷根據癥狀的變化調整用藥,堅持服用中藥湯劑,至第十二診時,患者幾乎已無任何不適癥狀,無乏力,納可,睡眠調,二便正常。面色黑黯好轉,精神狀態也恢復到較佳水平,已能投入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對戰勝病魔充滿信心。后續該患者仍于牛陽教授門診間斷調藥,至2020年7月撰寫該文之際該患者身體各方面情況都良好。
按語:本例患者系惡性腫瘤術后,因手術創傷較大,損傷氣血,術后患者精神不佳,惡心,乏力,眠差,這些癥狀都提示患者正氣已虛,脾氣不足,陰陽失衡。而這種不良的身體狀態也不利于防止轉移復發,不利于患者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牛陽教授認為脾胃者,土也。土為萬物之母,諸臟腑百骸受氣于脾胃而后能強。故治宜以補益脾胃為主,選用參苓白術散合保和丸加減以健脾益氣,促進運化,恢復正氣,抵御病邪,防止復發。因患者面色黑黯,舌暗有瘀斑,故以桃仁、紅花、香附、郁金、川芎活血化瘀,患者脾虛不運,濕濁郁而化熱,酌加藿香、佩蘭、茵陳化濁清熱。總體以健脾益氣為基礎,辨證論治,隨癥加減,療效明顯。
3.2 病案2 張某,女,65歲,2020年3月31日初診。患者訴5月前查出乳腺癌、甲狀腺癌,立即于寧夏醫科大總院行手術治療。刻下患者神清,面色少華,頭發缺乏光澤,自覺口干、口苦,乏力明顯,睡眠欠佳,納可,大便溏不成形,小便色黃。舌質暗,苔白膩,脈弦細。辨證為脾氣虧虛證。治以健脾益氣為法。方以香砂六君子湯合四物湯加減。藥用:炒白術15 g,黨參20 g,茯苓20 g,炒山藥20 g,陳皮15 g,木香12 g,砂仁后下10 g,黃芪30 g,當歸15 g,熟地黃20 g,赤芍12 g,炒白芍20 g,厚樸10 g,生甘草6 g。共7劑,每日1劑,水煎400 mL,分早晚服用。囑患者服藥期間清淡飲食,調暢情志,忌勞累,避風寒。
2020年4月7日二診,患者訴服藥后睡眠好轉,乏力減輕,口干、口苦緩解,現手足心熱,大便仍不成形。舌質暗紅,邊有瘀斑,舌苔根黃略膩,脈弦細。效不更方,沿用健脾益氣的治療法則,在原方基礎上增加炒扁豆15 g,連翹12 g,以化濕濁散郁熱。繼服7劑,服藥方法同前。
該患者門診以健脾益氣的治則為核心間斷根據癥狀變化調整中藥,治療3個月后,自覺不適癥狀有所恢復,精神、面色有所好轉。現繼于門診堅持治療。
按語:該案患者本就正氣不足,又因乳腺癌手術耗氣傷血,術后患者脾胃虛弱,氣血虧虛,治以健脾益氣為法,選用香砂六君子湯調理脾胃,益其生化之源。患者術中失血過多,故合以四物湯補血養血,促進機體功能的恢復。患者二診時出現手足心熱的癥狀,結合其舌脈的變化,究其原因其脾胃失于運化,濕濁郁久而生熱,故在原方基礎上增加炒扁豆、連翹以化濕濁散郁熱,體現了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療效可觀。
4 小結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手術作為乳腺癌現行的最佳治療方法,在切除局部病灶的同時,因其“峻攻”為害,往往會導致邪去正傷,以致經脈受損,脾胃虛弱,血絡瘀滯。而中醫藥可以調整臟腑陰陽平衡,增強機體免疫,降低乳腺癌術后并發癥,促進患者術后的恢復;還可以減輕乳腺癌化療、放療及內分泌治療所帶來的不良反應;而且在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存活率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9]。牛陽教授認為中醫治療乳腺癌術后應以扶正固本為大法,通過調理脾胃扶助正氣,正所謂正氣復而邪自安。處方應以藥效平和為要,慎防癌毒未散,胃又受到戕害。正如《活法機要》所言:“壯人無積,虛則有之,脾胃怯弱,氣血兩衰,四時有感,皆能成積。”“重視調治脾胃”的理念應始終貫穿于乳腺癌術后治療的始終,使脾胃重新恢復健運,則五臟得養,正氣得充,從而可以減少術后并發癥,抑制腫瘤的復發與轉移。
此外,辨證論治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牛陽教授還針對性地提出了乳腺癌臨床各期的治療原則。在乳腺癌早期多以肝郁氣滯為主,兼見脾虛痰濕、沖任失調者,治療宜疏肝理氣、健脾化濕、調和沖任,在此時正氣尚充,應當以攻邪為主。乳腺癌發展至中期時則多見熱毒內蘊、氣滯血瘀者,此時治療宜清熱解毒、行氣活血,這一時期正邪相互交爭,應當攻邪與扶正并舉。乳腺癌術后則多見脾胃受損、氣血兩虧者,治療宜補益脾胃、益氣養血為主,此時正氣漸虛,邪氣偏盛,當扶正為主,輔以攻邪。在臨床中應該遵循各個時期不同的治則,靈活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