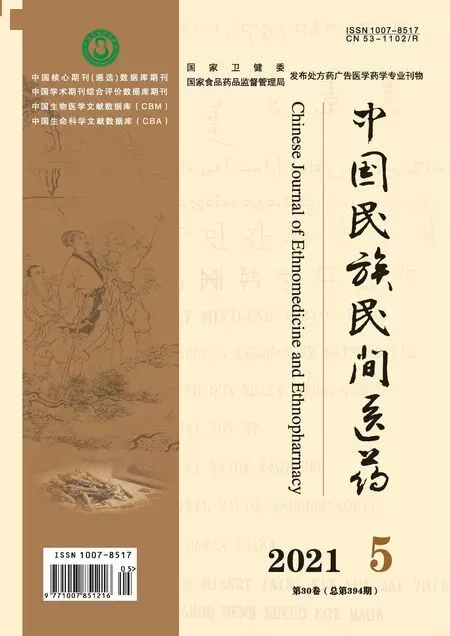敦煌醫學之養生論
孫 雪 梁建慶,* 李金田 李 娟 馬利芳 藺興遙 安耀榮
1.甘肅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敦煌醫學與轉化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00;3.甘肅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敦煌學是敦煌卷子顯世之后應用而興起的一門新的學問,敦煌醫學則是敦煌學中關于中醫藥的內容,在壁畫、彩塑、圖案、題記、書法及藏經洞大批遺書中都有大量記載和描繪[1-5]。筆者通過對敦煌醫學的探究,發現敦煌古代養生之道已有千年積淀,它以中國傳統哲學為理論基礎,融入了道家、佛家等宗教思想,集防治疾病、修身、煉養等為一體,貫穿古代先民生活的始終[6-7]。文章旨在通過對敦煌古代先民養生文化的探究,窺其現象本質,挖其內涵,汲取傳統養生文化精華為人類健康服務。
1 敦煌傳統哲學中的養生觀
“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氣者,必彰于物”(《素問·氣交變大論》)。人生于天地,長于天地,皆因一氣所生[8-9]。人與自然息息相通。敦煌醫理類著作《明堂五臟論》(P.3655)記載:“納陰陽而所生,成乾坤而所長。”[10]《張仲景五臟論》(P.2115)又載:“天地之內,人最為貴,頭圓法天,足方法地。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七星,人有七孔。天有八風,人有八節。天有十二時,人有十二經脈。天有二十四氣,人有二十四俞,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骨節。天有晝夜,人有睡眠。天有雷電,人有嗔怒。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地有泉水,人有血脈。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地有山石,人有骨齒。地有草木,人有毛發。四大五蔭,假合成身,一大不調,百病俱起。”以天例人、援物比類,可見古代哲學中對自然與人的重視。正是在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導下,敦煌古醫籍提倡適四時陰陽以保精氣的養生之道[11]。人與自然息息相關,立于天地間則必須順應天地,敦煌傳統哲學中雖未明確提出養生的概念,但從大量敦煌卷子記載的實用性可以窺探出醫理著作對此養生概念的鋪墊,人談及養生必與天地相關,正如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
2 敦煌遺書之食療養生
食療養生即利用食物來影響機體各方面的功能,使其獲得健康或預疾防病的一種長遠的養生行為[12-13]。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藥》載:“五菜為充,五果為助,五谷為養,五畜為益。”[2]此處不僅列舉了先民的飲食結構,更是指出飲食要做到營養充沛,膳食平衡,足見敦煌先民對于飲食養生的早期認識。這種飲食觀念是養生首當其沖要重視的。這也是最早的平衡膳食的記載,至今現代營養學仍無法超越[14-15]。繼五菜、五果、五谷、五畜的飲食結構之后,該書提出了五臟勞損的食療方劑,以食入方,藥食同用,符合調理養生。其遵循“以臟補臟”的原則來治療勞損,指出“補肝湯內加羊肝,補心加雞心,補脾加牛肉,補肺加犬肺,補腎加豬腎,各一具,即成也”[2]。雖遺書記載這種觀念是藥食同用,但這種以臟補臟的食療養生觀念已走入尋常百家[16]。
中醫學將食物或藥物分為寒、熱、溫、涼4種特性,基于人體質的不同應選擇相應特性的食物或藥物。敦煌遺書《食療本草》(S·76)記載了26種果蔬的特性,且附食療方劑64首。其中每種食物除注明四性之外,還記載了其主治、功效、服用禁忌等,部分食物還記載了產地、采摘季節等,可見敦煌先民對食物的透徹認識以及對藥食同用的重視。用食物之性,執食療之方,以求人和安康。這種食療養生的觀念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是敦煌西域先民對于養生的認識,同時也是他們對于食物自然特性的認可,可以說食療養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子。
敦煌遺書《呼吸靜功妙訣》(P·3810)云:“人生以氣為本,以息為元,以心為根,以腎為蒂……又偃臥榻上,少睡片時起來,啜淡粥半碗。不可坐(作)勞惱怒,以損靜功。每日能專心依法行之,兩月之后自見功效。神仙粥:山藥蒸熟,去皮一斤,雞頭實半斤,煮熟去殼,搗為末,入粳半升,慢火煮成粥,空心食之。或韭子末二三雨(兩)在內尤妙。食粥后用好熱酒飲三杯,妙。此粥善補虛勞,益氣強志,壯元陽,止泄,精神妙。”[2]此記載描述了呼吸靜功法與神仙粥同用達到“精神妙”的境界[17]。“神仙粥”主要成分為山藥,《神農本草經》將其列為上品,謂之“主健中補虛、除寒熱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耳目聰明”[18]。“神仙粥”可以說符合龔廷賢[19]的“固腎氣、保根本,調脾胃、養后天”養生思想。敦煌先民很早就認識到山藥入粥的養生方式,靜功與養生神仙粥搭配力求精神和[20-21]。這一觀念對研究飲食營養與養生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食療養生受到大眾青睞,借助自然果實以補生命所需,既保證營養又無藥物的毒副作用。敦煌遺書中對食物特性認識、論述以及入粥的方式都足以窺見先民對人和安康的追求,對于養生的重視。這對于后世食療養生是一筆寶貴財富,對于中國傳統養生體系形成有參考意義。
3 敦煌形象醫學之修身養生
敦煌形象醫學,即敦煌石窟中彩塑、建筑、壁畫中有關中醫藥的內容。尤以敦煌壁畫為多,展現了敦煌先民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對人和安康的養生追求。敦煌壁畫中發現大量練功、氣功、運動的畫面,展現了敦煌先民對古代運動養生重視[22-24]。
北涼第272窟西壁佛龕兩側的供養菩薩,兩側各畫四排小菩薩,每排有五身,共40尊。壁畫中每個菩薩表情不一,造型各異,均作坐姿,多有擰腰、側目、弄指、翹腳等動作,與印度養生瑜伽有異曲同工之處。40個小菩薩保留了四十個養生保健動作,尤以第一行中間菩薩為養生氣功典型,其兩掌向前上舉,掌心朝上翻轉,舒掌展指,頜部微微仰起,呈托球狀式,此舉意在通達經絡,陰陽相交,延年益壽。有學者[25]認為它是昔日佛門僧侶強身健體養生之法,是一種練身、練氣,動靜結合的健身養生法。張弘強等[26]依據此供養菩薩以及相關敦煌學的內容對敦煌石窟氣功—臍密功進行了論述。這種獨特的養生氣功方式不僅傳達古代先民對養生的重視的信息更是為后世留下養生氣功的寶貴財富。
坐禪是佛教獨特的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其通過調身、調息、調心,達到心神合一的狀態。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東頂南側的《禪修圖》,描繪了身披彩色袈裟的兩位高僧在綠意盎然的叢林間坐禪修身,兩人周身有動物圍繞,但依然盤坐自然,手結印契,坐禪瞑想,可見已經達到人佛合一的心境,與自然融為一體。自然萬物生生不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方可找到生命之源達到生命不息的境界。北魏第259窟禪定佛,其趺坐(雙腿盤坐),雙手相合貼于小腹置于腿上,挺胸抬頭,氣定神閑,定是收攝心神,元氣充實。這種靜坐身的養生方式在其他窟并不少見,如盛唐第79窟千佛及供養童子“坐禪”、盛唐第194窟彩塑菩薩“禪觀”等,均是以修習禪定的靜功,來達到強身健體、防病治病的目的。“精、氣、神”是人最重要的物質,坐禪可養精化氣,煉氣化神,強身健體,延年益壽[27]。這種坐禪的養生方式秉承著對生命的敬畏和鐘愛,凝聚著敦煌先民的生命價值觀,為中國傳統養生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宋第7窟東壁北側八塔變(第七塔)壁畫,描繪了一幅獼猴獻蜜圖,圖中一只獼猴正在歡樂跳舞,旁邊有一個赤裸身體的小和尚在模仿獼猴的舞姿動作,似猴拳。這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導引圖》[28]中部分模仿動物形態的導引動物有異曲同工之妙。華佗曰:“ 我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能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29]這種養生導引的方式,順應萬物以調形,通過感悟生命的精氣神、順應生命活動的自然節律, 進一步調節身心、舒血暢氣, 從而達到養生健體的目的[30]。
綜上,敦煌文化中養生內容融諸家之長,集身心一體,承對自然生命的敬畏與熱愛,對后世養生之道有參考意義。養生理論、食療養生以及形象醫學中的修身養生不僅利于后世人民對養生追求的多樣化,更是對于中國傳統養生體系的構建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