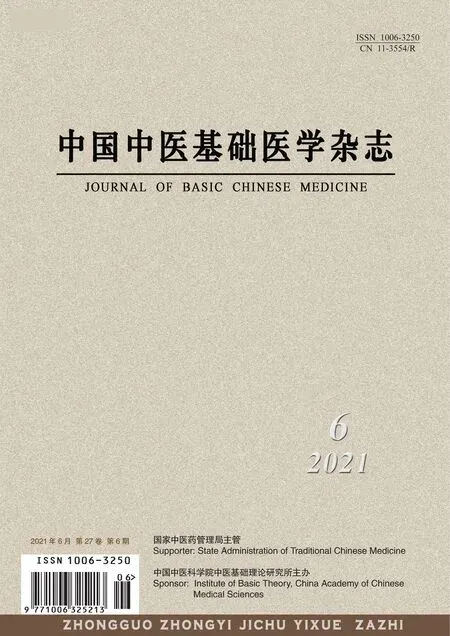河間學說與仲景思想關系探析?
王東琪, 梁尚華
(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 201203)
劉河間作為金元四大家之首,被后人稱為“寒涼派”創始人,亦是溫病學說的開辟者,后世學界對其評價褒貶不一。如張景岳批劉河間曰:“醫道之壞,莫此為甚”;然劉河間弟子張子和則認為:“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人而已”。本文認為,“河間學說”與“傷寒學說”二者理論觀點雖有差異,但絕非純粹的對抗與不可調和,深入探析二者間的臨證思想足可見其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
1 河間學說與仲景思想爭論聚焦
后世關于二者學術差異的探究聚焦于寒溫之爭,而其中有2個核心概念是構建寒溫之爭的基礎,即“傷寒”與“六經”,兩位先賢對這一對概念的認識有很大的差異,繼而導致寒溫之爭逐漸激化。究其原因,則在于劉河間對傳統的誤讀,即以《黃帝內經》理論附會《傷寒論》[1]。
1.1 對“傷寒”概念的認識差異
劉河間與張仲景對“傷寒”的理解有明顯差異,主要區別體現在對“傷寒即熱病”說及劉河間對“仲景傷寒”內涵的認識兩方面。
首先,劉河間對傷寒概念的理解遵循《黃帝內經》《難經》,并根據《素問·熱論篇》中的“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和《難經·五十八難》中“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認為傷寒與熱病系同一概念,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而張仲景所論傷寒僅為狹義傷寒:“以至仲景直言傷寒者,言外傷之寒邪也,以分風寒暑濕之所傷,主療不同。故只言傷寒而不通言熱病也。[2]”
河間學說開溫病先河,后世溫病醫家基于劉河間“仲景傷寒僅言寒邪”的觀點,進一步擴充了對溫病、熱病、濕病的論述,逐漸形成寒溫對立的局面。此中有2個問題需深入辨析,一為張仲景傷寒是否僅言寒邪,二為《黃帝內經》廣義狹義傷寒的劃分是否適用于《傷寒論》。
探究“仲景傷寒是否僅言寒邪”,實際上是從另一個角度回答傷寒溫病之爭的焦點,即“《傷寒論》可不可以指導溫病治療”。陸九芝明確提出:“陽明為溫病之藪”;王少峰于《傷寒論從新》寫到:“《傷寒論》為外感之專書也,善治傷寒者,必善治溫病。”陸九芝及王少峰均認為仲景傷寒不僅以寒邪論之,而且對一切外感病的治療均有指導作用。國醫大師裘沛然亦提出“傷寒溫病一體論”的重要學術觀點。其次,陳修園在《古今醫論》中說: “至云仲景《傷寒論》獨為傷寒而作,非治雜癥,試觀其中表里寒熱虛實陰陽諸法全備,雜癥俱可仿之為則,雖代有名賢雜癥諸書,不過引而伸之,觸而長之,誰能出其范圍,后學果能熟讀揣摩,則治雜癥思過半矣,推而廣之,并可統治男婦小兒一切雜癥。”《傷寒論》之法不僅可以治療一切外感熱病,亦包括內傷雜癥。現代傷寒大家劉渡舟便是“《傷寒論》傷寒雜病同治”的提倡者[3]。由此可見,《傷寒論》的實際診療范疇比劉河間理解得要廣得多。
此外,張仲景“傷寒”內涵與《黃帝內經》“傷寒”內涵亦有所不同。《黃帝內經》中“傷寒”是以病因名病,張仲景書中的“傷寒”是以癥狀名證[1]484。張仲景強調的是外邪作用在人體與正氣交爭的后果,而《黃帝內經》強調的則是具體所感的邪氣。這也體現出醫經、經方在診療上的不同思路:醫經以病因辨病為主,經方則以癥狀辨證為主。
綜上,劉河間對張仲景“傷寒”內涵的解釋與張仲景本意并不完全相符,因此不能認定張仲景“傷寒”僅論寒邪,借此忽視或者否定《傷寒論》對溫病理論的啟發。
1.2 對“六經”概念理解之差異
對“六經”的認識,各代醫家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劉河間與張仲景對“六經”辨識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是辨證對象的不同。劉河間云:“六經傳授,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2]487”他依據《熱論》中列出的六經病提綱以及“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的治則,表明六經辨證綱領是針對熱病的辨證方法,即三陽為表熱,三陰為里熱[4]。同時批駁了朱肱對三陰三陽的認識:“古圣訓陰陽為表里,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后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主張三陰三陽不該以寒熱劃分,當以表里劃分。劉河間認為傷寒三陰三陽是熱傳表里之別而非寒熱之異,而六經辨證綱領則是針對熱邪傳變部位的定位。
若僅憑劉河間這一理論就否定四逆輩在三陰病的主方地位,則會在臨床中犯下“寒者寒之”的錯誤。張仲景所論“六經”究竟當如何理解一直是千古難解的謎題,正如惲鐵樵所言:“《傷寒論》第一重要之處為六經,而第一難解之處亦為六經。凡讀傷寒者,無不于此致力,凡注傷寒者亦無不于此致力。”根據王慶國[5]等學者的研究,后世對于張仲景“六經”內涵的解讀至少有41種,包括臟腑說、經絡說、氣化說、六部說、病理層次說等。筆者認為,這些學說都可以體現張仲景“六經”的內涵,卻不能完全概括。事實上,張仲景的“六經”既包括寒熱亦融會表里——三陰三陽中各自有著表、半表半里以及里的分部,此即病位,而陰陽則為病性,寒熱虛實得另辨,因為錯綜相見[6]。傷寒大家萬友生[7]亦認為,張仲景所謂的“六經”不僅包括臟腑和經絡,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表現人體的氣化功能,可見張仲景所論“六經”并不局限于《素問·熱論篇》,而是比較全面的。張仲景的六經辨證理論包含了臟腑、三焦、八綱、病因、氣血津液等辨證方法,并非簡單的表里或陰陽可以概括。
其次是各經病證的不同。張仲景所言之“六經”,包含著“證候群”的概念而非簡單的名稱,在探討“六經”差異之時,必須要落實到癥狀上去。劉河間在《傷寒直格》[2]508中引用了《黃帝內經》 所述的六經辨證綱領:“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故身熱目疼而鼻干,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故胸脅痛而耳聾……四日太陰受之……故腹滿而嗌干。五日少陰受之……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陰受之……故煩滿囊縮。”可以看到,二者對于六經病證的認識差別主要集中于三陰病。此段話中,劉河間對于太陰病的認識更類似于《傷寒論》中的陽明病,而少陰病則接近于少陽病。故后世學者不可將二者所述六經名稱直接對應起來,而更應關注病名之下的具體證候。
柯韻伯謂:“仲景之六經,為百病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制。”俞根初亦言:“以六經鈐百病,為確定之總訣。[8]”張仲景的六經辨證體系是針對所有疾病的辨證方法,而劉河間“六經傳變皆是熱證”之說,更多的是向《黃帝內經》理論的靠攏,與張仲景“六經”有著較大不同。綜上所述,劉河間對于“六經”概念的闡發并不能體現出對《傷寒論》整體理論框架的理解,二者的“六經”概念更像是2個獨立成論的個體,不宜互參互釋。
1.3 依《黃帝內經》釋傷寒合理性探究
綜上分析,劉河間與張仲景對“傷寒”和“六經”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該差異也是后世溫病學派能夠突破傷寒、開辟溫病學說的基礎。在劉河間的闡述下,“火熱論”中的“熱”與《傷寒論》中的“寒”顯得格外對立,這是因為其慣用《黃帝內經》中的理論和概念去解釋《傷寒論》。
醫經、經方自古有別。《傷寒雜病論》源于《湯液經法》, 為經方派著作,而《黃帝內經》則為醫經派著作。明代學者俞弁在其論著《續醫說》中明確表示,醫經與經方學派有不同的理論來源:“原百病之起愈,本乎黃帝;辨百藥之味性,本乎神農;湯液則本乎伊尹”[9]。
后世認為張仲景著《傷寒論》時參考《黃帝內經》最重要的依據就是《傷寒論序》。而據學者楊紹伊考證,《傷寒論序》并非張仲景所撰,葉橘泉、錢超塵、李茂如等大家都對此考證評價頗高[1]。這一考證有力地否定了“仲景恪守《內經》理論”的直接證明。現代傷寒大家胡希恕更是大膽提出“仲景書本與《內經》無關”[10]的觀點。
綜上,“以內經釋傷寒”是值得商榷的,劉河間據此得到的相關學術觀點亦不可成為肯定火熱而否定傷寒的有力證據。看似激烈的寒溫之爭,實則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兩端,要明確2種學說之間的聯系,重點在于探究二者的臨證法則。
2 劉河間遣方用藥多遵循張仲景之法
劉河間首倡“火熱論”,用藥多為寒涼,其學術觀點和用藥特點更為后世溫病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然深入探究劉河間遣方用藥的特點,可發現其治法治則仍多遵張仲景之法,其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 倡寒涼而不避辛溫
劉完素雖為火熱論的創始人,但絕非“悉以實火言病”,更不是“用藥悉取寒涼”[11]。在臨床實踐中,劉河間對于辛溫藥物的運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如馮惟敏在《重刻劉守真先生宣明論序》中所言:“而近世傍求醫論,以謂熱病用河間,其亦就所重立言邪,可謂獨識其全矣。泛觀河間諸書,烏附等藥,亦多用之。[2]185”《黃帝素問宣明論方》[12]共載方劑352首,用附子之方21首,治療涉及虛勞、痰飲、痹證、下利、痛證、消渴、喑痱等多種病證。其中用丁香附子散治療脾胃虛弱之痞結吐逆,以及在痛證的治療中使用附子及烏頭,即是繼承了張仲景理中湯和烏頭赤石脂湯的思路。《宣明論方》全書中除藥性平和與寒熱并用方占66%外,偏于溫熱的占21%,而偏于寒涼的只占13%[13]。
在治療外感病方面,劉河間雖擅用辛涼藥物,但是對麻桂類方的價值是肯定的,并且在經方的基礎上處方而非自立門戶,這與后世“敬麻桂而遠之”的溫病醫家的做法有著本質區別。“傷寒無汗,表病里和,則麻黃湯汗之,或天水散之類亦佳”[2]516。一個“或”字,足以看出河間學說與仲景傷寒學說之間并非對峙的關系。劉河間將辛溫解表藥的治療機理解釋為“身熱惡寒,麻黃湯汗之,汗泄熱去,身涼即愈,然則豈有寒者歟”[2]331?這種解讀與傳統傷寒學派理論出入較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劉河間治火的特色并非單純的“熱者寒之”,而是獨具匠心的“火郁發之”[14]。
2.2 補充完善張仲景表里雙解之法
劉河間在《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2]378中說:“余自制‘雙解’‘通圣’辛涼之劑,不尊仲景法,桂枝、麻黃發表之藥,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其實早在張仲景書中,即有相當多表里雙解法的應用。表里雙解法是張仲景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解表攻里法、解表宣肺法、解表化飲法、解表清熱法、解表溫中法、解表和里法、解表通下法、解表利水法、解表清里法、解表止利法、解表和少法、解表助陽法[15]。相關方劑有大小青龍湯、葛根芩連湯、大柴胡湯、桂枝加大黃湯、麻黃附子湯、麻杏甘石湯等。《傷寒雜病論》[16]首創 “并病”與“合病”的概念,而且這一理論貫穿始終,是張仲景對六經辨證的補充。在表里兩經同病時即需要使用表里雙解法。劉河間在表里雙解法的運用中強調“火郁法之”的概念:“且如一切怫熱郁結者,不必止以辛甘熱藥能開發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蔥、豉之類寒藥,皆能開發郁結,以其本熱,故得寒則散也”。然而熱邪究竟是“怫郁于表”還是“怫郁于里”,劉河間對此的區分可能并不十分嚴格,但是可以肯定表里雙解法乃張仲景余緒。
2.3 寒涼攻邪不忘重視脾胃
張仲景在外感病及內傷雜病的治療中,祛邪之余注重扶正,時時不忘顧護脾胃,為后世醫家在重視脾胃以論治疾病方面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指導和方法。劉河間倡傷寒火熱病機理論,主寒涼攻邪,但在臨床中亦非常重視脾胃,對脾胃生理病理有著完整的認識,認為“土為萬物之母,水為萬物之源,故水土同在于下,而為萬物之根本。地干而無水濕之性,則萬物根本不潤,而枝葉衰矣”,而土之為病乃由于濕氣的過多或衰少,“水濕過與不及,猶地之旱澇”。劉河間指出脾胃之病的治療大法為“補瀉脾胃之本者,燥其濕則為瀉,潤其燥則為補”,在用藥方面承襲了許多張仲景的經驗。如在《黃帝內經宣明論方》[17]中,用藥頻次最高的前10味藥分別是炙甘草、茯苓、白術、人參、大黃、當歸、生姜、黃芩、木香和陳皮,并且高頻地出現人參和炙甘草、茯苓和白術、人參和茯苓、茯苓和炙甘草的藥物配伍。在治療中土不足時,炙甘草、茯苓、白術與人參亦是張仲景最為常見的用藥。又如劉河間創麥門冬飲子治療膈消證,方以麥門冬滋陰為君,輔以瓜蔞、知母、炙甘草、生地、人參、葛根益氣生津,這當中就包含了張仲景麥門冬湯、白虎湯等涼潤陽明之方的思想。劉河間雖然主張下法卻并非濫用下法之人,強調須得在有明確的里熱時才可以使用,否則就會“蓄熱內余而成結胸。或為虛痞,懊憹喘滿,腹痛,下利不止,發黃,驚狂,斑出,諸熱變證,危而死矣”[2]509,這與《傷寒論》中表證“誤下”成“壞病”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所以說河間學說并非悉取寒涼,其對于脾胃的重視往往被后世所忽略。
3 結論
河間學說深植于《黃帝內經》,在闡發張仲景理論時不可避免地引入《黃帝內經》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部分中醫名詞概念的歧義,給后世學者帶來理解困難。深刻認識此種差異,將有助于全面了解河間學說與張仲景思想的內在聯系,也有助于理解建立在河間學說基礎上的溫病學派與傷寒學派既非對立關系也非割裂關系。張仲景思想是河間學說的重要基礎,河間學說是張仲景思想的補充和發揮,這也證明學好經典對于梳理中醫各家學說的重要性。經典是教尺,是在浩瀚文書中為學者指引方向的燈塔。兩位先賢的思想都是寶庫,對于臨床實踐均有著獨特的優勢,只有摒除門戶之爭才能融會古今之說,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中醫藥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