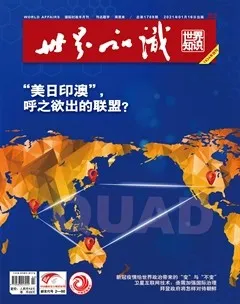脫歐后英國轉向“印太”,會掀起多大波瀾
張蓓

2020年11月30日,英國首相鮑里斯簽署《英歐貿易與合作協議》。
2020年12月30日,《英歐貿易與合作協議》正式生效,這也標志著脫歐過渡期結束,英國正式離開歐盟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徹底脫歐。與此同時,一種新冠病毒變種在英廣泛傳播,引發全球矚目。內外交困之下,英國仍試圖加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存在,宣布將派遣海軍船只前往中國南海,凸顯了脫歐之后英國外交的“印太”轉向。
“后脫歐時代”艱難開啟
2020年12月,英國再次成為國際關注焦點。首先是新冠疫情。一種新冠病毒變種被發現在英廣泛傳播,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再度執行嚴格管控措施。這一傳染性提高了79%的新冠病毒變種也引發了全球警覺,包括歐盟成員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紛紛采取緊急措施,暫停與英國的海陸空交通。在多國開始推行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戰勝疫情曙光浮現之際,英國出現的新冠病毒變種無疑為全球抗疫平添波折,而這也以殘酷方式凸顯英國在疫情大考中的較差表現。疫情也給英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統計,2020年英經濟將萎縮11.3%,預計將成為七國集團中受損最大的國家。
其次是脫歐。圣誕節前夕,英國和歐盟談判終于傳來好消息,持續了九個月的英歐貿易談判終于達成協議。然而如其樸實的名稱——《英歐貿易與合作協議》所示,協議最大意義在于避免了英國“無協議脫歐”的最壞結局,與建立“富有雄心”的貿易關系相距甚遠。協議僅對英歐貨物貿易做出無關稅、無配額的安排,就英國對歐的重要出口部門——服務業并無過多安排,在數據領域的保障也極為有限。從任何角度看,這都是一份“極簡主義”的協議。這份協議也意味著,英歐關系未來發展方向已經確定:經濟上,英國和歐盟將變成兩個不同的市場,具有不一樣的監管和法律空間。這勢必對雙方貨物和服務貿易產生障礙,也將阻礙人員跨境流動。據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估計,這些障礙或許在未來15年內使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損失5.2%。
疫情的延宕、脫歐的代價均說明“后脫歐時代”英國的前景難言樂觀。但結束了四年內耗,終于在一個極具分裂性、占據全部政治帶寬的議題上“過關”,英國政策精英終于可以騰出手來,將開啟脫歐進程來的口號、計劃、目標落到實處,在國內經濟領域“拉平地區差距”,在科學技術領域“成為科學超級大國”,在國內憲政關系上“維護堅如磐石的聯合王國”。而在對外關系領域,最響亮的口號則是“全球英國”,其走向也最引人關注。英國主動將安全、外交與防務排除在英歐談判之外,凸顯了其利用脫歐大幅度改變本國外交定位的雄心。在國際形勢加速演變、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英國作為歐盟外的歐洲大國、北約領軍國家、西方聯盟的忠實擁躉,仍保有豐富外交、安全、政治資源,其脫歐后的戰略選擇也值得關注。
轉向“印太”態勢明顯
從近幾年英國的舉動來看,脫歐后英國一個明顯戰略調整即轉向“印太”。近年來,“印太”成為受到多方熱捧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概念。這一概念“實體化”的趨勢也十分明顯,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紛紛加以推動塑造。歐洲國家也逐步接受了這一概念,并認可其所代表區域為未來國際秩序誕生的重要舞臺,認為應當盡早入局,搶得先機。其中動作較快的法國于2019年出臺“印太”安全報告,2020年9月德國政府發布“印太”政策指導方針,此后荷蘭也發布其“印太”戰略。法德荷三國“印太”戰略的出臺顯示歐盟正在積極醞釀歐洲“印太”統一立場。
盡管英國并沒有發布正式的“印太”政策文件,但英國近年來的布局和動作絲毫不遜于其他歐洲國家。英國轉向“印太”有充足的內部動力。脫歐已使英國在歐洲地區聲譽、信譽、好感度受損,因而英國希望能以“秩序守衛者”“同盟貢獻者”“公正調停者”“平等對話者”身份,在“印太”地區一展身手。英國的“印太”轉向也與英國脫歐“舍近求遠”的關鍵邏輯吻合,符合脫歐的“政治正確”。
英國自認為在“印太”地區仍有“帝國遺產”可資利用。英國曾在印度洋—太平洋一帶擁有廣闊的殖民領地,去殖民運動后也保留了一些“遺產”,如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的迪戈加西亞群島等英屬印度洋領地,地區內仍有多國將英女王視為國家元首,外交紐帶深厚。英國參與了地區很多歷史悠久的安全合作機制,如1941年成立的“五眼聯盟”(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國情報機構組成),1971年達成的“五國聯防”(包括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近兩年來“印太”話題在英國智庫界掀起熱烈討論,英國政府也有實際舉措。即便英國短時間內不出臺“印太”政策文件,其“印太”轉向的取向也已經十分清晰:這將是一個貿易、外交、防務結合的綜合性戰略。
貿易為重點。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英國”的原始內涵就包括在全球廣泛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恢復英國“偉大的貿易國家”的地位。加強與“印太”的貿易無疑是其重要方向,是英國在脫歐后拓展貿易網絡、彌補脫歐損失的關鍵。2020年10月英國與日本達成自貿協定,2020年12月與越南完成自貿協定談判,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自貿協定談判也在進行中。2020年6月,英國宣布將尋求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得到了部分成員支持。CPTPP被英國視作其貿易轉向“印太”的重要抓手。雖然經濟效益有限,英國希望借此打開“印太”服務貿易大門,并參與塑造地區經濟規則。

2020年12月15日,印度外長蘇杰生與到訪的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共同出席一場新聞發布會。
外交領域更為積極。在英國的外交機構內部,已新設置了“印太司長”,很快將搭建班子。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更建議要在英國國安會內設置“印太委員會”,并設置“首相印太特使”職務。近一年來英國在地區頻繁活動。2020年2月外交與發展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訪問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2020年9月訪問韓國與越南,2020年12月訪問印度。2021年1月首相約翰遜原計劃訪問印度,參加印度共和國日慶典,后因為疫情原因取消。英國也在積極爭取成為東盟的官方對話伙伴。此外,英國還試圖利用2021年擔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的機會邀請澳大利亞、印度、韓國參加七國集團峰會,為其提出的“民主十國”倡議做準備。
軍事領域更為活躍。英國加大了對中國南海干涉的力度,2016年英國戰機飛越中國南海,2018年9月第一次派遣“海神之子”號船塢登陸艦侵入中國西沙群島12海里領海范圍內,2019年1月英美在南海舉行首次聯合軍演,時任國防大臣威廉姆森更聲稱英國要在中國南海一帶建新軍事基地。2020年在英國公共財政受極大沖擊的背景下,英國國防部仍獲得165億英鎊的追加投資。這筆投資將主要用于支持英國在亞洲海域的行動。除了軍事部署之外,英國近年來加緊與地區國家達成軍事合作協議安排:2017年,與日本達成防務物流協定,與菲律賓達成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與越南達成防務相關合作諒解備忘錄;2018年,與新加坡達成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2019年,與印度達成防務設備備忘錄。
綜合來看,英國的“印太”轉向有兩大特點。第一,相較于法國偏向防務安全與德國偏向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英國是“軟硬兼施”,既追求商業利益,又要插手地區安全秩序。當下英國“印太”戰略的雙重性是對卡梅倫時代“重商主義”外交戰略的重要修正。第二,英國已有明確的地區合作伙伴,即依靠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印度等核心國家,并根據不同議題選擇合作對象。
英國需要找到本國地位
宏愿已經許下,布局也已到位,英國“印太”轉向能走多遠卻仍是一個關鍵問題。毋庸置疑,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七國集團成員的英國仍有可觀戰略資源,能夠在“印太”地區發揮一定影響力,但其天花板也十分明顯。
疫情凸顯英國的能力短板,脫歐則暴露了國際競爭下英國社會經濟模式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脫歐進程雖已結束,脫歐背后的推動力——如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并未消失。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隱憂與蘇格蘭、北愛爾蘭等歷史憲政問題都將對英國執政者構成長期挑戰。而若要展示轉向“印太”的“認真態度”,英國就需要將本已有限的資源持續投入這一與本土相距遙遠的地區,進而使其他方向的投入縮減。此外,英國對“印太”的設想和志向頗多,如為倫敦金融城找到新領域和新市場、在規則塑造上下先手棋等,但英國也要認識到自身能力資源有限的現實,其無法實現安全、經貿、國際合作等所有目標。
英國高估了自己在地區的受歡迎程度。英國當前的優先伙伴仍主要是英語圈國家,而以東盟為代表的地區力量對域外力量介入的態度則較為復雜。很多地區國家希望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維護“印太”的和平穩定。若英國介入只為攪局、拉偏架,注定不會得到廣泛支持。2020年11月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經濟貿易協定也將對地緣經濟產生重要影響,成功的地區一體化合作勢必將對域外國家介入形成門檻。
中美競爭是英國“印太”轉向無法回避的問題。而如何在中美博弈中找到本國定位已成為脫歐后英國外交的難題。在這方面,過去一年來英國傳遞出諸多混亂信號。在涉及美國打壓中國企業華為的議題上,英國屈服于美國的壓力;英還在涉港議題上多次發表錯誤言論,干涉中國內政;疫情后英國保守黨內的反華高潮也令中方警覺。然而,英國又多次表態其不愿在中美間“選邊站隊”。外交大臣拉布2020年9月在內部會議上表示英國要塑造格局,稱“未來并非只由中美歐三家決定”。這一態度遭到美國批評,認為英國試圖“率領一幫小國家搞針對兩大國的不結盟運動”。這些混亂信號說明脫歐后“全球英國”口號雖宏大好聽,卻不能直接回答英國當前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而在“印太”地區,若不能理順本國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的定位,英國的“印太”轉向也注定難以掀起大的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