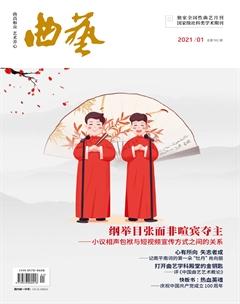相聲創作不能“短視”
孫晨
當前,短視頻在你我他之間傳來傳去,想躲都躲不掉。
有人說,從前的手機除了接打電話,什么都干不了;現在的手機只要換一塊核動力電池,基本什么都能干。特別是手機上的短視頻,更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睡覺之前,再看一眼;睡醒之后,手指一抖”,基本成了現代人的常規操作。
上班路上當旅伴、工作間隙當陪伴、吃飯時間當伙伴,短視頻閃爍間映照出的,其實是當代都市人時間的碎片化和生活的浮華化。人在緊張的生活節奏里,需要能“一笑了之”的消遣——也許明星、美食、時尚、美妝、旅游、動漫等短視頻還會有相對固定的受眾群體,但搞笑類短視頻的受眾面應該廣泛得多,對其他要把笑聲帶給受眾的藝術形式的影響力度也大得多。
所以,我們似乎應該要討論下搞笑短視頻與相聲,究竟孰勝孰負的問題。
相聲是笑的藝術,搞笑短視頻也追求“笑果”,但就目前的影響力而言,前者似乎不占優勢。“看看人家這‘包袱多好,比你們的相聲好玩多了。”甚至有些相聲從業者也慨嘆:“這相聲還怎么寫,這相聲還怎么說呀?”
我們不必這樣感嘆,但應該有些思考。
在短視頻流行前,一些時尚用語和流行笑話也會成為一段時間內的“流量擔當”,當時也有人說——“看這個,比你們說的相聲有意思”,有些相聲演員也要“緊跟時代”,或主動或被動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塞上幾句,好像不這樣做就落伍了一樣。但現在看來,時尚真的就在那“一時之上”。繁華過后,只有一直被說“越來越沒意思”的相聲還立在舞臺上,翻翻過去的記憶,可能還會在相聲的某個節點上看到哪一年的時尚用語,然后我們恍然——“原來那年流行的是這個啊!”
就此而言,相聲作為一種經過歷史考驗、實踐檢驗的成熟藝術結構,天然就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延展性,能在保證自我藝術規律的前提下“化他為我”,有效提升自身的豐度。無論是“年度金句”“流行語言”還是當下的搞笑短視頻,與相聲都是沒有可比性的。如果說一定要在兩者間找到連接點,那我們相聲從業者也可以很自信地說,搞笑短視頻中的許多致笑手法都來源于相聲藝術。
將搞笑短視頻還原為相聲腳本,頂多就是一個具有“三番四抖”完整結構的包袱,或者只是一組“吃了吐”的重復組合,或“先褒后貶”,或“先貶后褒”,在經過夸張、反轉、裝傻等表現方式后,最終完成一個“搞笑”的簡單動作。但就是這一點連接,一方面讓相聲藝術被無意識地矮化——因為搞笑的“程度”不夠;一方面又在悄然侵蝕相聲的藝術肌理,混淆受眾對相聲的認知,在無形中消減相聲的藝術影響力——這在部分相聲演員看到短視頻在贏得受眾方面的巨大潛力時變得更為嚴重。
對此,相聲從業者要保持足夠的藝術定力。
相聲的創作規律和組織包袱的手法被搞笑短視頻或有意或無意地合理利用,是相聲藝術影響力的重要證明,相聲從業者對此以平常心看待的同時,還要充分認識到相聲藝術的本質。
相聲是一種讓人發笑的曲藝形式,它的全部藝術魅力都來源于對生活的反映、對社會的記錄,這意味著相聲的“笑果”不應是也絕不能是無根之木、水面飄萍,而是演員與觀眾在同感融情共鳴后的結果。相聲的笑不應該像某些搞笑短視頻一樣,是無底線的發泄、無原則的“審丑”、無節制的“耍笑”的混合物,如果放任相聲藝術被風行一時的搞笑短視頻所裹挾,那將是相聲藝術的悲劇。
一段相聲一定是一個完整的藝術作品,相聲絕對不能碎片化。《紅樓夢》是文學經典,但被撕成無數碎片的《紅樓夢》就只能是支離破碎的“沖盹兒”,不再具有“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后“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藝術感染力。同樣的,如果我們把一段完整的相聲,無節制沒追求地切碎并制作為無數的搞笑短視頻,那就是自毀前程。
短視頻可以精制濫造,相聲藝術不行;短視頻可以張口就來,相聲藝術不行;短視頻可以“只為一樂”,相聲藝術不行;短視頻可以一笑了之,相聲藝術不行。
每一個相聲從業者都要秉持“相聲好不好,笑聲最重要;相聲出成果,關鍵在創作”的觀念,始終在娛樂的亂流中保持自我,用心創作精品力作。
相聲是有傳統有傳承且歷經幾百年時代變遷考驗的藝術形式,根系深扎在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樂群眾所樂,頌群眾所感,諷群眾所惡。在發展新、理念新、格局新的新時代,相聲藝術要緊跟時代,用笑聲記錄火熱生活的同時,引領笑的藝術向更高的層次進步發展。
為此,相聲從業者要聚焦火熱的生活,從生活的海洋中捕撈靈感、收獲素材。而不是想著走“終南捷徑”,一味從搞笑短視頻中尋找素材。縱觀前輩藝術家們留下的經典相聲作品,每一個優秀橋段、每一個經典包袱、每一行雋永金句,都能在火熱的生活當中找到出處和依據。生活才是藝術創作的動力,生活才是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的源泉。
20世紀70年代末,馬季先生的相聲《白骨精現形記》《舞臺風雷》火遍全國,但他沒有在掌聲和贊許中享受安逸,而是堅持走進基層,在人民群眾中體驗生活,“從生活中去找相聲”。為創作新作品,馬季曾帶著還在度新婚蜜月的姜昆先生離開北京,下沉到湖南桃源縣體驗生活。他們一邊采訪體驗一邊用心創作,但在春節前還是沒能寫出滿意的作品。他們商量后決定,不回北京過春節,就留在桃源縣。他們到水利工地去采風,找縣里的干部聊天,采訪農村青年,過了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春節。最終,他們帶去的是白紙,帶回來的是作品。《新桃花源記》的影響自不必說,姜昆創作的《迎春花開》是特殊歷史時期后文藝舞臺上第一段歌頌農村青年追求崇高愛情的相聲作品。這兩個作品成了詮釋那個火熱年代的最佳注解,是藝術家對生活的的致敬,更是生活對藝術家真誠付出的回報。
只論一點,可見其余。哪個藝術家輩出、好作品井噴的年代都并非偶然,而是相聲從業者實打實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提煉生活后的必然結果。當代的曲藝創作者也在充分繼承這一優良傳統,但火候可能稍差。
現在一些采風活動,大都是“乘風而來,隨風而去”,往多了說,在一地“瀏覽”個三天五日;再少些,下車一看一轉一拍照也不是沒有。在碎片化的時間中抻出像模像樣的作品,似乎頗有創作搞笑短視頻的“自覺”。
還有一些更“忙”的作者,連“乘風而來,隨風而去”也做不到了。為了出活兒,就守著電腦碼字,在網上搜笑話,在手機里找靈感,到搞笑短視頻里找笑料。這種本末倒置的創作,很難創作出接地氣、有生活的優秀作品。這不是在嚼別人嚼過的饃,這是在嚼別人吐掉的饃。
盯著電腦找素材,盯著手機找包袱,感受不過丈許,目光只以尺計,在杯水中起風波,于螺螄殼中做道場,這樣創作出的作品可能風靡一時但不可能傳于后世。只有把探索的目光投向生活,我們的可視空間才能達到無限。只有深入生活,腳踩豐饒的土地,創作者才能找到施展藝術才華的無限空間。
創作不能抄近路,創作不能走捷徑。搞笑短視頻里沒有真正能打動人心的創作靈感和素材,一味坐在電腦前也無法找到創作的正確道路。
當代相聲從業者要繼承優良傳統,要學習傳統的精華,要掌握傳統相聲的創作技術和技巧,不能隔著屏幕看生活,在“亂花漸欲迷人眼”中失去了自己的創作。新時代的相聲從業者要認真學習,在前輩藝術家留下的經典中去尋找創新的動力。
被如何在生活中尋找素材的問題所困擾,那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理解生活的真諦。我們每天都在生活,我們就是生活中的一分子。寫不出今天的精彩,是我們還沒有解決“心入”的問題。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做有“心”人,那我們每時每刻都是在體驗生活。
生活是豐富繁雜的,我們平時就要用心在生活中去尋找精彩的“零配件”并將之收藏在大腦中做庫存,這就是積累和財富。當進行創作時,這些從生活中提取存貯的“生鮮”就會跳出來自動組合排列,生成新的人物和新的藝術形象。有了人物,還要營造這些人物藝術化的生存環境。如此,人有了,景也搭好了,再加一點藝術化的“編織”,故事也就自然發生了,作品也就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如此構成的創作序列,才是來自生活的、有生活依據的,才是能真正體現創作者自我風格的。
由此可見,相聲作者的目光不能短淺,相聲藝術創作的實踐也沒有捷徑可走。“身入”生活是體驗生活的表面現象,“心入”生活才是真正和生活對話。只有遵循藝術規律,只有真正地走進生活,只有踏實地向生活學習,只有用生活充實頭腦,才會在創作時有所突破,才能在創作時有所創新,才能生產出優質的 “藝術笑果”。
相聲作品可以有意識地以短視頻為載體,但相聲創作不能“短視”。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