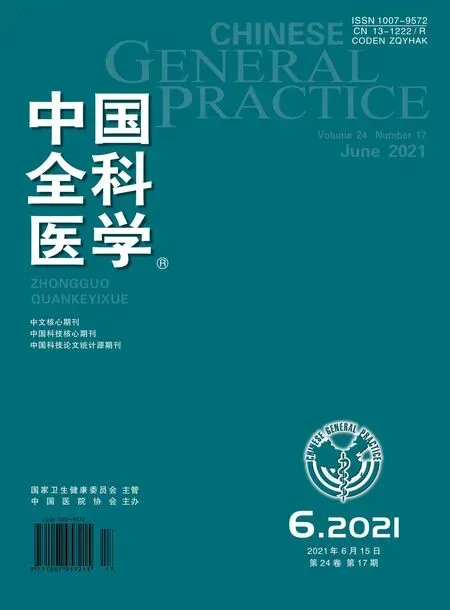老年人藥源性腎損害的原因及全-專聯(lián)合預防策略的探討
魏珊,劉英莉
本文創(chuàng)新點及不足:
(1)創(chuàng)新性:本文在“醫(yī)聯(lián)體”背景下提出老年人在共病狀態(tài)下用藥安全的全-專聯(lián)合管理策略,明確全科醫(yī)師和專科醫(yī)師在此管理模式里扮演的角色,有助于全方位、多層次管理老年人安全用藥問題、避免藥源性腎損害。同時對于慢性共病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及自我管理具有借鑒意義。
(2)不足:對于加強全-專聯(lián)合管理仍需進一步探索細化措施,并進行相關臨床研究。
隨著社會發(fā)展及醫(yī)療水平的提高,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全球60歲及以上的人口(10.49億)約占總人口的12.8%[1],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8.1%[2]。隨著老年人的生理機能減退及體內多系統(tǒng)穩(wěn)態(tài)失調,老年人慢性病及慢性病共病的患病率隨之上升[3],多重用藥愈發(fā)常見。且由于老年人視力、記憶力減退,依從性差,潛在的不適當用藥(PIM)也隨之升高,極大增加了老年人藥物不良事件(ADE)和藥物不良反應(ADR)等相關用藥問題的風險[4]。由ADE和ADR所致的藥源性腎臟病稱為藥源性腎損害(durg-induced renal injury)或藥物相關性腎臟病(durg associated renal disease)。老年人常伴隨生理性腎功能衰退[5],藥物轉運、代謝及清除能力也隨年齡增長而減弱[6],因此老年人極易發(fā)生藥源性腎損害。本文通過研究老年人特殊的生理病理及藥代學、藥動學,明確老年人易發(fā)生藥源性腎損害的原因,根據(jù)老年人特殊的臨床用藥特點提出針對性的預防策略,建立全科-專科聯(lián)合管理的新模式,加強老年人在共病狀態(tài)下多重用藥的安全性及安全用藥的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對提高老年人用藥安全意識、減少老年人ADR及ADE發(fā)生率、預防藥源性腎損害有重要意義。
1 藥源性腎損害概述
多數(shù)研究將藥源性腎損害定義為:有至少24~48 h藥物暴露史,血清肌酐在24~72 h內較基線水平升高0.5 mg/dl或升高了 50%[7]。
1.1 藥物所致的急性腎損傷(AKI)臨床表現(xiàn) AKI大部分表現(xiàn)為腎實質性AKI,小部分可為功能性(腎前性)或梗阻性(腎后性)AKI。累及腎小球或微血管時可出現(xiàn)急進性腎炎綜合征、腎病綜合征、小血管炎或血栓性微血管病[8]。藥物引起的AKI占全部AKI的8%~60%[9-10]。老年人藥源性AKI發(fā)生率占所有老年人AKI的10%~65%[11-18],社區(qū)環(huán)境中老年人藥源性AKI(CA-AKI)發(fā)生率占所有老年人AKI的19%~54%[9,19]。藥物導致的慢性腎損害常在長期持續(xù)或反復間斷用藥后緩慢起病,可表現(xiàn)為逐漸出現(xiàn)多尿或夜尿增多、電解質紊亂(如慢性低鉀血癥)、腎性貧血、腎小管酸中毒和慢性腎衰竭等[8]。
1.2 藥源性腎損害機制 藥物可通過以下機制分別或共同作用導致腎損傷:(1)直接腎毒性[20]:藥物及其代謝產(chǎn)物通過有機離子轉運蛋白在近端小管濃縮和重吸收的同時大量聚集[21],導致近端腎小管上皮變性壞死,腎小管基底膜斷裂[22],可表現(xiàn)為急性腎小管壞死或急、慢性腎小管間質疾病。(2)免疫炎性反應[23]:藥物及其代謝產(chǎn)物等外源性抗原或壞死的腎小管上皮等內源性抗原可誘發(fā)免疫反應導致腎損傷,可表現(xiàn)為腎小管間質性腎病、腎小球疾病。(3)腎小管梗阻[24]:藥物或其代謝產(chǎn)物濃度升高后析出大量晶體鹽類物質阻塞腎小管,導致腎小管功能障礙,主要表現(xiàn)為急性腎小管壞死。還有一些藥物可引起溶血或橫紋肌溶解,產(chǎn)生的內源性物質(血紅蛋白或肌紅蛋白)阻塞腎小管的同時也會通過影響腎內血流動力學及細胞毒性作用而損傷腎臟。(4)腎缺血性損傷:某些藥物通過減少循環(huán)血容量或收縮腎血管引起腎血流量下降,進而引起腎臟組織缺血缺氧性損傷,嚴重時可發(fā)生AKI。(5)其他:有文獻報告環(huán)孢素、他克莫司、雌激素、絲裂霉素、奎尼丁等藥物可導致溶血尿毒癥綜合征,其機制可能由上述多種因素參與[25]。
1.3 藥源性腎損害危險因素 藥源性腎損害危險因素有[26]:(1)患者方面:年齡、性別、伴隨疾病(慢性腎臟疾病、腎血管疾病、糖尿病、充血性心力衰竭、肝硬化、敗血癥、多發(fā)性骨髓瘤、酸堿紊亂、低蛋白血癥)、既往過敏史。有研究發(fā)現(xiàn),在低血容量的患者中46%出現(xiàn)氨基糖苷類抗生素腎毒性,而無低血容量者僅為6%[27]。(2)藥物方面:藥物本身的腎毒性、給藥時間、給藥途徑、給藥頻率、用藥劑量、治療時間、藥物間的協(xié)同效應等。如氨基糖苷類抗生素一般用藥7~10 d腎毒性最強,而利福平則常見于停藥后再次使用或在間歇治療時,正常劑量下數(shù)小時至數(shù)天即可出現(xiàn)嚴重過敏反應,甚至AKI[27]。當存在危險因素時應盡量避免用腎毒性藥物,并尋找替代療法。如果必須使用,則應提前積極糾正易感因素,調整用藥劑量、延長用藥間隔時間、縮短療程,同時應密切監(jiān)測患者腎功能變化,對老年人及原有腎功能不全者可監(jiān)測早期腎損傷指標變化。一旦發(fā)生腎毒性損害,應及時停藥,必要時輔助激素治療。大多數(shù)抗生素的腎毒性在停藥后可以完全恢復,少部分則可能出現(xiàn)不可逆性的腎損害。
2 老年人易發(fā)生藥源性腎損害的原因
2.1 腎臟易感性及生理性腎臟結構和功能減退 腎臟由于以下原因易受到藥物損傷:(1)腎血流量(RPF)占靜息心輸出量的20%~25%,這使腎臟易接觸更多的循環(huán)藥物;(2)腎小管的濃縮功能使腎臟暴露于更高濃度的藥物中;(3)腎小管上皮細胞、內皮細胞及腎內毛細血管的表面積大,易發(fā)生抗原-抗體復合物的沉積;(4)轉運蛋白尤其有機陰離子轉運蛋白(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s,OATs)可進一步增加藥物的濃度[28];(5)腎臟耗氧量大,對缺血缺氧敏感,影響血流的藥物容易引發(fā)腎損傷。
健康人40歲后腎血漿流量(RBF)降低。從20~90歲,其降低幅度可達50%,腎小球濾過率(GFR)則以每年0.75~1.05 ml/min的速度遞減,合并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GFR下降速度更快[29-31]。有研究發(fā)現(xiàn),31%~49%的健康老年人的GFR<60 ml/min,70歲以上的老年人高達50%[32]。這些變化可能會增加腎臟對藥物損傷的敏感性,因此老年人易發(fā)生藥源性腎損害。
2.2 年齡相關的藥物代謝動力學和藥物效應動力學變化 與年齡相關的生物學和生理變化可能導致藥物代謝動力學和藥物效應動力學改變。藥物的敏感性及耐受性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
2.2.1 藥物代謝動力學改變 藥物代謝動力學改變包括:(1)吸收:與年齡相關的生理變化可能會引起藥物吸收的變化[33],老年人胃壁細胞功能降低,胃酸分泌減少[34],胃內pH值的改變會影響藥物的解離度,進而影響口服藥物的吸收量,胃排空及胃腸蠕動減慢、胃腸血流量減少、小腸表面積縮減、消化液及各種消化酶分泌減少[34],可直接影響藥物在胃腸道內的停留時間和吸收速率,而組織血流灌注減少會影響皮下、肌內和透皮給藥的吸收率。(2)分布:藥物與血漿蛋白的結合、體液pH值和藥物理化性質、局部器官血流量、組織親和力及體內屏障(如血-腦脊液屏障等)均能影響藥物在體內的分布[35]。患有慢性疾病和營養(yǎng)不良的老年人血漿蛋白濃度顯著降低,導致結合型藥物血藥濃度降低,游離型藥物血藥濃度相對升高,藥理活性增強,進而可能增加其毒性。同時使用多個血漿蛋白結合率高的藥物時,由于競爭置換或藥物結合達到飽和,游離型藥物濃度增大,也易產(chǎn)生毒性反應。老年人心室舒張功能障礙,心輸出量逐漸下降[36],局部器官血流量減少,影響藥物到達靶組織的濃度,從而改變藥物效應。隨著年齡增加,體液總量減少,而體內脂肪量逐年增加[37],尤其在老年女性中更明顯[38]。老年人體液量的減少會導致一些水溶性藥物(例如鋰、地高辛)的表觀分布容積(Vd)減小[39],血藥濃度增高,而脂肪增加可使脂溶性藥物(例如地西泮)的Vd增大,藥物在脂肪組織中蓄積,增加ADE和ADR的發(fā)生。(3)代謝:肝臟是藥物代謝的主要場所。隨著年齡的增長,肝臟的質量和灌注量逐漸下降[40],在老年人中肝臟血流量下降40%~60%,高度清除藥物的肝臟首過效應(first pass effect)可能會降低,某些藥物的生物利用度(bioavailability)可在老年人中增加,而某些藥物的肝臟藥物清除率在老年人中最多可降低30%。肝酶尤其是細胞色素P-450(CYP450)活性降低[41],會導致藥物代謝減慢、作用時間延長、毒性反應增加[42]。另外,藥物代謝速率存在個體差異,需因人而異調整用藥劑量。(4)清除:腎臟是清除藥物的主要器官,主要通過腎小球濾過、腎小管被動重吸收、腎小管主動分泌清除藥物。老年人的腎臟組織、腎血流量、GFR和腎小管分泌功能等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29-32],那些主要由腎以原型排出的藥物或腎毒性大的藥物的t1/2在老年人體內明顯延長,進一步影響藥物在體內的濃度和機體清除藥物的時間,使藥物效應增強或ADR增加[42]。
2.2.2 藥物效應動力學改變 由于各系統(tǒng)的穩(wěn)態(tài)儲備減少,酶活性下降,受體親和力降低,內環(huán)境調節(jié)紊亂,老年人對藥物的敏感性增加。研究表明,老年人對藥物的感受性和耐受性與年輕人相比有顯著差異[43]。老年人的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對苯二氮類藥物(地西泮、硝基安定)的敏感性增加,老年人對異丙腎上腺素、沙丁胺醇和普萘洛爾敏感性不同于年輕人。服用血管擴張劑時,老年人直立性低血壓的風險更大,對華法林的反應也更敏感。因此,老年人的藥效反應個體差異較大,更容易發(fā)生ADR。
2.3 多重用藥 多重用藥主要根據(jù)藥物種類(≥5種)或藥物應用是否屬于臨床需要而定義。高齡、一病多藥和共病多重用藥是ADR和藥物-藥物相互作用(DDI)的潛在危險因素,其發(fā)生頻率隨用藥種類及持續(xù)時間的增加而增加[44]。
ADR、DDI、藥物-疾病不良相互作用可使藥效下降、藥物毒性增加,進而增加組織損傷及死亡風險。在中國,≥75歲老年人中長期服藥≥3種者占28.9%(n=3 448)[45]。國內各門診患者平均用藥3~7種,存在PIM發(fā)生率為26.33%~57.54%,住院患者平均用藥7.71種,存在PIM發(fā)生率約為43.00%[27,45-48]。在國外,≥65歲的老年人中約39.9%的老年人服用5種及以上藥物,且服用≥10種藥物與年齡增長密切相關(20~29歲占0.3%;≥80歲占24.0%)[49-50]。因ADE就診的老年人(≥65歲)分別占所有門、急診ADE就診者的34.7%和23.0%[51]。在住院患者中ADR發(fā)生率約為15.1%,其中嚴重ADR的發(fā)生率約為6.7%,致命ADR的發(fā)生率約為0.32%[52]。該人群死亡風險約增加了2倍[53]。ADR因此成為致死原因的第五位[54]。
2.4 老年人用藥行為 用藥行為主要取決于服藥者的藥物認識和應對方式。多重用藥、抑郁、衰弱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下降的老年人依從性差[55],家庭人均月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接受過安全用藥教育、由醫(yī)院獲取藥物、既往有不良反應史及有照料者是保護性因素,高齡、患慢性病及用藥種類較多是危險因素[56]。我國老年人安全用藥知識缺乏,存在漏服或錯服藥品、吃過期藥、自行購藥、自行增減藥量或停藥、聽信廣告購藥及認為藥越新越貴越好等不規(guī)范用藥情況,對于閱讀說明書、檢查有效期、醫(yī)生診斷后用藥、了解ADR及DDI相關知識、滋補保健藥品也會發(fā)生ADR的認知情況也不樂觀[56]。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計,因不合理用藥行為而導致住院患者發(fā)生ADR的比例為10%~20%,其中5%的患者因嚴重的ADR而導致死亡[57]。
3 全-專科聯(lián)合對老年人藥源性腎損害的預防策略
隨著中國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推進,全科醫(yī)師在實現(xiàn)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的實踐探索中愈發(fā)重要。通過社區(qū)與綜合醫(yī)院開展醫(yī)療聯(lián)合合作,建立全科-專科聯(lián)合管理的新模式,強化診治過程中的合作,優(yōu)化治療流程,共同構建醫(yī)療信息平臺,實現(xiàn)健康檔案、實驗室檢查等資源共享,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共病狀態(tài)下多重用藥的安全性,加強患者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預防老年人藥源性腎損害的發(fā)生。
3.1 醫(yī)師是基礎
3.1.1 全科醫(yī)師在首診時應全面分析病史,根據(jù)患者主訴及常見老年綜合征發(fā)散性提問,如睡眠情況、大便頻率及性狀、是否頻繁起夜等,是否使用藥物助眠、通便等,盡可能準確記錄服藥種類、劑量及時間,同時判斷出治療疾病的主要藥物、輔助治療藥物、不必要的藥物及可能產(chǎn)生ADR的藥物,建立SOAP(Subjective-Objective-Assessment-Plan)門診藥學病歷[58],同時充分運用計算機信息技術建立數(shù)據(jù)庫[59],提供簡明可靠的藥物信息與藥學監(jiān)護,協(xié)助專科醫(yī)師監(jiān)測藥物療效和ADR,及時調整用藥方案。
全科醫(yī)師應至少每3個月對老年共病患者進行1次隨訪。隨訪內容包括:查看患者血糖、血壓等慢性病控制監(jiān)測指標記錄冊,詳細詢問患者近期癥狀、用藥情況及有無ADR相關癥狀。根據(jù)慢性病控制情況分類干預:對慢性病控制良好、無ADR、無新發(fā)并發(fā)癥或原有并發(fā)癥無加重的患者,預約進行下一次隨訪;對控制不佳或出現(xiàn)ADR的患者轉診到專科門診處由全科-專科聯(lián)合診治共同管理,并定期復診;對聯(lián)合管理仍控制不佳及出現(xiàn)新的并發(fā)癥或原有并發(fā)癥加重的患者可通過醫(yī)院的雙向轉診綠色通道直達醫(yī)院住院,出院后轉回社區(qū)醫(yī)院管理。
3.1.2 專科醫(yī)師在用藥前應查看患者SOAP門診藥學病歷,因人而異選擇合適的藥物種類、劑量、用藥時機,盡量采用非藥理學干預措施,避免過度用藥,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根據(jù)藥物治療方案風險評估和減緩策略藥物治療方案風險評估選擇藥物療效佳、ADR少的最優(yōu)用藥方案[60],避免多藥合用。具體包括:(1)藥物種類:需考慮慢性病共病時聯(lián)合用藥可能引發(fā)的藥物相互作用以及長期用藥可能引發(fā)的患者依從性差的問題,精簡藥方,安全用藥。(2)用藥劑量:宜從小劑量開始,逐步過渡到最適劑量。根據(jù)中國藥典相關要求,>60周歲的老年患者用藥劑量是常規(guī)劑量的1/2~3/4[61]。對于經(jīng)腎臟排泄和治療指數(shù)窄的藥物要根據(jù)血藥濃度調整給藥劑量和次數(shù)。(3)用藥時機:需綜合藥物t1/2及老年人生物節(jié)律機制合理選擇給藥時機,以便于增強藥物療效,降低ADR。(4)特殊藥品:在使用麻醉藥品、精神藥品、醫(yī)療用毒性藥品和放射藥品時,應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的管理規(guī)定實行特殊的處置方法,對老年人更應把握特殊藥物如安眠藥的使用,避免ADR的發(fā)生。
專科醫(yī)師在用藥期間應定期監(jiān)測患者生化指標,還可參考老年人健康用藥的輔助工具,如Beers標準、老年人不恰當處方工具(IPET)、老年人潛在不恰當處方篩選工具(STOPP)[60],并借助評估量表(如單維度藥物素養(yǎng)評估量表、諾氏評估量表、風險評估數(shù)字量表等),評價治療效果及PIM情況,及時調整用藥方案。如使用腎毒性藥物時應定期檢查腎功能,使用治療指數(shù)窄的藥物時應進行血藥濃度監(jiān)測。
對于已經(jīng)發(fā)生的藥源性疾病要及時總結經(jīng)驗教訓,專科醫(yī)師應詳細記錄發(fā)生原因、臨床表現(xiàn)、治療方案、治療效果,提醒全科醫(yī)師注意隨訪監(jiān)測,避免此類藥品ADR的再次發(fā)生。及時從全科醫(yī)師及患者用藥記錄中得到用藥反饋,對存在潛在危險性的藥物或長期服用后治療效果不明顯的藥物進行調整。
3.2 患者是關鍵 患者是用藥的主體,其用藥依從性是保障臨床用藥的科學性及準確性、預防藥源性腎損害的關鍵[57]。研究表明,接受過安全用藥教育的老年人用藥依從性高,因此無論全科醫(yī)師還是專科醫(yī)師均應注重加強老年人安全用藥教育,消除用藥誤區(qū),提高健康素養(yǎng),規(guī)范用藥行為[56]。
3.2.1 全科醫(yī)師應采用多種形式加強老年人安全用藥的宣傳教育,包括:(1)發(fā)放用藥安全教育材料(如講義、視頻節(jié)目等),不定期開展專題講座、有獎問答、提供免費的血壓和血糖測量的同時進行宣教等活動[55],從用藥原則、注意事項、常見誤區(qū)、家庭儲藥注意事項、ADR以及預防措施等方面對慢性病老年人給予健康教育[62],指導老年人及家屬學會家庭血糖、血壓監(jiān)測并記錄;(2)通過多種途徑提醒老年人用藥行為:如在高危患者的處方袋上貼上亮眼的筆記,向患者提供簡單的用藥安全教育提示列表,推薦記憶力、視力不佳的老年人使用貯藥盒[63],保證定時定量服藥,發(fā)放如“按時用藥”等趣味的提醒卡片給老年人貼于家里醒目位置。
3.2.2 專科醫(yī)師應針對患有不同疾病的患者開展個性化健康教育。根據(jù)患者現(xiàn)有資料判斷是否存在高危因素,如年齡、合并多種慢性疾病、同時服用多種藥物以及腎損傷藥物的使用等,進而通過檢查血清肌酐、肌酐清除率或血清胱抑素C等客觀的腎功能指標識別早期腎損傷的患者[64],除制定安全個性化治療方案的同時要向患者宣教腎損傷健康知識、生活行為注意事項、可能造成腎損害的藥物及目前所用藥物可能的ADR,制定不適隨診方案,囑患者定期至社區(qū)醫(yī)院評估用藥效果,定期監(jiān)測腎功能。對于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專科醫(yī)師應加強患者健康教育,包括疾病臨床表現(xiàn)、危害、飲食和運動處方、藥物治療知識、自我血糖血壓監(jiān)測操作技巧和意義等,有助于全科醫(yī)師對慢性病患者的長期健康管理。
3.3 加強社會支持和健康管理 社會支持的強弱潛在影響著老年人身心健康及生活質量,同時也與藥物治療方案風險密切相關。當?shù)蒯t(yī)院提供的藥品種類、就醫(yī)的方便程度影響著慢性病患者長期用藥的連續(xù)性,對于認知功能減退甚至癡呆的老年人,需明確是否有照料者及其認知功能、健康素養(yǎng)、陪護時間,一方面,專科醫(yī)師應盡量選擇給藥方便的藥物,同時加強照料者的安全用藥教育,避免錯服/漏服藥物、服用過期藥等現(xiàn)象,進行定期檢查,及時調整用藥方案或劑量。另一方面,社區(qū)醫(yī)院可以通過建立家庭醫(yī)生簽約模式、健康小組的護理管理及建立醫(yī)院-社區(qū)-家庭的延伸服務體系改善老年人用藥行為,加強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55,65-66]。
4 總結與展望
我國老年人群體龐大,服用藥物種類多且繁雜,且老年人視力、記憶力減退,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用藥安全的健康管理難以規(guī)范高效的進行。一方面,綜合醫(yī)院門診就診量大,診治病患時間有限,而老年就診患者通常存在共病及多重用藥問題,且國內外尚無完善統(tǒng)一的老年人藥源性腎損害及安全用藥指南,專科醫(yī)師無法在短時間綜合評估患者病情,制定全方位、個性化的用藥方案并進行詳細的相關疾病和用藥安全的健康教育;由于綜合醫(yī)院掛號難、看病貴,患者定期隨訪困難,失訪率高,專科醫(yī)師難以及時得到用藥反饋、記錄ADR并調整用藥方案。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全科醫(yī)學起步晚、基礎弱,全科醫(yī)師數(shù)量不足、質量不高、結構不優(yōu),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尚存在簽而不約、服務滯后等問題,居民對全科醫(yī)師缺乏了解以至于不信任,健康信息化建設滯后、發(fā)展不平衡,都給全科醫(yī)師進行醫(yī)療保健、康復、慢性病管理、診療轉診等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65]。進而影響全科醫(yī)師與專科醫(yī)師進行有效協(xié)同,對建立全-專聯(lián)合管理模式、實現(xiàn)區(qū)域醫(yī)聯(lián)體內分級診療提出了新考驗。
通過建立多專業(yè)的社區(qū)服務團隊 (multispecialty community providers,MCPs)、構建新型照顧模式、培養(yǎng)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保證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整體性和連續(xù)性;通過統(tǒng)一電子醫(yī)療系統(tǒng)、打造信息化的醫(yī)療服務平臺(基于全生命周期電子健康綜合檔案、醫(yī)技預約、聯(lián)合病床整合平臺)、建立全-專聯(lián)合門診、加強全科醫(yī)師與專科醫(yī)師的醫(yī)療行為整合培訓,完善全-專聯(lián)合管理,構成醫(yī)聯(lián)體內醫(yī)療協(xié)作的良性循環(huán)。
綜上所述,由于腎臟易感性及老年人生理性腎功能衰退、年齡相關的藥物代謝動力學和藥物效應動力學變化、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多重用藥和不良用藥行為,老年人用藥安全及藥源性腎損害潛在風險較高,亟需重視并解決。通過全-專聯(lián)合管理,一方面,專科醫(yī)師在診治時根據(jù)老年人生理特點及病史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加強患者健康宣教,定期隨訪血藥濃度、腎功能,密切觀察療效和藥物反應,制定隨診方案。另一方面,全科醫(yī)師要加強老年人長期居家服用藥物過程中的宣傳教育和健康管理,定期隨訪慢性病控制情況并識別可能的ADR,給予多種形式的用藥安全干預措施,提升老年人安全用藥知識及自我管理水平,避免藥源性腎損害的發(fā)生。未來可結合各社區(qū)老年人患病情況、用藥特點制定針對性預防策略,進一步改進數(shù)字化信息平臺,實現(xiàn)資源安全有效共享,借助健康信息技術進行與緩解期患者溝通交流,提醒日常生活及用藥事項,監(jiān)測生命體征,以及及時回訪;設立個體化醫(yī)療試點,對有需求的患者進行個性化照顧;進一步加強全-專聯(lián)合健康管理,提高醫(yī)療服務質量和效率。
作者貢獻:魏珊、劉英莉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劉英莉進行可行性分析;魏珊進行文獻收集及整理,并撰寫論文;劉英莉對文章整體負責,監(jiān)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