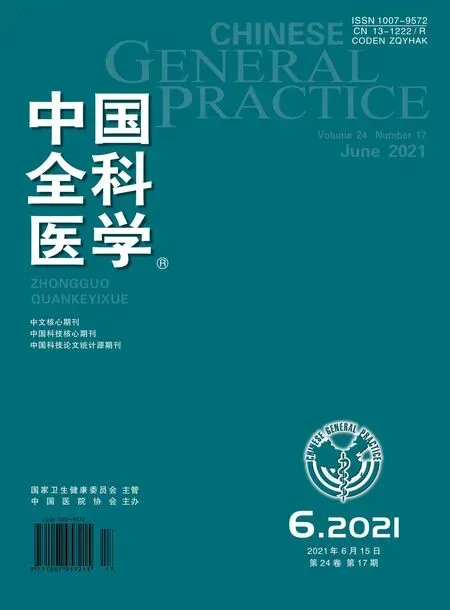加拿大《最佳實踐建議:卒中后抑郁、認知、疲勞》解讀
王梅杰,鄧雨芳,周翔,崔曉敏,姚卓婭,劉芳麗*
卒中是常見的心腦血管疾病,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與生命安全。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卒中是全球范圍內第二致死的原因,也是我國居民首位致死、致殘性疾病[1-3]。卒中患者常見的并發癥包括卒中后抑郁(PSD)、卒中后血管性認知障礙(PVCI)及卒中后疲勞(PSF),這些癥狀常共存于一體,影響患者的康復效果、功能恢復及生活質量,甚至增加了患者的死亡率。我國醫護人員常忽略卒中后并發癥的存在,加之卒中后并發癥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導致此類患者未能得到及時的識別與治療。因此,預防卒中后并發癥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國內現有的卒中相關指南及專家共識涵蓋卒中患者的診斷、治療和康復,但少有指南從PSD、PVCI、PSF方面進行綜合管理。加拿大心臟卒中協會于2019年更新的《最佳實踐建議:卒中后抑郁、認知、疲勞》[4](以下簡稱《建議》)是一套全面的循證指南,該《建議》建立在2015年加拿大《建議》[5]的基礎上,其強調組織多學科綜合管理PSD、PVCI、PSF的重要性,采用加拿大卒中治療最佳實踐推薦報告的證據水平標準評價證據質量,將證據質量分為A~C等級。本課題組對該《建議》的重點內容進行整理并解讀,以便于對我國制定類似的指南或建議提供參考。
1 PSD、PVCI及PSF的相互聯系
PSD、PVCI及PSF是卒中患者常見的并發癥,有20%~50%的患者會出現此類并發癥中的一種[6]。并發癥可重疊出現,相互影響,增加疾病診斷及管理的復雜性。研究表明,30%的卒中患者抑郁和疲勞共存,可能原因為抑郁和疲勞受同一種額葉皮質通路支配,通路損傷導致抑郁和疲勞共存[7-8],也可能與認知障礙有關。輕度認知障礙的患者抑郁癥的總體患病率為32%,PSD與PSF可能相互獨立亦可能相互關聯[9]。亦有研究表明PSD與PSF為雙向相關關系[10]。
2 PSD最佳實踐建議
PSD表現為情緒低沉、悲傷、無興趣、自責等,常伴有軀體癥狀,患病率為29%~31%[11-12]。目前尚無明確的概念及診斷標準。最佳實踐建議,經歷過卒中的患者均應被認為有發生抑郁的風險,并且這種風險可能發生在疾病恢復期的任何階段。提示我國醫護人員在臨床實踐中應該向患者及其家屬提供有關卒中對其情緒影響的信息和健康教育,并對此類患者在后期康復階段進行隨訪,篩查和評估PSD的發生情況。
2.1 PSD的篩查和評估 PSD常發生在卒中后1年內[13],在此期間應該對患者進行階段性篩查。可在住院患者急性期、過渡期、康復期、出院到社區和日常健康評估期間進行篩查,特別是在過渡期。研究發現PSD的風險因素及預測因子對其篩查過程具有重要意義,但尚無相應的檢測工具[14]。《建議》推薦的篩查工具包括流行病學中心研究-抑郁量表(CES-D)、漢密爾頓抑郁評分量表(HDRS)和患者健康問卷9(PHQ-9)[15],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臨床中應由經過培訓的專業人員使用篩查工具進行篩查,對經篩查有PSD的高風險患者,需進一步使用抑郁量表對患者進行評估以判斷抑郁癥狀的嚴重程度,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
目前用于PSD患者的篩查評估量表種類繁多且對患者的測量缺乏特異性。且我國目前使用的量表均來自國外,缺乏適合我國文化特點的PSD篩查量表;未來研究者應進一步研究PSD的篩查工具,為早期發現、早起診斷和防治PSD提供依據。
2.2 PSD的治療 PSD的治療方式包括非藥物治療和藥物治療。《建議》對PSD較重且伴有溝通和認知障礙的患者可采用心理治療和抗抑郁藥物相結合的治療方法。認知行為療法或人際關系療法也是PSD的一種有效療法。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輔助治療方法包括音樂療法、正念療法及動機性訪談等,但此類方法還處于研究的早期階段。深呼吸、冥想、體育鍛煉、重復經顱磁刺激或對于嚴重難治性抑郁癥患者進行深部腦刺激,這些治療方法雖然有相關研究,但其有效性缺乏足夠的證據,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其可行性。
《建議》指出在沒有其他治療的前提下,應密切監測輕度PSD患者的抑郁癥狀是否改善,時間通常為2~4周,如果抑郁癥狀持續或惡化并干擾臨床治療,應考慮藥物治療。XU等[16]研究證實了抗抑郁藥物對PSD患者的治療效果,表明抗抑郁藥能有效減輕PSD患者的抑郁癥狀。但在選擇有效抗抑郁藥物時,應在個體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患者的風險因素及藥物的不良反應,特別是在老年人群中。通常選擇性5-羥色胺再吸收抑制劑為首選抗抑郁藥,若治療后抑郁癥狀緩解,至少需維持治療6~12個月,在此過程中應監測卒中患者抑郁癥狀是否復發。若治療2~4周后抑郁癥狀沒有改善,應首先評估患者藥物治療依從性,如果依從性符合要求,則考慮增加藥物劑量,添加其他藥物或更換藥物。在初始治療階段可考慮維持治療,如果決定停用抗抑郁藥物,應在1~2個月內逐漸減量。盡管預防性應用抗抑郁藥物可以有效預防PSD,但其對患者機體功能的影響尚不清楚。因此,目前不建議所有卒中患者常規使用預防性抗抑郁藥物,但認知行為療法對PSD的預防性治療是有效的。
綜上所述,抑郁可發生在卒中后的任何階段,我國醫護人員應在卒中患者的癥狀管理中,注意觀察患者的心理變化,做到早期識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對于存在抑郁風險的卒中患者,在應用抗抑郁藥物之前,可先進行認知行為療法的干預。
3 PVCI最佳實踐建議
PVCI特指卒中后發生的認知功能下降,主要表現為自理能力下降、工作能力減退、社會功能受損及心理健康等問題,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生存時間[17]。SUN等[18]研究結果顯示,20%~80%的卒中患者會出現認知障礙。血管性認知障礙(VCI)是指由各種腦血管病發生的危險因素直接導致的或與之相關因素導致的認知功能障礙,涵蓋從輕度認知障礙到血管性癡呆的過程[19]。VCI為僅次于阿爾茨海默病的第二大癡呆原因。《建議》指出臨床上有明顯卒中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的患者均應被考慮為有血管認知功能損害的風險。
3.1 PVCI的篩查和評估 VCI概念提出的意義在于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血管性的認知功能下降,防止或延緩發展為血管性癡呆。篩查的對象包括:卒中和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的患者;有其他血管疾病和VCI危險因素的卒中患者,如隱匿性卒中或腦白質病變、高血壓、糖尿病、心房顫動或其他有心臟病的神經影像學表現,特別是既往病史中有認知、知覺或功能改變的患者;另外,因抑郁癥和VCI可同時存在,卒中后疑似有認知障礙也應該進行PSD篩查,此類患者應使用有針對性的、經過驗證的及不同的等效評估工具進行篩查,如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CA)、簡明精神狀態檢查量表(MMSE)。篩查時間包括:在接受急救,特別是在沒有譫妄的情況下,出現認知、知覺或功能障礙時;在住院和以家庭為基礎的康復期間;在出院后到門診或社區醫療機構隨訪時。
有卒中病史并表現出認知障礙的患者(無論是臨床、病史、個人或家庭報告或篩查過程中發現),應由具有神經認知功能專業知識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最好是由臨床神經心理學專家進行評估。應在患者急救期間、康復出院或轉院之前、在接受康復治療時、恢復駕駛或工作時,對其認知能力進行全面評估。另外,卒中后出現急性認知障礙的患者應接受持續性認知障礙的安全風險評估。
《建議》提示我國臨床實踐中,在卒中發生的任何階段,應考慮年齡、卒中的嚴重程度及卒中前患者的功能狀態等,對患者進行全面評估,同時應注意溝通與感覺運動障礙、譫妄、神經精神癥狀和其他可能對認知有影響的疾病。此外,VCI的發生可能與一系列的組織缺陷有關,進一步評估時可考慮患者的感覺運動功能、注意力、定向力、記憶力、信息處理速度和執行功能等方面。未來研究中需要深入研究標準化評估的方法來確定認知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
3.2 PVCI的治療 《建議》指出治療PVCI首先應控制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脂血癥等血管危險因素,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卒中復發風險。其次,PVCI的干預措施包括補償策略和直接修復認知訓練,策略的選擇應根據個人的臨床情況而定。另外,可使用輔助電子和非電子設備的外部策略以及編碼檢索、自我效能訓練和無錯誤學習的內部策略,通過補償來治療記憶障礙。通過元認知策略培訓或正式解決問題的策略來治療執行功能障礙。最后,新興的認知障礙干預措施包括重復經顱磁刺激或經顱直流電刺激,虛擬現實環境的使用,以及約束誘導的方法在受損的認知領域中應用,但這些策略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其可行性。在確定干預措施時應考慮PVCI患者的學習能力,以及如何提供最好的教育使干預的效果最大化。干預措施應以人為本,根據最佳證據進行個體化,并具有促進恢復所需活動的長期目標(如自我護理、休閑、駕駛、重返工作等),且對卒中患者、家庭和看護人的價值觀和期望有所關注。另外,應考慮患者的認知和溝通能力,對于認知和溝通能力有問題的患者,可給予其他支持(如家庭參與),使患者在最大限度上參與目標設定或參與康復。如果障礙的程度已達到中度癡呆階段(無法生活自理),干預措施應更加側重于為照顧者提供教育和支持,代替對患者進行認知康復。
此外,對于PVCI患者,可以進一步評估,建議藥物治療。雖然目前PVCI尚沒有特異性的治療藥物,但研究結果顯示,卒中后有血管性或混合性癡呆的個體可考慮使用膽堿酯酶抑制劑(多奈哌齊、卡巴拉汀、加蘭他敏)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拮抗劑(美金剛),可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20-21]。VCI患者的腦皮質、海馬和紋狀體等部位存在乙酰膽堿通路破壞、乙酰膽堿含量減少、乙酰膽堿活性下降等[20,22],這些為膽堿酯酶抑制劑治療VCI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此類藥物的臨床療效仍存在爭議。因此,應基于患者的臨床評估來使用此類藥物。以上研究提示,我國臨床實踐在借鑒國外藥物治療建議的基礎上,也應開展多中心的PVCI治療和護理干預的臨床研究,促進卒中患者的認知康復。
4 PSF最佳實踐建議
PSF是一種多維的運動感知、情感和認知體驗,其特征是患者在體力或精神活動期間會出現疲憊、精神不振和厭倦的早期疲勞感,通常不能通過休息得到改善。PSF總發病率為39%~75%,住院時約為51%[22-23],發病后1年內可高達69.5%[24],是卒中患者常見的并發癥,可能出現在卒中后康復過程的任何階段。但其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可能與生物學、行為心理學、社會和行為等因素有關[19],危險因素與性別、年齡、卒中類型、抑郁等有關。PSF癥狀常被忽視,因此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應預測PSF的可能性,對有卒中病史的患者通過評估、教育和干預來減輕其疲勞感。需注意的是PSF與卒中的嚴重程度無關,輕度卒中的患者仍然可能發生PSF。
4.1 PSF的篩查和評估 篩查和評估卒中患者是否出現疲勞及其嚴重程度是進行有效管理的前提。雖然目前有較多量表可用于評估PSF〔如疲勞嚴重程度量表(FSS)、個人強度目錄(CIS)、疲勞影響量(FIS)、表疲勞評價量表(FAS)等〕,但對PSF患者特異性的篩查和評估工具仍沒有明確的統一標準。因此選擇量表時應評估其適用對象、評估該量表是否為國際公認權威的量表、評估患者的人口學特征及疾病階段等。《建議》指出PSF患者應篩查與疲勞相關的或加重疲勞的藥物。對于身體狀況穩定但合并疲勞的卒中患者,應對可能導致疲勞的身體及心理因素進行全面評估,特別是在康復或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時[25]。在患者接受急救或住院康復出院之前,醫護人員應向患者及其家屬提供PSF的基本信息。在患者回到社區后,應在后續的就診中定期篩查卒中患者是否患有PSF。
4.2 PSF的管理 PSF是一種多因素、多癥狀后遺癥,病理機制尚未明確,尚無明確有效的治療措施,采取個體化、多學科的管理方案對改善PSF患者的生活質量、提高治療效果至關重要。疲勞管理是對PSF患者進行疲勞相關知識和自我管理的一種治療方法,可以讓患者知曉非正常疲勞的原因及對日常生活的影響。通過對疲勞的管理,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并幫助治療策略療效的實現[26]。《建議》指出對PSF患者進行疲勞相關知識和自我管理的健康教育是管理的主要內容。HOFER等[27]對PSF患者開展20次的疲勞管理課程培訓,包括識別疲勞癥狀、找出導致疲勞的原因及盡量避免導致疲勞的活動等,制定個人休息策略,制定1 d中實際可達到的目標,患者成功管理了疲勞癥狀,最大限度上改善了日常活動功能。其他干預措施包括:心理干預、正念療法、運動干預等,但此類方法缺乏足夠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的支持。
目前對于PSF的治療尚無特效藥物,用藥目的主要是針對引起PSF的慢性疼痛和不適進行治療。在一些卒中患者中,可使用莫達非尼治療PSF[26],但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充分驗證此類治療方法的可行性。此外,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推薦使用抗抑郁藥物治療PSF。OVERGAARD等[28]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發現,PSF患者服用莫達非尼3個月后,疲勞癥狀得到有效緩解。但在使用藥物時應謹慎,且只能用于診斷明確的患者,應特別注意藥物的不良反應。
以上研究提示臨床實踐中應由疲勞癥狀管理方面有經驗的醫務人員向卒中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有關日常時間管理和活動與休息的健康教育,鼓勵卒中患者向其家庭成員、護理人員等傳達休息需求;并進一步研究開發PSF的篩查和評估工具。
5 小結
2019年更新的《建議》,為我國醫護人員的臨床實踐提供循證依據。抑郁、VCI、疲勞在卒中患者中普遍存在,但易被忽視,《建議》強調篩查和評估的重要性,提示我國醫護人員應從篩查、評估和管理三個方面入手,將PSD、PVCI和PSF納入到現有的卒中管理方案中,進行多學科綜合管理;并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制定個體化診療方案和構建適合我國臨床環境的PSD、PVCI及PSF臨床護理實踐方案,規范和指導臨床實踐;改善卒中患者的照護結局,提高我國卒中患者的生活質量。
作者貢獻:王梅杰、鄧雨芳、周翔、崔曉敏負責文獻收集、整理,撰寫論文;姚卓婭負責文章的審校;劉芳麗負責文章的選題、修改、對文章整體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