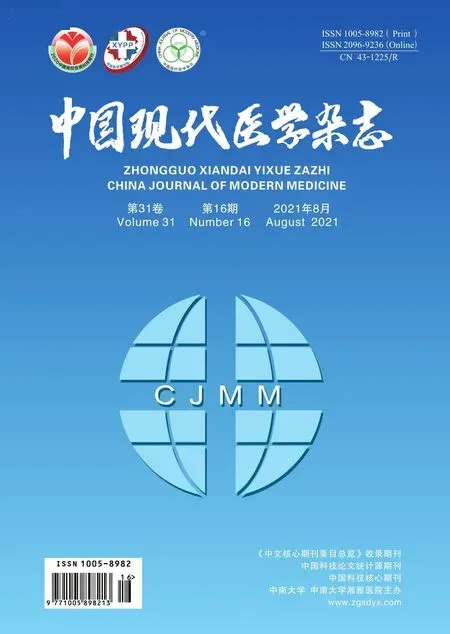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在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中的研究進展*
甄艷華,任海燕,鄭加賀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放射科,遼寧沈陽110004)
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arterialsclerosis obliterans,ASO)是動脈粥樣硬化最常見的表現之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及身體功能。有研究表明炎癥反應在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及預后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3]。系統性炎癥通過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破壞斑塊穩定、損害內皮功能或導致動脈過早僵硬,增加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4]。另外慢性血管炎癥反應還參與了球囊血管成形術和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發展[5-7]。球囊擴張和血管損傷過程中的剪切應力是血管炎癥的觸發事件,它刺激促炎分子的產生和循環單核細胞的活化[8-9]。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通過測量血清生物標志物來量化炎癥程度,C 反應蛋白、白細胞介素-6、白細胞、腫瘤壞死因子-α 等[10-11]被認為是有效的預測因子,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作為心血管疾病分層和預后的有效生物標志物[12],尤其是下肢ASO,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中性粒細胞代表亞臨床炎癥階段,釋放促氧化劑和凝血酶原物質,導致內皮損傷和血小板聚集[13]。較低的淋巴細胞計數反映了皮質醇產量的增加,這與血管事件引起的生理壓力或健康狀況不佳有關[14]。NLR 是一種簡單的衍生標志物,其相對便宜,比其他標志物更易獲得,并且已經證明其是反映炎癥細胞失衡和活化中性粒細胞在動脈粥樣化形成中作用的心血管結果良好的預測因子[15-16],且其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中的應用已經得到廣泛證實[17-19],而關于NLR 與下肢ASO 的關系的相關研究還不多,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總結NLR 在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中的應用進展。
1 NLR與下肢ASO疾病的嚴重程度
泛大西洋學會聯盟(TASC)-Ⅱ分級以血管造影為基礎,根據病變的復雜性和解剖分布將下肢ASO分為4 類,在臨床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研究表明[20]NLR 是TASC-Ⅱ類下肢ASO 的獨立預測因子。該研究分析了343 例下肢ASO 患者,結果表明低密度脂蛋白[=1.010(95% CI:1.003,1.017),P=0.004)]、高密度脂蛋白[=0.940(95% CI:0.894,0.987),P=0.013]和NLR[=1.910(95% CI:1.510,2.410),P=0.001]是預測較高TASC 分級的獨立影響因素。對于TASC-ⅡC 類和D 類患者,NLR 截點值為3.05,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5.0%和62.9%。下肢ASO 還可根據臨床癥狀使用Fontaine 進行分類,然而DEMIRTAS 等[21]的研究中,平均NLR 與下肢ASO 的Fontaine's 分級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平均NLR:I 級為(3.3±1.1)%,Ⅱ級為(3.1±1.3)%,Ⅲ級為(3.4±1.1)%],因此,NLR 與下肢ASO 疾病嚴重程度的關系還需進一步研究。
嚴重肢體缺血(critical limb ischemia,CLI)是下肢ASO 的嚴重階段,包括靜息痛、潰瘍、壞疽等,具有較高的死亡率及截肢率[22]。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腔內治療已經得到迅速發展,但死亡率和截肢率仍然很高[23]。因此對CLI 患者進行分層,以輔助臨床決策非常重要。BELAJ 等[24]對1 995 例外周動脈疾病的患者進行分析,研究表明較高的NLR與下肢CLI 的發生具有相關性。NLR>2.5 時患者發生CLI 的風險增大1.6 倍。GARY 等[25]分析了2121 例下肢ASO 的患者,ROC 曲線分析NLR 的截點值為3.95,CLI 在NLR>3.95 組的發生率明顯高于NLR≤3.95 組(分別為48.5%和24.3%),這對于降低CLI患者死亡率具有重要意義。
2 NLR與下肢ASO患者的術后療效相關性
NLR 不但可以評估下肢ASO 的嚴重程度,還可以預測下肢ASO 患者動脈血運重建的預后情況。GONZALEZ-FAJARDO 等[26]隨訪了561 例接受血管手術治療(包括腔內治療及外科手術治療)的慢性CLI 患者,研究結果表明術前NLR>5 的患者其5年內的死亡率及截肢率均高于NLR<5 的患者。SPARK 等[27]隨訪了149 例接受腔內治療或外科手術的CLI 患者,多因素分析表明術前NLR>5.25 是預測CLI 患者死亡情況的有效指標[=2.3(95% CI:1.2,4.2),P=0.007]。另外,ERTURK 等[28]的研究表明術前NLR>3.0 是下肢ASO 患者血管手術治療(包括腔內治療及外科手術治療)術后發生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危險因素[=2.040(95% CI:1.260,3.300),P=0.004]。NLR 不僅影響著下肢ASO 患者血運重建后的情況,還與保守治療后的截肢率密切相關。LUO 等[29]隨訪了172 例接受保守的CLI 患者,結果表明術后NLR 是CLI 患者發生截肢的獨立危險因素,術后NLR≥3.8 的CLI 患者截肢風險較高。
經皮腔內血管成形術(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是目前治療下肢ASO 病變的主要手段[30]。術后再狹窄仍然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研究表明炎癥反應與術后再狹窄的發生密切相關[3,31-32]。WELT 等[33]的動物實驗表明球囊損傷后的炎癥反應是短暫的,主要由中性粒細胞組成。相比之下,支架植入后的炎癥反應更長,包括中性粒細胞的早期釋放和巨噬細胞的積聚。趨化因子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和白細胞介素-8等趨化因子在球囊損傷后短暫表達,而在支架植入后則持續表達。因此支架植入術比普通球囊血管成形術對于組織損傷更加嚴重,會有更顯著的炎癥反應。而目前對于NLR 與球囊血管成形術預后的關系的研究較少,ZHEN 等[34]隨訪了106 例接受PTA 的股腘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結果表明NLR是股腘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PTA 術后6 個月一期通暢率的獨立危險因素。CHANG 等[35]回顧性分析了術前NLR 與180 例股腘動脈慢性完全閉塞患者支架術后再狹窄發生率的關系,多因素分析表明術前NLR>3.62 是預測短期支架內再狹窄發生率的獨立危險因素[=1.703(95% CI:1.521,2.163),P=0.002]。CHAN 等[36]回顧性分析了83 例接受膝下血管成形術的CLI 患者,與NLR 較低的患者比較,NLR≥5.25 的患者在1年后死亡的風險顯著增加[=1.970(95% CI:1.080,3.620),P=0.030]。淋巴細胞計數<1.5×109/L 的患者具有更高的死亡率[=1.880(95% CI:1.020,3.700),P<0.05]。因此,NLR 可能是對接受下肢動脈血管成形術患者進行風險分層的有效工具。
3 NLR與其他炎癥因子的聯合使用
多種炎癥因子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的炎癥過程,因此,同時測量不同的炎癥生物標志物可以為評估患者預后提供更多的信息。TASOGLU 等[37]通過NLR 與血小板- 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PLR)來評估CLI 患者的保肢率,研究中隨訪了104 例慢性CLI 患者,根據NLR 與PLR的ROC 曲線截點值(分別為3.2 和160)將患者分為高危組(NLR>3.2 和PLR>160)、中危組(NLR >3.2 或PLR>160)、低危組(NLR<3.2 和PLR<160),各組的生存率及保肢率均有差異(P<0.05),多因素分析高危組是中期截肢率的獨立危險因素[=4.700(95% CI:1.000,12.600),P<0.05]。聯合使用多種炎癥因子評價下肢ASO 患者預后情況的研究相對較少,哪些炎癥因子聯合使用能更好評價預后,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4 NLR的局限性
對于NLR 在心血管生物標志物方面的作用已經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然而NLR 作為一種預測因子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不同的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截點值。在包括9 427 例受試者在內的全國健康和營養檢查調查的代表性樣本中,普通人群的平均NLR 為2.15,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吸煙者NLR 顯著高于不患此類疾病及不吸煙者[38]。其次,NLR 容易受到分子或分母變化的影響,例如風濕免疫性疾病、癌癥、糖尿病等都會產生影響[39-40],因此,容易產生潛在的偏倚,從而導致假陽性關聯。另外,炎癥反應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有多種炎癥因子參與,單一炎癥因子的預測效果有限,因此多種炎癥生物標志物的組合可能有助于評估下肢ASO 疾病的嚴重程度及預后。
綜上所述,NLR 這一簡單、快速、可廣泛獲得的生物標志物可以為風險分層提供額外的無創工具,以評估下肢ASO 的嚴重程度、治療反應和預后。然而對于特定人群的NLR 正常值,還應該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以闡明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的潛在機制,以此來評估抗炎治療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