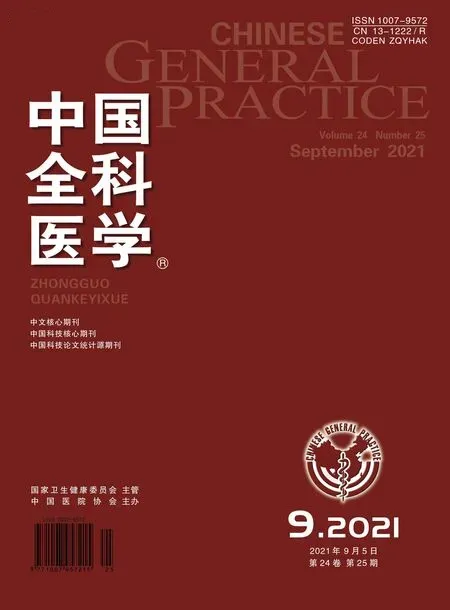完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建設:基于基層衛生“平戰”防疫視角
黃蛟靈,黃豪,梁鴻,方菲,崔雅琦,陳晨,陳淑琴,唐嵐,王朝昕,常偉,姚玉鳳*
為提升特大城市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治理能力、積極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海市委、市政府印發《關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并制定三年行動計劃,強調要堅持依法防控、系統治理,預防為主、平戰結合,統一指揮、聯防聯控,科技引領、精準施策,爭取到2025年重大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能力達到國際一流水準,將上海建成全球公共衛生最安全城市之一[1]。大城市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建設的牢固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衛生“網底”筑構[2-3],除了戰時應急響應,更要看基層平時常態化工作是否扎實[4]。當前對于基層衛生在大城市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中的功能定位與作用、現實困境與“短板”缺乏系統調研與深入探討。本研究聚焦基層衛生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發揮的作用,通過實地考察與小組座談等形式,選取上海市5個區10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作為調研地點,深入考察上海市基層衛生在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實踐探索,并剖析當前存在的問題與困境,為完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提供政策建議與決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研究于上海市范圍內進行調查,調查區域的選取主要考慮了上海市城區與郊區的差異性,共選擇了2個中心城區區域、2個郊區區域及1個城郊區域(區域的選擇兼顧了隨機性與實際操作性)。每個區域隨機選擇2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現場訪談,共調研10家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本文對于調查區域及單位進行匿名化處理,僅以代表性區域命名,以代表性區域的選擇來反映上海市基本情況。本次調查除了選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即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外,還調研了各區疾控業務相關部門,即衛生健康委員會和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共開展5場調研。
1.2 調查工具 本次調查主要采用小組座談的方式進行,根據調查對象的差異設計了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完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建設訪談大綱”,訪談大綱共有3個版本,包括社區衛生(CHSC)卷、疾控(CDC)卷、衛生健康委(HC)卷,3個版本分別適用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即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含站點)〕、區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區衛生健康委員會3個座談場景。其中,CHSC卷訪談對象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人(主任或副主任)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護士、公共衛生醫師、藥師、檢驗后勤等人員,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疫情期間承接主要任務、組織架構、實際工作內容、內部協同、主要問題與建議等。CDC卷與HC卷訪談對象主要包括中心或委員會負責人(主任或副主任)及辦公室與信息部門相關人員、業務管理與質控部門人員、突發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與傳染病預防控制條線管理人員等,訪談內容主要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疫情中的主要職能與實際作用、暴露的“短板”、衛生健康委員會/疾控中心如何予以支持及如何平戰結合。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于2020年6—9月于上海市各調查區域內開展,調查組由課題組研究人員與研究生組成,提前3 d發送訪談大綱給各調研機構,由調研機構對重點訪談內容進行提前準備。座談由調查組與調研機構人員構成,主要座談對象控制在15人以內,允許其余相關人員列席并就訪談內容進行適當補充。座談時間為1~2 h。調研同時輔之以關鍵人士訪談,以解決共同座談中可能存在的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訪談內容回避情況。關鍵人士訪談主要對基層醫務人員進行,包括上門排查、支援道口、隔離點、機場醫務人員,每個區選擇3~5名訪談人員(包括全科醫生、護士、公共衛生醫生)。
1.4 資料分析 座談與關鍵人士訪談由調查組人員進行實時記錄,并在調查結束后進行統一整理。整理方式為將各個區同類記錄整理匯編,形成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記錄1份、衛生健康委員會記錄1份、疾控中心記錄1份。課題組成員進一步梳理記錄內容,歸納形成功能作用與“短板”的共性內容。
2 結果
2.1 基層衛生在公共衛生防疫體系中發揮的作用
2.1.1 戰時應急響應,區域聯防聯控 調研地所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均在疫情暴發初期快速成立疫情防控管理小組,疫情防控管理小組一般由中心主任擔任組長,設有信息組、排摸組、居家組、后勤組等。調查表明突發疫情初期工作壓力主要集中在上門摸排篩查及支援區域隔離點。上門排查工作由社區家庭醫生或護士執行,對風險地區返滬人員進行14 d每日體溫測量與登記,對異常人員進行第一時間轉送。疫情初期隔離點隔離人員主要為國內風險地區返滬人員、密接人員,隨著國內疫情逐漸控制,其構成人員主要為國外歸國人員。隔離點的分配由上海市各區域之間及區域內統籌,各中心實行責任分工駐點。基層衛生醫務人員入駐隔離點,對隔離人員進行流行病學登記與信息采集、采樣與醫療觀察,以及提供必要的醫療衛生服務。
同時,調查表明基層衛生與區域內居委會和民警有序分工協同,在居委與民警協同下共同開展防疫工作,實現區域內聯防聯控。在返滬人員進入小區后由居委進行隔離告知,建立對應的隔離微信群,群由被隔離人員、居委干事與負責的基層醫務人員構成,進行信息的溝通交流,居委干事協助基層醫務人員開展工作,避免可能存在的不理解與不配合。突發事件由居委、基層醫務人員、民警進行第一時間溝通協同處理。
2.1.2 院內分診篩查,保障基本醫療 被調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均正常開放,滿足居民的基本醫療需求。所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了院內分診設置,通過人流疏導與篩查開展院內感染防控。一般在中心入口處進行體溫測量與流行病學調查,并且對人流進行標識引導,避免聚集。體溫異常者會被引導至留觀室進一步排查,經排查體溫異常且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存在風險者,均由120轉運至就近開設發熱門診的二、三級醫院。
同時中心執行上海市對于慢性病長處方政策的延長政策,對于診斷明確、病情穩定、需要長期服用治療性用藥的簽約慢性病患者,可最多一次開具3個月用量的藥物,盡可能減少患者的配藥出行與院內聚集。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線上就診預約,與簽約家庭醫生提前預約時間段就診,實現分時段有序就診。設有病房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也正常運行,加強病房患者與探視者的體溫測量與管理。
2.1.3 借力新冠肺炎疫情,做實簽約服務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除了全面開診,滿足居民基本醫療需求外,家庭醫生團隊借助此次疫情契機,持續推進家庭醫生簽約工作。上海市于2015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本市社區衛生服務綜合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及8個配套文件,開始了新一輪社區衛生服務綜合改革[5],在全國層面較早探索踐行“簽約一人、履約一人、做實一人”。而30%簽約率瓶頸成為各個區域各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重點突破工作[6]。疫情暴發初期,家庭醫生團隊借助手機APP、微信、電話、短信等多種途徑與簽約居民建立了更為密切的“伙伴式”關系,推送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健康教育信息,緩解居民對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焦慮感與心理健康問題,并且提供必要的健康咨詢與預約服務。
隨著疫情進入常態化階段,家庭醫生團隊著力開展家庭醫生樓宇服務。上海市2018年提出“健康樓宇”的概念,2020年開始全市試點工作,家庭醫生樓宇服務旨在為功能社區的職業人群提供綜合、連續、全程的健康管理服務,努力消除中青年群體在健康管理服務上的空白點[7]。而借力此次疫情,全市范圍內正式開啟家庭醫生樓宇服務,進入樓宇進行合作洽談,通過線上與線下的方式開展健康宣教、駐點服務與簽約工作。
2.2 當前基層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存在的不足
2.2.1 物資與人力資源數量不足 調研發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疫情暴發初期普遍存在口罩、防護服、醫用手套、防護鏡等防疫物資短缺問題,對基層醫務人員開展防疫工作造成較大制約,并且對基層醫務人員自身健康帶來安全隱患,尤其困擾有道口防疫與多隔離點防疫任務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伴隨疫情的逐漸控制與穩定,防疫物資也逐漸到位,實現對基層醫務人員防疫工作的保障與支持。
人力資源的不足導致基層衛生戰時與平時工作疊加,壓力大。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介紹上海市目前有6 000余個家庭醫生團隊,團隊主要由家庭醫生與護理人員(助手)組成(各個區情況略有差異),服務上海市2 400余萬常住人口,平均一個團隊服務4 000名常住居民,遠高于2 500名數量的服務標準[8]。除了日常基本醫療服務與公共衛生服務外,疫情應急期間基層衛生還承擔了道口支援、隔離點防疫任務,且疫情進入常態化階段后,日常工作與防疫工作將長期并存,對本就存在人力資源缺口的中心造成了較大工作負荷。有限的人力資源也存在職能錯位的情況。調查發現,部分隔離點醫務人員同時承擔了收取快遞、換洗床單、消殺、采樣等內場與外場工作,存在醫務人員職能錯位的現象。
2.2.2 心理防疫能力不足 基層衛生心理應急防疫職能缺位,調研發現當前基層衛生醫務人員均不具備心理咨詢資質,也并不提供專業心理與精神疾病的診療服務。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為一種身體上、精神上的完美狀態,以及良好的適應力,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衰弱的狀態[9]。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基本醫療服務,家庭醫生承擔著全人群健康管理職能,是實現全民健康的重要抓手,當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心理健康職能缺位是實現全民健康管理的較大“短板”。
2.2.3 內部分工與多部門管理不足 調研發現社區家庭醫生團隊存在基本醫療與公共衛生割裂的狀況。家庭醫生團隊主要包括家庭醫生、護士、公共衛生醫師、助理等,家庭醫生主要負責門診看病,社區護士協助家庭醫生進行慢性病隨訪、健康體檢、健康檔案建設,公共衛生醫師則延續條線管理。當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基本醫療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提供是割裂式的,這種分工模式作為實現全民健康的方法手段在理念上存在偏差,暴露在防疫階段顯得尤為明顯。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作為基本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的主要提供機構,由區衛生健康委(或鎮政府)、疾病預防控制等部門共同管理,在公共衛生條線則由婦幼、精神衛生、殘疾人/腫瘤患者、結核、學校營養等多條線轄管。同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處于街道層面,實行市級—區級(鎮)—街道多層級管理。公共衛生防疫涉及多部門之間的聯動與協同,而規劃落實中由于各部門之間目標定位不同、行動模式差異、責任邊界模糊等,不同部門之間互相掣肘甚至走向相反,容易形成政策“孤島”。這種多層級、多條線、多部門管理為社區平時與戰時工作造成一定困擾,主要表現為多條線數據重復填寫報送、多部門管理考核指標“打架”現象。
2.2.4 基層衛生激勵機制與活力不足 基層衛生人員流失與招聘困難,調研表明多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存在用人招聘困境,尤其是公共衛生醫師招聘難。當前對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站點的公共衛生醫師人數缺乏統計,但是調研普遍反映社區公共衛生醫師人數不足,且人員招聘困難導致當前公共衛生工作開展存在難度。同時,除了招人難外,社區還存在人員流失困境。
收支兩條線制約基層衛生活力。無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疫情防控的主要場景都在社區。中國的基層社區在公共衛生應急防疫中具有地理位置和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天然優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承擔著對轄區內居民醫療、預防、保健、康復等六位一體的職責功能[10]。然而調研發現政府在實行新一輪“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收支兩條線政策后,基層衛生服務的收入所得上繳財政,基層醫務人員在疫情期間工作負擔極度加大情況下并未得到額外收入補貼,一定程度削弱了基層醫務人員參與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熱情。
3 政策建議:理順四大關系
3.1 理順基本醫療與公共衛生關系 厘清基本概念、研制平戰簽約服務清單。首先需要厘清何為“基本”,何為“醫療”與“公共衛生”。前者涉及服務提供的邊界問題,后者涉及醫療與公共衛生的關系與職能分工問題。核心概念“公共衛生”隨著我國頂層設計政策演化,已經不再局限于傳染病防治,而拓寬到全人口健康,傳統意義上的基本醫療與公共衛生在基層衛生層面得到了融合。在“基本”邊界劃分基礎上簽約服務包需要進一步細化,平時工作與戰時工作均應當在清單中有所體現,或者在已有清單中添加戰時工作內容,與績效考核有所關聯,也涉及家庭醫生團隊工作內容與后期分工問題。
明晰團隊職責分工、細化成員績效考核。家庭醫生團隊構成包括家庭醫生、護士、公共衛生醫師、團隊助理等,雖然不同區域有不同的團隊構成與協同模式,但可以明確的是家庭醫生團隊是開展基本醫療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主體。當前家庭醫生團隊職能分工仍然處于探索階段,團隊中不同主體承擔哪些工作內容及如何分工并未形成一致性規范。當前研究顯示家庭醫生團隊模式存在家庭醫生365模式、家庭醫生11253模式、家庭醫生團隊長模式等[11-13]。在社區衛生服務經歷長達十年的實踐探索后,有必要總結創新模式,厘清各自職能分工,將基本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融入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包中,進行精準化的團隊分工與責任邊界劃分。
3.2 理順平時與戰時關系 加強團隊心理專長、補齊心理應急“短板”。在疫情期間,社區居民由于長時間的居家隔離、生活不便及關于疫情的大量消極信息,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14]。當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大多未開設精神衛生科,本文建議在社區開設心理咨詢室,而不是精神科門診。原因如下:第一,當前社區居民對于精神健康存在較大的認知不足,存在對有精神障礙居民“污名化”的傾向,居民更傾向于“咨詢”而非“看病”[15]。第二,心理咨詢室的主要功能是前期心理問題疏導與診斷,當出現嚴重精神疾病時轉診患者至精神衛生中心接受治療,并且接收由精神衛生中心返回社區的人員名單進行跟蹤隨訪。因此通過對當前家庭醫生開展心理咨詢培訓、考核與資助或許最貼合居民需求。
構建社區志愿者庫、加強志愿者應急培訓。調研發現社區防疫層面在出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面臨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所有社區在防疫工作中均會納入志愿者進行支援,包括道口防疫篩查、居民區進出排查、隔離點服務等。所有志愿者的號召與調配都是臨時性的,當前對于志愿者防疫培訓較少。因此本文建議構建志愿者庫,并加強對志愿者的公共衛生應急培訓,培訓可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可采用“線上+線下”方式開展季度性培訓,在對防疫流程操作化培訓過程中,融入家庭醫生的健康宣教服務,加深志愿者自身健康管理與安全防護認知。
3.3 理順社區與上級關系 公共衛生醫師下沉社區,補齊人員“短板”。上海市各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公共衛生醫師人數均存在較大缺口[16],平時與戰時工作壓力大,尤其是疫情常態化中平戰結合期間工作負荷突出。建議根據服務常住人口數量,增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公共衛生醫師編制數量。在編制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可通過上級公共衛生專業機構人員下沉社區的方法彌補人員缺口“短板”。
加強疾控對社區指導,提升社區應急能力。疾控部門具有對下級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公共衛生指導的功能,但是目前疫情暴發凸顯了其指導功能缺位的問題。當前疾控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指導尚未形成規范,即無明確時間周期、無明確指導內容、無培訓考核標準,且培訓對象局限(主要培訓對象為公共衛生醫師)。
3.4 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 弱化收支兩條線制度,激發社區活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與疾病公共衛生服務被認為是政府責任,而承擔這兩項工作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被明確賦予了“公益”性質[17]。公辦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政府財政托底,同時中心所有收入也上繳政府部門。這樣一種公辦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社區活力,造成了當前供給側缺乏活力與主動性的問題[18]。
為了破解這一困局,上海市探索建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費,即家庭醫生每簽約一個居民可以獲得10元·人-1·月-1簽約服務費[19]。有觀點指出“簽約服務費不納入基層機構績效工資總額”的政策引導下,簽約服務費將成為家庭醫生薪酬收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簽約服務費標準和籌資渠道決定了簽約服務費對家庭醫生和團隊成員的薪酬補償作用[20]。政府責任體現在基本服務的提供上,并不意味著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存在方式是政府辦、政府管、政府提供。全科模式較為成熟的英國提供了“購買與提供分開”模式。英國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形式,成立健康與福祉理事會并設立衛生與社會照顧服務聯合購買基金池,統籌地方的公共衛生與醫療決策[21],為我國下一步基層改革提供了可借鑒范本。
作者貢獻:黃蛟靈撰寫論文;梁鴻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黃豪、方菲、崔雅琦、陳晨、陳淑琴、唐嵐開展調查與訪談工作;常偉進行論文的修訂;王朝昕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姚玉鳳對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