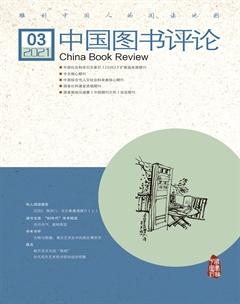借尸還魂
王銳
【導(dǎo)??讀】宮崎市定的作品在當(dāng)下的圖書(shū)市場(chǎng)中頗為流行。但必須注意到,宮崎的史學(xué)思想與近代日本右翼思潮之間有著比較緊密的聯(lián)系。宮崎的許多論著,從題材上來(lái)看或許屬于中國(guó)古代史范疇,但在著述目的上,則很大程度上是為近代以來(lái)日本的對(duì)外擴(kuò)張政策進(jìn)行歷史的論證。在這其中,他對(duì)明代倭寇的分析就是典型例子。
【關(guān)鍵詞】宮崎市定??倭寇??東洋史
最近幾年,與日本右翼有著千絲萬(wàn)縷聯(lián)系的史家宮崎市定的著作被大量翻譯到中國(guó),在中國(guó)的圖書(shū)市場(chǎng)中十分流行,成為大眾歷史領(lǐng)域的寵兒,同時(shí)還有不少專(zhuān)業(yè)研究者為其背書(shū)。宮崎市定不僅是一位史學(xué)研究者,而且早年還參與了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zhēng)。從1939年到1944年,他以京東大學(xué)東洋史專(zhuān)家的身份參與了旨在為日本侵略服務(wù)的東方文化學(xué)院與東亞研究所的相關(guān)項(xiàng)目。在1943年,他出版了一本專(zhuān)門(mén)討論日本歷史的著作《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從書(shū)名就可看出,他援引《隋書(shū)·倭國(guó)傳》中“日出處天子致書(shū)日沒(méi)處天子”的記載,凸顯日本是所謂“日出之國(guó)”,中國(guó)乃“日沒(méi)之處”。如果說(shuō)此書(shū)中的這段話是日本使臣刻意張揚(yáng)其主體性,那么宮崎在戰(zhàn)爭(zhēng)背景下取此典故以為書(shū)名,其目的也就顯而易見(jiàn)。對(duì)此,他晚年如是評(píng)說(shuō):
《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成書(shū)于“二戰(zhàn)”期間,今天再次閱讀,不可否認(rèn),在我撰述意圖中確實(shí)有些“發(fā)揚(yáng)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辭上也顯得有些過(guò)時(shí),今天看簡(jiǎn)直毫無(wú)辦法。然而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那種動(dòng)不動(dòng)就通過(guò)揭露自己國(guó)家的劣根性來(lái)表示進(jìn)步的現(xiàn)代風(fēng)潮,反而令人覺(jué)得不適。還有,如書(shū)中的《倭寇的本質(zhì)與日本的南進(jìn)》一篇,因當(dāng)時(shí)急于表達(dá)自己的主張,今天看來(lái)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應(yīng)有的說(shuō)服力。[1]
“二戰(zhàn)”以后,日本國(guó)內(nèi)開(kāi)始清算戰(zhàn)爭(zhēng)期間的意識(shí)形態(tài)。這其中固然有美國(guó)支持下帶有美式自由主義色彩的反戰(zhàn)宣傳,但影響更大的當(dāng)屬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學(xué)術(shù)研究與大眾宣傳,特別是在東洋史研究領(lǐng)域,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頗為流行,或許這便是讓宮崎深感不適的“現(xiàn)代風(fēng)潮”[2]。由此可見(jiàn),宮崎本質(zhì)上并未否定自己在此書(shū)中的核心觀點(diǎn),只是覺(jué)得書(shū)中的措辭時(shí)代感過(guò)強(qiáng),太“急于表達(dá)自己的主張”,致使失去“應(yīng)有的說(shuō)服力”。換句話說(shuō),假如此書(shū)在修辭上更加巧妙、表達(dá)上更加靈活,是不是就更有說(shuō)服力呢?
宮崎提到收入此書(shū)的一篇名為“倭寇的本質(zhì)與日本的南進(jìn)”的文章。文章題目中的“日本的南進(jìn)”,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二戰(zhàn)”期間日本軍部的南進(jìn)政策。如此直白的措辭,或許就是宮崎后來(lái)所說(shuō)的太“急于表達(dá)自己的主張”。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此文為倭寇所做的翻案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圖。
宮崎開(kāi)篇即言:“所謂倭寇,絕對(duì)不是以強(qiáng)取財(cái)物為目的的強(qiáng)盜集團(tuán)。”[3]23為什么這么說(shuō)?他從分析明代負(fù)責(zé)海外貿(mào)易的市舶司開(kāi)始。他認(rèn)為后者旨在為明廷服務(wù),日本一方的受益者也限于室町幕府的將軍及其周?chē)鷻?quán)貴,對(duì)于雙方民眾而言,這一機(jī)構(gòu)的作用極為有限。因此,“兩國(guó)的民眾必然會(huì)在中國(guó)沿海的島嶼上尋找適當(dāng)?shù)牡攸c(diǎn)進(jìn)行走私貿(mào)易”[3]28。明廷對(duì)此自然是嚴(yán)厲取締,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宮崎對(duì)于此時(shí)日本人心態(tài)的描述:
日本人只是希望能夠和平地進(jìn)行貿(mào)易,即使這樣的貿(mào)易違反了中國(guó)的國(guó)法,但這也似乎與日本人無(wú)關(guān)。因此,在明軍與走私成員爭(zhēng)斗之時(shí),日本人基本上保持著事不關(guān)己的中立態(tài)度,只是希望騷亂能夠盡早平息,期待著明朝允許日中兩國(guó)民眾自由貿(mào)易的日子早點(diǎn)到來(lái)。[3]31
宮崎一面提到日本參與中國(guó)沿海的走私貿(mào)易,一面又說(shuō)此舉即便違反明代律法,也和日本人無(wú)關(guān),因?yàn)槿毡臼窃诟恪白杂少Q(mào)易”。且不說(shuō)此處的“自由貿(mào)易”明顯挪用了近代西方全球擴(kuò)張時(shí)期的概念,根本不是古代東亞世界的史事;其直接目的,更是意在彰顯日本是東亞“自由貿(mào)易”的維護(hù)者,而明代中國(guó)則是“閉關(guān)鎖國(guó)”,不讓本國(guó)“民眾”與日本自由做生意。此論宛如鴉片戰(zhàn)爭(zhēng)前夕,帶有武裝殖民集團(tuán)性質(zhì)的英國(guó)東印度公司指責(zé)清政府封閉自大,拒絕與其展開(kāi)“自由貿(mào)易”一樣。
照此邏輯,日本商人為了維護(hù)中日之間的“自由貿(mào)易”,自然不能僅止于“期待著”,而是要有所作為:
世人動(dòng)輒將倭寇誤解為以掠奪為目的的海盜行為,實(shí)際上并非如此……日本商人最初可能只是觀望,但一旦意識(shí)到既有的權(quán)益無(wú)法恢復(fù),中國(guó)的貿(mào)易伙伴又被官府羈押,受到迫害,因此,當(dāng)有貿(mào)易伙伴請(qǐng)求他們出手援助時(shí),便再也無(wú)法坐視不管,從而加入復(fù)仇戰(zhàn)爭(zhēng)中去。這才是倭寇的本質(zhì),才是他們的本來(lái)面目。兩國(guó)政府之間的統(tǒng)制貿(mào)易無(wú)法滿(mǎn)足民間的要求,于是民間貿(mào)易開(kāi)始興起,對(duì)民間貿(mào)易進(jìn)行干涉,并從干涉發(fā)展到軍事討伐,然后對(duì)軍事討伐進(jìn)行復(fù)仇,然后對(duì)復(fù)仇進(jìn)行援助,經(jīng)過(guò)了這一系列的過(guò)程才出現(xiàn)了倭寇。[3]33
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把海洋作為區(qū)別于陸地的空間規(guī)劃,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這種區(qū)分原則支配了17、18世紀(jì)的國(guó)際法的基本結(jié)構(gòu)——海洋開(kāi)放、第一個(gè)全球化地球圖景誕生之后的國(guó)際法基本結(jié)構(gòu)”[4]。這背后是西方列強(qiáng)開(kāi)始通過(guò)航海活動(dòng)對(duì)廣大的非西方地區(qū)進(jìn)行瓜分。而這一歷史過(guò)程的物質(zhì)基礎(chǔ)、經(jīng)濟(jì)動(dòng)力及其如何打著諸如“自由貿(mào)易”之類(lèi)意識(shí)形態(tài)說(shuō)辭,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也進(jìn)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5]由此可見(jiàn),宮崎筆下的倭寇根本不像生活在古代東亞世界里的人,而是神似近代西方全球擴(kuò)張中的各色先驅(qū)者。在這樣的論述框架下,倭寇就成為具有現(xiàn)代意識(shí)的群體,他們不但具有類(lèi)似“契約精神”的氣質(zhì),拯救深受中國(guó)“體制”束縛的“民間商人”,而且通過(guò)一系列俠義之舉,敲開(kāi)封閉的中國(guó)的大門(mén)。
正像早期殖民者深入美洲、非洲“不毛之地”的勇武之舉在近代西方廣受傳播一樣,宮崎也毫不吝嗇地稱(chēng)贊倭寇入侵中國(guó)。在他筆下,倭寇的“目的也絕不是掠奪,他們只是出于哥們兒意氣,參與了遭受官府迫害的中國(guó)同類(lèi)的復(fù)仇運(yùn)動(dòng)中去”。因此,“倭寇絕不是以中國(guó)民眾為敵的”。更有甚者,“倭寇是戰(zhàn)爭(zhēng)的天才。有中國(guó)內(nèi)地人做向?qū)В瑢?duì)地理形勢(shì)又非常了解,總能夠通過(guò)伏兵的戰(zhàn)術(shù)以寡敵眾,尤其是日本刀的使用出神入化,讓膽小的明朝官兵聞風(fēng)喪膽”。[3]35,36如果這樣的邏輯可以成立,那么斗轉(zhuǎn)星移,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日本侵華也不是為了掠奪,而是出于另一種“哥們兒意氣”——“大東亞共榮”,把中國(guó)從西方勢(shì)力的魔爪下解救出來(lái);日本只是與“冥頑不化”的中國(guó)抵抗者為敵,而不以中國(guó)民眾為敵。至于日軍如何“威武善戰(zhàn)”,更是在大量的宣傳品中廣為傳播。總之,在明代倭寇身上,宮崎或許看到了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分子的侵華日軍之先驅(qū)。
同樣地,就像西方殖民者把在非洲、美洲的活動(dòng)形塑為“教化”當(dāng)?shù)孛癖姟⑦M(jìn)行開(kāi)發(fā)建設(shè)一樣,宮崎強(qiáng)調(diào):“倭寇的暴行絕不是一種營(yíng)利行為,當(dāng)然也不是日本人樂(lè)意這么做。日本人最終還是希望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下從事通商貿(mào)易。”[3]39“日本人本來(lái)就愛(ài)好和平,自始至終都只是想與中國(guó)民眾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下進(jìn)行通商貿(mào)易。如前所述,只是在萬(wàn)不得已的情況下加入到了中國(guó)官府與民眾的斗爭(zhēng)中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倭寇。”[3]46只要對(duì)明代后期至20世紀(jì)40年代的中日關(guān)系史稍有了解,就不禁會(huì)對(duì)宮崎的這番論調(diào)啞然失笑。破壞東亞“和平環(huán)境”的禍?zhǔn)拙烤故钦l(shuí),日本各方力量有多少是“本來(lái)就愛(ài)好和平”的,這些問(wèn)題的答案其實(shí)非常清楚。可關(guān)鍵在于,宮崎認(rèn)為他的這項(xiàng)研究是在“深入事實(shí)的內(nèi)部,闡明事情的真相”[3]47,這真是讓人感到錯(cuò)愕。
更讓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宮崎此論在戰(zhàn)后似乎也沒(méi)有太多變化,這或許是在實(shí)踐他對(duì)戰(zhàn)后進(jìn)步思潮的不快。在影響頗廣的《亞洲史概說(shuō)》一書(shū)中,他如是敘述倭寇:
所謂的“倭寇”,是由于明朝行之過(guò)甚的鎖國(guó)政策本身出現(xiàn)了破綻所導(dǎo)致的……自宋元以來(lái),日本人與中國(guó)沿海民眾就已經(jīng)開(kāi)始進(jìn)行自由貿(mào)易了,但明朝政府采取鎖國(guó)政策之后,自由貿(mào)易就變成了走私貿(mào)易。而嘉靖皇帝對(duì)走私貿(mào)易的壓制,與其說(shuō)針對(duì)日本人,不如說(shuō)是針對(duì)中國(guó)人,試圖以此對(duì)民眾加以嚴(yán)厲的控制。為了反抗這一官方壓制,中國(guó)人只好勾結(jié)日本人掠奪沿海城市,這便是倭寇的真相。[6]
很明顯,相比于戰(zhàn)時(shí),這些敘述更“學(xué)術(shù)化”、更“平實(shí)”,但核心觀點(diǎn)依然保留著。宮崎晚年自言:“本國(guó)人未必最了解自己的歷史,外國(guó)人的理解常常更加準(zhǔn)確,這可以說(shuō)是歷史研究中特有的趣味所在。”[7]不知對(duì)于明代的這段歷史,宮崎是否也覺(jué)得自己較之中國(guó)人理解得“更加準(zhǔn)確”?從他在《亞洲史概說(shuō)》中的倭寇“真相”論與戰(zhàn)時(shí)觀點(diǎn)一脈相承來(lái)看,也許他真的是這么認(rèn)為的。而這一點(diǎn)恰恰是今人在閱讀宮崎史論時(shí)不能忽視的。
此外,在《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一書(shū)里,宮崎收錄了一篇名為“中國(guó)的開(kāi)放與日本——中國(guó)式的體制與日本式的體制”的文章。此文意在通過(guò)對(duì)比中日兩國(guó)在近代面對(duì)西洋文明時(shí)的不同態(tài)度,凸顯中日之間“體制”的巨大差異。在他看來(lái),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就有獨(dú)特的體制,歷代王朝皆以維護(hù)這一體制自任,面對(duì)外來(lái)文化,在無(wú)損此體制的完整性時(shí),中國(guó)古人尚能汲取一二,一旦覺(jué)得外來(lái)文化會(huì)對(duì)中國(guó)體制造成巨大沖擊,那么王朝統(tǒng)治者就會(huì)選擇深閉固拒,致使國(guó)勢(shì)衰微。顯而易見(jiàn),他如此敘述中國(guó)歷史,自然是為了拿來(lái)與日本體制做對(duì)比,以此彰顯后者的優(yōu)越性。宮崎聲稱(chēng),正因?yàn)椤叭毡静粩嗟嘏c中國(guó)式體制抗衡,堅(jiān)持采用日本式的體制”,所以日本一直希望與中國(guó)建立“對(duì)等”的外交關(guān)系,“從對(duì)等的立場(chǎng)展開(kāi)兩國(guó)之間的外交關(guān)系必定是最自然的想法,這種平等精神在東亞范圍內(nèi)是日本所獨(dú)有的”,甚至此乃“日本式體制對(duì)于世界歷史的意義”。[8]128只是不知宮崎下此結(jié)論時(shí),是否考慮過(guò)日本長(zhǎng)期對(duì)朝鮮與琉球的壓迫姿態(tài)。
當(dāng)然,宮崎此論的更直接目的是論述近代中國(guó)與日本不同的歷史進(jìn)程。他指出,正由于日本體制具有“平等”精神,所以它“自身也始終是開(kāi)放的。對(duì)于外國(guó)文明,無(wú)論何時(shí)都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且迅速將其日本化,用以強(qiáng)化日本的體制。我們應(yīng)當(dāng)立足于這樣的觀點(diǎn),來(lái)重新認(rèn)識(shí)日本式體制的長(zhǎng)處”[8]141。此文撰寫(xiě)于20世紀(jì)40年代,如果認(rèn)為近代“外國(guó)文明”的“精華”是帝國(guó)主義、殖民主義、軍國(guó)主義的話,那么當(dāng)時(shí)的日本確實(shí)吸收得非常迅速,并且用“萬(wàn)世一系”“八纮一宇”“王道樂(lè)土”等本土概念文飾之,東洋風(fēng)與西洋景混為一體。而在宮崎眼里,這樣的日本體制堪稱(chēng)東亞之光:
東亞諸國(guó)有時(shí)也對(duì)中國(guó)舊體制發(fā)起反抗,但最終都被卷入其中,只有日本凜然獨(dú)立,維持著獨(dú)特的日本式體制,并不斷促使中國(guó)式體制的反省,這在歷史上值得大書(shū)特書(shū)。在歐美的壓迫下,東洋各國(guó)或被征服,或淪為半殖民地,唯有日本不糾纏于應(yīng)對(duì)的方式,只要無(wú)礙大局,就可以聽(tīng)該聽(tīng)之言,斥該斥之物,也就是在這樣的過(guò)程當(dāng)中,日本式體制的基礎(chǔ)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加強(qiáng)。[8]142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以來(lái),日本一直覬覦中國(guó)的領(lǐng)土,甲午中日戰(zhàn)爭(zhēng)之后,更是在中國(guó)搶奪了大量經(jīng)濟(jì)利益。說(shuō)近代日本工業(yè)迅速發(fā)展的第一桶金來(lái)自對(duì)中國(guó)的掠奪也不為過(guò)。凡此種種,在宮崎那里都變成了日本處心積慮地促使中國(guó)從舊體制中“反省”,并認(rèn)為應(yīng)被“大書(shū)特書(shū)”,這真不知該從何說(shuō)起。而更讓他備感“驕傲”的是,面對(duì)歐美的壓力,日本并未屈服,依然保持獨(dú)立,這更讓日本成為亞洲各國(guó)的“榜樣”。
只是隨著“二戰(zhàn)”結(jié)束,日本戰(zhàn)敗,日本國(guó)內(nèi)瞬間從過(guò)往的高傲自大變成對(duì)占領(lǐng)軍的卑躬屈膝、極盡諂媚之能事。不少日本國(guó)民寫(xiě)信給美國(guó)占領(lǐng)者,讓后者嚴(yán)厲處分戰(zhàn)時(shí)日本領(lǐng)導(dǎo)人,各種檢舉揭發(fā)更是層出不窮。對(duì)于此時(shí)日本的實(shí)際統(tǒng)治者麥克阿瑟,《朝日新聞》稱(chēng)贊他為“我們的父”。不少女子甚至寫(xiě)信給他,強(qiáng)烈表達(dá)“我想給你生孩子”的愿望。[9]或許是感受到了這樣的氛圍,宮崎在發(fā)表于1958年的《東洋史上的日本》一文里批評(píng):“戰(zhàn)爭(zhēng)期間日本的狂妄自大,一旦戰(zhàn)敗馬上就完蛋了!于是又出現(xiàn)了無(wú)止境的卑躬屈膝的自卑感,于是又出現(xiàn)了日本民族是未開(kāi)化的、野蠻的、不干凈的、不道德的,是罪人,日本的歷史完全是捏造的,明治維新也是騙人的假玩意兒,日清甲午戰(zhàn)爭(zhēng)、日俄戰(zhàn)爭(zhēng),都是日本資產(chǎn)階級(jí)搞的侵略勾當(dāng)?shù)日撜{(diào)。”[10]195-196而回應(yīng)之道,在宮崎看來(lái),就必須“把日本的歷史完全客觀地放在世界歷史中來(lái)加以考察”[10]196。由此可見(jiàn),宮崎史學(xué)的世界史視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助這一方式來(lái)彰顯日本自身的特色。
宮崎強(qiáng)調(diào),世界各地文明無(wú)不處于各種聯(lián)系當(dāng)中,文化流動(dòng)貫穿歷史進(jìn)程,只是不同文化一旦相遇,是互相交融,抑或彼此對(duì)抗,在歷史中具有不同的顯現(xiàn)罷了。基于此,他認(rèn)為日本文化在此流動(dòng)性的背景下,可以稱(chēng)為“終點(diǎn)站文化”或“中轉(zhuǎn)站文化”:
說(shuō)最近代的日本文化是中轉(zhuǎn)站文化……我的意思是,經(jīng)過(guò)選擇之后,合格的東西傳播了進(jìn)來(lái),合適的東西保存了下來(lái)。為了使之進(jìn)一步符合自己的審美觀,不停地在加工著,無(wú)論它出自哪里,經(jīng)過(guò)兩三代,就都變成了優(yōu)秀的本地文化,然后再與新來(lái)的外來(lái)文化進(jìn)行較量,反復(fù)進(jìn)行選擇、同化的過(guò)程。[10]201
這個(gè)觀點(diǎn),其實(shí)與戰(zhàn)時(shí)宮崎對(duì)“日本體制”的稱(chēng)贊在基本結(jié)論上并無(wú)不同,都是為了突出日本能基于自身立場(chǎng),不斷吸收、消化外來(lái)新文化的“特性”。只是這個(gè)“特性”,在戰(zhàn)時(shí)可以用來(lái)證明日本文化乃東亞翹楚,在戰(zhàn)后則可用來(lái)證明日本文化自有生命力,不應(yīng)遭受前文所述的各種非議。所以宮崎指出:“所謂新文化,本來(lái)應(yīng)該由內(nèi)部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但是,創(chuàng)造必須在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并且還要讓這些有利條件實(shí)現(xiàn)最佳配比之后才有可能產(chǎn)生。”[10]202值得注意的是,這番話絕非泛泛而談,而是為了突出“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前提必須是一切有利條件在這里實(shí)現(xiàn)了最佳的結(jié)合,如果我前面所說(shuō)的話不錯(cuò)的話,那么應(yīng)該說(shuō)唯有今天的日本才具備了這樣的資格”[10]203。回到歷史語(yǔ)境,“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亞洲許多被殖民國(guó)家紛紛獨(dú)立,新中國(guó)成立更是影響了世界格局,舊的殖民體系在亞洲早已土崩瓦解。照理說(shuō),日本過(guò)去建立在舊秩序之上的優(yōu)越感應(yīng)該降溫才是,可這些時(shí)代變化似乎對(duì)宮崎沒(méi)什么影響,他繞了一個(gè)大圈子,最終還是在宣稱(chēng)日本文化在亞洲的優(yōu)越性。
因此,就很難認(rèn)為宮崎的史學(xué)思想在戰(zhàn)后有什么巨大變化。在《亞洲史概說(shuō)》里敘述近代日本歷史的部分,他專(zhuān)門(mén)用一節(jié)來(lái)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功與罪”。作為中國(guó)人,筆者實(shí)在難以理解“二戰(zhàn)”中的日本究竟何“功”之有。而所謂“罪”,在宮崎筆下,不是“陸軍軍官演出的腳本總是過(guò)于脫離現(xiàn)實(shí)”,就是海軍首腦“沒(méi)能改變思路,而是始終堅(jiān)持巨艦巨炮主義”。[6]355,356總之,都是屬于戰(zhàn)略上的失誤,而非對(duì)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本身進(jìn)行否定。這就好比“九一八”事變的幕后策劃者石原莞爾并不反對(duì)侵吞中國(guó),只是不主張操之過(guò)急地借盧溝橋事變來(lái)造成中日全面開(kāi)戰(zhàn)而已。如果今人不會(huì)因?yàn)槭暮笠环N態(tài)度而認(rèn)為他是反戰(zhàn)人士,那么對(duì)于宮崎的“二戰(zhàn)”觀,也可用相似的邏輯來(lái)審視。
1992年,宮崎在為自己所著的《中國(guó)史》撰寫(xiě)跋文時(shí),談到該書(shū)在中國(guó)臺(tái)灣有中文譯本,在韓國(guó)有韓文譯本,并且覺(jué)得會(huì)“一定程度流傳于世”,于是感慨:“像《中國(guó)史》這種題目的著作,雖然有許多作者以各種語(yǔ)言撰寫(xiě),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同類(lèi)書(shū)中,只有我的書(shū)被翻譯到中國(guó)臺(tái)灣與韓國(guó)。”[11]489他由是展開(kāi)聯(lián)想:
與這兩地相反,法國(guó)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屬印度、美國(guó)殖民地的菲律賓、曾為荷蘭領(lǐng)土的印度尼西亞等國(guó),主權(quán)國(guó)因擔(dān)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發(fā)現(xiàn)最近近世文明長(zhǎng)處的機(jī)會(huì),結(jié)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會(huì)的落后。雖然是關(guān)乎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問(wèn)題,但幾乎從未聽(tīng)說(shuō)過(guò)有哪個(gè)歷史學(xué)家曾經(jīng)指出這種真相,這是為何?[11]490
很明顯,這番話的未盡之言是通過(guò)強(qiáng)調(diào)法國(guó)、英國(guó)等老牌殖民主義國(guó)家在殖民地沒(méi)有用“新教育”去教化當(dāng)?shù)孛癖姡瑢?dǎo)致這些地區(qū)享受不到“近世文明”,來(lái)突出日本在中國(guó)臺(tái)灣、韓國(guó)的殖民活動(dòng)是盡了“責(zé)任”的,這兩處地方擺脫“落后”狀態(tài),是有日本殖民者的一份“功勞”的。當(dāng)然,宮崎在沉浸于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國(guó)臺(tái)灣、韓國(guó)傳播的同時(shí),或許有意忽視了“二戰(zhàn)”后許多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家的著作也在日本頗為流傳,而這些史學(xué)著作背后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毛澤東選集》,更是長(zhǎng)期廣受日本青年歡迎。不過(guò),及至去世前宮崎依然保持這種殖民主義的幻覺(jué),也實(shí)在讓人忍不住“嘖嘖稱(chēng)奇”。試想如果與宮崎具有相似理念的人,看到他的許多著作也在當(dāng)代中國(guó)大有市場(chǎng),會(huì)不會(huì)也會(huì)聯(lián)想到“二戰(zhàn)”期間日本在中國(guó)占領(lǐng)區(qū)的各種作為,會(huì)不會(huì)也將其視為在給中國(guó)人民普及“新文明教育”?從宮崎的汪精衛(wèi)研究與今天國(guó)內(nèi)一些對(duì)汪偽政權(quán)及其首腦進(jìn)行另類(lèi)闡釋的論著在結(jié)論上頗有相似性來(lái)看[12],似乎筆者并非杞人憂天。
注釋
[1][日]宮崎市定.前言[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14.
[2]關(guān)于宮崎對(duì)于戰(zhàn)后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態(tài)度,參見(jiàn)[日]宮崎市定.中國(guó)歷史的分期[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414-1418.
[3][日]宮崎市定.倭寇的本質(zhì)與日本的南進(jìn)[A].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4][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M].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
[5][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節(jié)選本)[M].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8-59.
[6][日]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shuō)[M].謝辰譯.北京:民主與建設(shè)出版社,2017.
[7][日]宮崎市定.前言[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61.
[8][日]宮崎市定.中國(guó)的開(kāi)放與日本——中國(guó)式的體制與日本式的體制[A].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9][美]約翰·道爾.擁抱戰(zhàn)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日本[M].胡博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8:207,208.
[10][日]宮崎市定.東洋史上的日本[M].日出之國(guó)與日沒(méi)之處.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1][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中國(guó)史[M].焦堃、瞿柘如譯.北京:民主與建設(shè)出版社,2019.
[12][日]宮崎市定.馮道與汪兆銘[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xué)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93-1395.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
(責(zé)任編輯?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