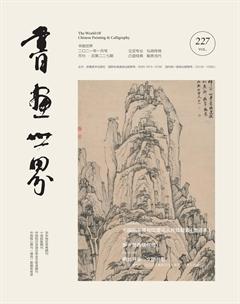詩畫傳家
包若冰



內容提要:吳茀之對中國畫傳統的堅守與其家學的影響密不可分。浦江縣前吳村吳茀之祖上以詩畫傳家,文士輩出。吳茀之的父親吳申卿與舅父黃尚慶皆善書畫,詩文修養深厚。兄長吳士維對自然生活觀察入微,吳茀之與其兄長一樣對寫生有深刻見解。吳茀之自小耳濡目染,以文人畫家要求自身,始終秉持中國畫的文學根基與獨立性發展,并將其作為中國畫教育需要承繼的傳統貫徹于教學之中。
關鍵詞:吳茀之;吳渭;黃尚慶;吳士維
吳茀之生于原金華府浦江縣前吳村的一戶書畫世家,祖上在江南地區頗有名望,父親吳申卿亦是清末的秀才,母親黃氏勤儉持家。黃氏于吳茀之十歲時去世,父親吳申卿續娶了一位潘氏。吳申卿有三個兒子,長子吳士維亦善詩文書畫,二子吳士續經營家業,幼子吳士綏(吳茀之)亦走上書畫藝術之路。吳茀之的舅父黃尚慶是清朝晚期浦江地區著名的書畫家,黃尚慶的女兒便是吳茀之的妻子。吳茀之家中詩文書畫的氣氛十分濃郁,吳茀之自小耳濡目染,立身處世與藝術追求皆受家學深刻影響。
一、清翁后人
浦江縣素來被稱為書畫之鄉,文風昌盛,吳氏祖上名士輩出,吳渭、吳萊、吳鳳來等皆為江南地區頗具聲望的文士。其中,吳茀之對吳渭十分尊崇。吳渭為宋末元初人士,字清翁,號潛齋。宋朝末期,吳渭曾擔任義烏縣令,入元后便回到浦江吳溪邊隱居,寄情于山水詩文,未再出仕。吳渭與謝翱等四人共同創立了“月泉吟社”,“延請著名文人方鳳、吳思齊、謝翱來家,共同訂定社約、題意、暫文、詩評等章則,然后發出詩題,征賦‘春日田園雜興”。此事在當時引起眾多關注,尤其在江南地區的影響很深。蘇、浙、閩、桂、贛等各省名士寄來詩稿兩千七百三十五首。經過評定,選取其中最優者六十名的七十四首詩,以名次排列,附上評語,編輯成《月泉吟社》。《月泉吟社征詩章則》中記載吳渭等人此次評選的標準:“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卻田園,全然泛言化物耳。”即以情景交融、辭與意會、物與我相一致者為佳,實質是托詩文以言志。《浙江人物簡志》中亦記載:“這些表面謳歌田園閑適生活之作,實則多寓遁世之意,并隱去了作者真實姓名,反映了當時文人對元朝統治者的消極反抗。”吳渭不慕官場名利,寄情于詩文山水之中,全其文人氣節。
吳茀之對吳渭深厚的詩文修養與文人品性很是憧憬,有兩方“清翁后人”印章,多次在畫作上鈐印“清翁后人”以此自稱。吳渭的文人品質對吳茀之的立身行事影響頗深。吳茀之始終秉持中國文人的性情修養,為人端方儒雅,言行篤慎,對國家與社會抱有深切的責任感,對中國畫的繼承與發展具有崇高的使命感,面對20世紀西方繪畫的沖擊,始終堅守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畫傳統的承繼。
二、黃尚慶的詩畫熏陶
吳茀之的父親吳申卿、舅父黃尚慶皆于詩畫修養深厚,于浦江地區頗具名聲。據記載,父親吳申卿是清朝末期的秀才,善詩文,亦善書畫,特別擅長白描仕女與鐘馗。黃尚慶十八歲時考取秀才,縣試、府試均獲第一名,文采斐然。據施明德所言,黃賓虹十七歲時亦曾慕名向黃尚慶習文學詩,可見其詩文學養廣受認可。吳茀之評價黃尚慶“一生治學甚勤苦,博覽群書,精詩文,尤工書畫,有大家風,名振浙東,其書畫散于各地頗多,其詩稿盡毀于回祿,未傳”。我們從字里行間皆可感受到吳茀之對黃尚慶詩文書畫的成就頗為推崇。黃尚慶對吳士維、吳茀之兄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藝術老師,他的藝術追求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茀之兄弟的藝術品位與發展方向。
黃尚慶的書法從顏體入手,勁悍縝密,后學李北海,書風圓潤厚重,骨肉兼備。黃尚慶善作大寫意,尤其擅畫蘆雁,取法邊壽民,追求“遺貌取神”,頗有意境。施明德評述黃尚慶的筆墨特點:“作畫用筆靈變,用墨鮮活,書法凝練而勁挺,有碑版的風韻。”黃尚慶的繪畫筆墨與書法的用筆特點如出一轍,作畫用筆靈活多變,中側鋒運轉變通,墨色潤澤,層次豐富。張岳健所著《吳茀之》中記載,吳茀之少年時期就以黃尚慶與吳士維的作品為臨本進行臨摹,且仿照他們題詩鈐印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上落款蓋章。可以說吳茀之少年時期建立的藝術審美便受到黃尚慶藝術風格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吳茀之意欲脫離吳昌碩的繪畫面貌尋求自身風格,始終堅持研習詩文與篆刻,將詩書印作為中國畫的重要組成因素。
三、吳士維與吳茀之的寫生觀
吳茀之的長兄吳士維自小跟隨父親學習詩文,亦受黃尚慶的書畫指導,于20世紀30年代便已聞名鄉鄰。吳士維長年居于鄉鎮,淡于名利,喜好垂釣,對農村的生活十分熟悉,所見事物多為市井中少見,因此畫作的題材較為廣博。吳士維以大寫意水墨出之,作品多有畫趣,透露著山水之間的野逸與靈秀。吳茀之曾贊許其兄吳士維畫作之妙,作序并賦詩云:“攘攘胡為者,橫行一代中。奇觀今百出,草莽盡英雄。”所言便是指吳士維畫中題材貼近百姓生活所見,為前人很少入畫之題材,且能夠以筆墨表現平常之物的精神,以筆墨展現平凡中的不凡。吳茀之作畫亦是如此。吳茀之自上海美專畢業后的作品飽含生活意趣,致力于擴大畫題,將以往不常入畫的蓖麻、馬纓花等入畫,意欲描繪一系列中草藥為題材的作品,20世紀50年代后的作品更多是描繪鄉村勞動生產生活之作。
吳士維對所畫對象觀察入微,對描寫自然景物的法度有獨到的見解,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吳士維以精于畫蟹聞名,吳茀之對吳士維畫螃蟹做出非常高的評價。吳茀之言:“同懷兄克持,以畫蟹鳴于時,觀今之畫蟹出其右者,余未見也。”吳士維的《百蟹圖》繪有大小螃蟹近百只,情態各異,妙趣橫生,形神畢肖,這是未經過細致的觀察所不能達到的。吳士維對自然的觀察體悟十分精心,尊重物象真實面貌,以發展的、全面的觀念體悟自然,感受生長凋落、四時變化。吳士維認為作畫首先便要體察萬物,不將它們作為自然的生命對象,則無法體悟其精神,更不用說將其繪制出來。他曾說:“別以為幾個葉片,沒有講究,世間萬物都有幼年、中年、老年。可很少有人知道,蘆葦也有生長的過程,它初生曰葭,中期曰蘆,長大才叫葦。它是叢生植物,都要在一叢中展現出層次來。再說蹼雁,俗稱水鴨,比家鴨小,背有花紋。《爾雅·禽科》叫‘鳧雁,其足蹼,其踵,企。就是腳爪間有幕蹼,可以在水中游泳,在空中能飛,……不知這些,就畫不成。”吳茀之在中國畫創作中對寫生的重視與其兄吳士維如出一轍。吳茀之十幾歲時便整日盯著鄉間的花草蟲魚,默默地記下它們的生長特征,以筆墨表現于紙上。吳茀之非常重視對自然界與生活中事物的觀察寫生。吳茀之不僅將寫生作為理解事物理法、搜集繪畫素材的方式,更是將其作為加深繪畫創作理解、拓展創作手法與意趣的途徑。吳茀之20世紀40年代最為滿意的作品《鱉》,便是生活中觸機而發,經過細致觀察所得,并對此作念念不忘。
20世紀上半葉浦江地區的中國畫風尚受 “揚州畫派”的影響頗深,黃尚慶與吳士維的繪畫面貌亦是如此,表現為疏放的寫意畫風。他們的作品中對邊壽民、李鱓等人畫風的融合吸收較為明顯。吳茀之曾背擬黃尚慶所畫蘆雁、吳士維所畫螃蟹,且在畫作上題幾行詩跋,落款鈐印。吳茀之少年時期跟隨黃尚慶與吳士維學畫,耳濡目染于他們的藝術審美與風格,對“揚州畫派”的畫風有所了解。吳茀之在舅父與兄長的藝術審美影響下,對疏放恣意的寫意畫亦頗有好感,為其日后創作風格轉向多變疏放打下基礎。吳茀之少年時期臨摹蔣廷錫、惲壽平等工整精致的作品,前往上海美專求學時被渾厚磅礴的金石寫意畫風吸引,轉而走上大寫意的創作之路。20世紀30年代回到上海后,經過師友點撥,他決心改換創作面貌,不再一味追求缶老的寫意畫風,力求學習“揚州八怪”的革新精神與個性表達。吳茀之于蘭花作品上題字“我畫放浪疏形骸”,可見他對自己的中國畫創作風格的發展傾向已經逐漸與金石寫意畫風拉開距離,轉而向疏放灑脫的繪畫面貌發展。吳茀之時常擬李鱓、任伯年的筆意作畫,進一步取法徐渭、陳淳、石濤、八大,多方取經,中國畫面貌愈加超脫靈變。
由此可見,吳氏以詩文書畫傳家,先祖多有學識淵博之輩,于江南地區負有盛名。吳申卿、黃尚慶、吳士維等皆有較為深厚的詩文涵養,兼善書畫。黃尚慶與吳士維皆是當時聞名當地的書畫家,書法渾厚率意,繪畫崇尚“揚州畫派”的畫風。吳氏家族重視詩文修養、喜愛書畫的文人傳統對吳茀之的中國畫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吳茀之在中國傳統文學與繪畫的熏陶下成長,以中國文人的行事持身為準,文學修養與學術研究皆是如此。吳茀之對中國畫“詩、書、畫、印”全面修養的倡導與中國畫發展的獨立性的堅守脫離不了其家學淵源的影響。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