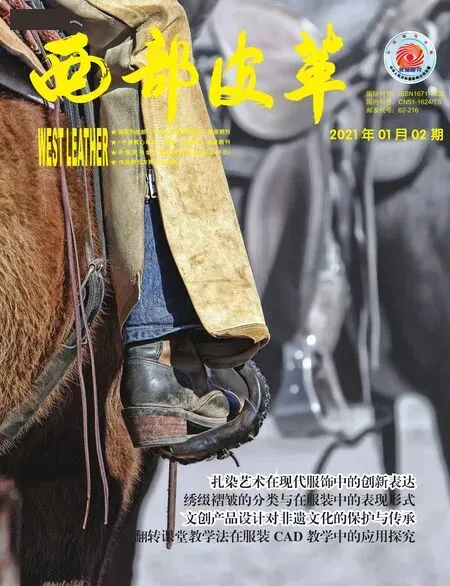西南深山里“別樣精致”的圖像敘事
——銅鼓村苗族婦女民間繪畫藝術探析
姚紹將
(凱里學院,貴州 凱里 556011)
1 苗族婦女文化與民族傳統文化生態
人類文化是人類生命活動的結果及其積累積淀。婦女文化則是指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及行為活動所創造具有一定性別特質的文化。苗族是沒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民族文化的傳承主要依靠的是口傳身授(言傳身教)和視覺圖像的傳達。苗族婦女文化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個特點是,苗族婦女傳統文化比苗族男性文化更具民族文化內涵和特征代表性。“男耕女織”的農耕文明社會分工在苗族社會里也并非界線分明。從苗族社會生活歷史我們可以找到證據,在當下的調研也更是證明了這一點,苗族婦女熱情好客“上得廳堂,下得廚房”,也勤勞能干,耕田種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從視覺文化方面而言,苗族傳統工藝文化、傳統婚戀嫁娶、原始宗教信仰文化等等方面,都以婦女的生活、地位、歷史文化等得到主體性彰顯為重要內容。比如苗族蜚聲海內外的蠟染、刺繡、銀飾、剪紙等傳統手工技藝,皆以苗族婦女為造物主體;雖然銀飾技藝是苗族男性工匠所制造的,但該工藝真正完成應當是盛裝時的美麗無比的苗族婦女身上。苗族服飾文化是苗族民族身份和文化特點的集中標識物之一,但又以婦女傳統盛裝服飾(文化)尤為顯著。再如苗族節日文化,除了有專門為婦女活動而生成的節日姊妹節外,絕大多數的節日,如吃新節、苗年、歌節等等節慶中多姿多彩、歡歌盛舞的婦女往往是最具吸引人們的眼睛群體。即使是在當下苗族腹地城市化城鎮化高速“擴展蔓延”的狀況中,苗族傳統村落的婦女除了承擔繁重的農務,繁瑣的家務之外,部分苗族婦女還擠出部分時間進城鎮務工,解決家庭部分經濟需求。同時我們發現,大旅游時代中苗族婦女形象獲得前所未有的傳播或彰顯,婦女傳統文化得到多樣性、多維度的調適和整合。我們在國內外的影視中和國際化大都市的某處廣告宣傳欄中看到諸多苗族少女們的美麗形象,她們不僅是民族家庭主婦,更是鄉村旅游和民族文化傳播的“形象大使”,也正如詩人所說的,盛裝的苗族婦女個個是舞蹈和歌唱家,本身也是藝術品。因此,苗族婦女文化更具苗文化的典型內涵和外延,是苗族文化生態的重要構成部分。
不言而喻,苗族民間繪畫并非只有苗族婦女進行創作,只是苗族婦女農民畫藝術家一直是重要的創作主體。究其原因除了有著自身民族文化和婦女文化的場域根源外,與苗族婦女的傳統手工藝有著密切的關系。苗族有著很多經典的婦女傳統手工藝,如苗族剪紙、蠟染、刺繡,在這些經典婦女工藝的工序之中中經常包含先在紙上描繪出需要剪、染及刺繡的圖案圖像,然后才開始進行下一步工序的前提。從諸多苗畫和刺繡圖案圖像的比較來看,都有著很多相似點。苗族婦女傳統工藝的基礎手繪,其實就是苗族婦女民間繪畫的圖案或圖式。這樣,也就難怪有學者認為苗族民間繪畫源于苗族人民的傳統手工藝,或者說苗族民間畫是在苗族手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為以上提及的苗族傳統工藝技能都是婦女所掌握,因此,苗族婦女成為了銅鼓村苗族民間畫的最大群體,從技能上來說也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部分苗族婦女一邊從事傳統手工藝,一邊從事民族民間繪畫的創作,部分逐漸脫離了工序復雜的傳統工藝,單純的從事苗畫的創作。更重要的是傳統手工藝是有溫度和靈性生命活動,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強調的,人類的傳統手工藝是人類最古老、最正直的職業,[1]也如日本工藝美學家柳宗悅也指出手工藝是最誠實的藝術。[2]也就是說手工藝是最能體現人類正直、誠實的珍貴品質。其實,銅鼓民間苗畫其實也可以說是具有這些珍貴品質民間藝術。
2 苗族婦女民間畫的性別審美特色
從苗族農民畫的產生和發展來看,苗族婦女扮演著主要角色。苗族婦女農民畫也逐漸成為苗族婦女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從大量的農民畫藝術作品中我們也看到這一點,亦即苗族婦女農民畫體現著苗族婦女的獨特審美觀念。首先,大膽、夸張的色彩運用是苗族農民畫最大特征。馬克思指出“色彩的感覺是一般美感中最大眾化的形式。”色彩是最能體現感性的視覺形式美的構成因素,與婦女作為感性的存在有著天然內在關系,與沒有文字的民族,及文化欠缺的民族婦女有著十分親和的微妙心理聯系。婦女在服飾穿著與搭配上的大紅大紫被認為是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艷麗、飽滿、明快、對比強烈的色彩傾向往往是女人色彩意識的“專利”。因此,在苗族婦女農民畫在用色上色彩明快、鮮艷,大紅大綠,對比非常強烈,隨心敷彩,隨意敷色。發展到新時代的苗族婦女農民畫幾乎都以熱烈激昂,歡快喜悅的色調來描繪苗家幸福生活,幾乎都以溫暖溫馨、多姿多彩的色韻講述民族傳說和故事。通過強烈色彩更能直觀感性、酣暢淋漓地表達以熱情奔放著稱的苗族婦女的審美情感。相對于線描作為理性、冷靜的視覺形式表達,色彩是最能表達人的情感的視覺形式語言要素,也是一種女性藝術常用形式語言。這也是苗族農民畫逐漸變成以婦女為創作主體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苗族婦女農民畫偉大的藝術想象力和詩性思維。想象力是藝術創造創新的強大動力,詩性思維是充滿想象力的童話、神話思維模式。苗族婦女的農民畫表現出了強大的藝術想象力。上文提及在鮮明和強烈的色彩運用是想象力的重要構成部分,另外,在構圖上散點透視為主,平視與俯視多視角結合,根據作者的民族民間文化基礎和審美創造的無限空間想象構圖,變形夸張,拙中藏巧。在創作主題上,也充滿了民族神話、傳說、故事的基底和無限想象。調研中,我們也發現很多苗族婦女農民畫創作者會把自己圖像中的“故事”娓娓道來,指著畫中神態各異,夸張造型的本民族先祖或神靈,驕傲地介紹,深情地講述……敘事飽滿,更充滿了古樸浪漫氣息,遵循著苗族婦女別樣精致的圖像敘事,仿佛進入一個神話、童話的縹緲幻境,而圖像的故事也往往擁有著歡喜、圓滿的結局。最后,是苗族婦女民間畫的婦女工藝特點。苗族婦女傳統工藝是基于婦女對所處世界的感受、認知和理解,最終形成民族婦女知識文化。比如苗族婦女傳統工藝的紡、織、染、印等,都源于與靜態的、細膩的、有色的、溫馴的事物打交道,比如纖柔的植物(纖維)、溫馴的動物以及能獲得標識的植物染料等等,也使得苗族民間畫有著工藝繁復細膩,畫面布置充實,極具親和真誠的吸引力和裝飾效果等特點。
3 苗族民族民間繪畫的保護與利用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和大旅游時代,鄉村傳統優秀民族文化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百姓對新時代美好生活追求也反應在民族民間文化之中,當然我們更應當正視優秀民間傳統文化遭遇的困境。苗族農民畫創作后繼無人是首要的直觀困境。調研顯示,能夠專心地從事苗族農民畫創作的畫家都是發髻花白的老年人和不諳世事的孩童。如銅鼓村熟練的農民畫家共計30余位,苗族年長的老人占據絕大部分比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現代社會工業的、城鎮的和科技的生活生產方式強而有力地沖擊、擠壓著苗族地區傳統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根本的原因。生活方式的轉變往往導致審美觀念的改變,都市生活體驗和現代網絡科技時代的審美觀念促使苗族年輕人尋求新的“刺激”和“洗禮”,導致苗族農民畫后繼無人。其次,農民畫的民族民間原生性文化生態土壤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或正在喪失,苗族農民畫的文化生態正在被取代或破壞。比如黔東南銅鼓村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正在被破壞。城鎮化速度的加快,銅鼓村周邊自然生態逐漸被現代猶如雨后春筍的城鎮建筑吞噬,傳統生活方式被游離在城鎮邊緣的生活作息方式取代,等等。
苗族民間繪畫正在面臨著機遇和挑戰。針對諸多存在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通過業內人士的深入調研形成一個全面的調查報告,找出主要問題,分析其內在與外在原因,在兼顧傳統的與現代的、地方的與國際的、內在的與外在的等幾個方面的原則下,再制定科學、合理、可行的體系性措施。首先,從民族民間藝術苗畫的內部發展而言,一是積極拓展新時代苗族民間畫創作題材的多樣性。二是汲取不同藝術的視覺形式語言之營養,提高苗畫獨特的藝術審美形式、內涵和文化創新能力。在大旅游和保護優秀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苗畫走兩條路線:一條路是完整保持其原生性,走博物館、藝術收藏館“珍品”收藏拍賣等路徑,以稀缺性、珍藏型提升農民畫藝術的文化歷史價值和經濟價值;另外一條路是選擇其中可以融入的時代時尚要素通過創意開發、策劃和現代產業運營來發展,結合大旅游休閑時代商品需求,來推薦民族民間藝術經典精品塑造。這兩條路徑既遵循著民族民間藝術自身內在發展規律,又結合時代發展,市場和社會需求,能夠有效保護民族民間藝術文化生態圈的同時,也符合當下藝術文化繼承、創新和利用開發的要求。其次,從苗族民間畫外部發展而言,政府及相關部門加大經濟投入,加強苗族民間畫的宣傳和推廣,建立健全保護和發展的機制體制,高度重視新時代藝術振興鄉村的途徑研究中苗畫發展的意義與價值;加強苗族民間畫傳承人的培養,形成合力,加強苗畫的研究、服務、管理人才的培養,積極申報苗畫的民間美術項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鼓勵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參與到民族民間藝術振興鄉村的歷史潮流中,為民族民間藝術發展,建設美麗鄉村貢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