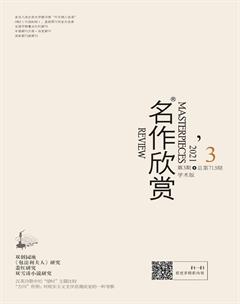《過故人莊》與《游山西村》之異同比較
摘 要:《過故人莊》為唐代田園詩人孟浩然的得意之作,《游山西村》乃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名篇之一。這兩首詩的創作時間雖相差四百多年,卻有著相似的創作思路。無論是創作題材、創作手法,還是心境的變化、感情的表達,都能從中尋出共通之處。然而,又由于時間上的跨度,作者經歷的不同,也使得這兩首詩在詩歌體式、創作視角、藝術風格及創作心境上有著較大差異。
關鍵詞:孟浩然 陸游 《過故人莊》 《游山西村》 異同比較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陸游是南宋著名的愛國詩人。這二人雖所處朝代不同,之間相隔了數百年,但他們的詩歌都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被人們所推崇。然學者們在對二人進行研究時,往往對其詩歌進行單一解讀,沒有發現二者其實可以進行比較互讀。筆者將以孟浩然所作《過故人莊》與陸游所作《游山西村》為例,將詩歌的創作題材、創作心境、創作手法、藝術風格等進行比較研究,具體分析二人在創作上有何相同之處,又有何相異之處,從而更好地體會不同年代的詩人所創作的詩歌給我們帶來的不同審美感受。
一、《過故人莊》與《游山西村》之創作背景
在研究詩人及其詩歌創作時,往往不能脫離的研究方法便是知人論世。那么,厘清《過故人莊》與《游山西村》這兩首詩是孟浩然和陸游分別在怎樣的背景下創作出來的,對于我們了解作者創作、解讀詩歌內容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1.《過故人莊》之創作背景
《過故人莊》收于《孟浩然全集》中,詩云: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舊唐書·孟浩然傳》載:“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這僅僅只一筆帶過了孟浩然的人生經歷。其他資料中關于孟浩然早期的記錄也僅有寥寥幾筆,并未詳細記錄孟浩然在游京師之前的情況,更沒有任何關于孟浩然創作《過故人莊》的相關記錄。魏平柱教授在《孟浩然的鹿門情結》中寫道:“張子容離開鹿門山舉進士在先天二年(713)即開元元年, 由此推斷孟浩然與張子容同隱應該在此之前, 孟浩然二十三時。”雖有對《過故人莊》創作時間的推測,然沒有具體證據。但從詩中“田家”“村邊”“桑麻”等詞確可讀出的是,此時孟浩然一定是在離鄉游京師之前,居于田園之中,過著平淡而自適的隱居生活。然而,孟浩然此時的隱居也不是真正的隱居,他是以“隱”求“仕”,在山中苦讀。而后游走京師,拜訪名士,然而引薦之路不通,又走上了科舉之路,科考失意后又一路漫游,回歸故里隱居。
2.《游山西村》之創作背景
《游山西村》收于《陸游集》中,詩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山西村,在浙江紹興東南方云門寺的西邊,當時屬于會稽縣。此詩作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春天,陸游四十三歲,在會稽云門。”因為在隆興二年(1164)陸游積極支持抗金將帥張浚北伐,符離戰敗后,遭到朝中主和投降派的排擠打擊,以“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從隆興府通判任上罷官回歸故里。由此可見,詩人創作這首詩時一定是有被貶的苦悶與失意之感。然作者在故鄉經歷了閑適、樸素的鄉居生活后,看到了百姓還依然保留著古老的“春社”風俗,由此產生了詩人對社會的一種認同,又重燃起對未來的期許。
二、《過故人莊》與《游山西村》之相同處
雖跨越四百多年的歷史,又為不同詩人創作,但通過對文本的細讀,我們確能看出孟浩然所作《過故人莊》與陸游所作《游山西村》在創作中有相同之處。
1.題材內容相似
《過故人莊》前半部分寫道:“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論語·微子》載:“子路從而后,遇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可見,先秦時“雞黍”就被作為很好的待客之物,這足以見故友的熱情相邀。翠綠的樹林圍繞著村落,蒼青的山巒連綿于城墻之外。眼前之景也讓人心生喜愛。再看《游山西村》前半部分:“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明明白白勸自己不要嘲笑農家臘酒渾濁,豐收之年主人家拿出豐盛的菜肴來留“我”在家中做客。正疑山重水復之間無路可走,不想柳暗花明處茅舍掩映。“具雞黍”與“足雞豚”兩詞,把農家那種熱情淳樸的待客之道描繪得生動無比。“綠樹”“青山”與“柳暗花明”兩句又把自然優美的田園風光刻畫得栩栩如生。足見兩位作者在凸顯淳樸熱情而又自然優美的田園生活取向上的不謀而合。
2.心境變化相似
朱光潛先生說:“表現情感最適當的方式是詩歌,因為語言節奏與內在節奏相契合,是自然的,‘不能已的。”而詩人在進行詩歌創作時,每一首詩所表達的情感、心境自然不是一成不變的。《過故人莊》首聯中著一“邀”字,表明作者并非不請自來,而是受到了故友的盛情相邀。但尾聯中卻轉一“還”字,這是作者反過來與友人相約,待到重陽佳節,再一同飲酒賞菊。由此可見,詩人孟浩然由被動的赴約轉換為主動申請。《游山西村》也同樣有這樣一個由被動做客到主動登門的心境變化。陸游在首聯用了“留”字,表明農家人的熱情挽留使作者卻之不恭,在尾聯卻說“無時”,這流露出對農家生活的戀戀不舍而要隨時登門拜訪的愿望。孟浩然與陸游想要表達的感情,與二者創作的《過故人莊》和《游山西村》這兩首詩的語言節奏完美契合。
3.創作手法相似
《過故人莊》由首聯到頸聯,分別講了眼前所見之景。“我”受邀于田家做客,故友以雞黍相待。村邊綠樹成蔭、青山延綿。“我”與友人坐于軒窗之旁,面對著谷場菜園,把酒閑談著莊稼的長勢,秋天會有怎樣的收成。這些情景,都是詩人真真切切眼中所見、親身所感。但詩的尾聯話鋒一轉,待到重陽佳節,“我”還來與你把酒言歡,共賞菊花。這分明是詩人對未發生之事的想象,乃是虛寫。
《游山西村》的前三聯也是詩人且游且觀、且感、且切身體會之景。詩人出游至農家,得到主人臘酒、雞豚之盛情款待,游至曲折山水之間,正疑無路可走,轉眼間又見柳暗花明、村舍掩映,擊鼓吹簫的春社之日已然接近,村民們依然保留著衣冠簡樸的古代風習。一幅自然和諧的農村風光躍然紙上。到這又由實轉虛,詩人在尾聯發出了自己的美好期許,愿今后也能乘著月色出游,拄著拐杖來敲你家的門,與農家促膝暢談。
由此可見,這兩首詩都是由實寫轉入虛寫,表達出作者對眼前之景、所經之事的喜愛與留戀。突破了詩的單一性,形成情感上的張力。這與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以及李商隱的“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的以實帶虛有著殊途同歸的審美效果。
4.表達感情相似
孟浩然與陸游都描寫了農家人的淳樸熱情,田園風光的自然優美,由此也就不難看出,二人所作之詩皆流露出對農村田園風光以及這種恬淡、自然生活的喜愛。孟浩然作《過故人莊》時隱居山林、鄉野之中,詩中所寫之景皆是農村生活里最常見、自然不過的景象,村外的綠樹、青山,與友人的把酒言歡,無一不體現出詩人輕松、自在的狀態。而陸游寫《游山西村》時雖是因為遭貶而無奈返鄉,但詩人經過最初的苦悶,重游自己的家鄉,經歷了一段沒有爾虞我詐的鄉村生活之后,心情也自然得到放松。在這樣閑適、輕松的田園生活里,好像人生都得到了升華,自有一種返璞歸真的豁達與通暢。再者,二人同時發出了今后會不請自來、重游故地的心愿,那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對農村田園生活的戀戀不舍之情。
三、《過故人莊》與《游山西村》之相異處
這兩首詩既為境遇不同的兩人所創作,時空上又由唐跨越到了南宋,那么它們之間必定會形成不可忽視的差異性。這些差異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這值得我們細細追究。
1.詩歌體式不同
《過故人莊》為五言律詩,全詩四聯八句共四十個字。《游山西村》為七言律詩,全詩四聯八句共五十六個字。五言與七言,雖每句僅相差兩字,但實際上詩的涵量卻有很大差別。這種涵量上的不同,放在律詩中也具有重要意義。陳伯海先生精辟指出:“律詩創作的中心課題,恰恰是要在有限的篇幅中爭取更大的藝術空間,于是五言與七言的差別便顯得關系重大。”五言有一種向人訴說的平白之感,講究的是對現實、自然以及內心世界的表達。而七言乃有一種流走之美,更強調的是詩人內心世界的表達,其中更摻入了詩人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思考。
五言律于初唐已有少量成熟詩篇,而真正得到發展是在盛唐,如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其中孟浩然的《過故人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七言律卻是中國最為成熟的詩歌體裁,發展到宋代,尤以宋人創作的理趣詩見勝。其中蘇軾、楊萬里、陸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五言與七言,并不是字數上簡單的加減,五律的章法和技法,在七律的體裁上得以發揚光大。在情感的表達上,七律也明顯更勝一籌。孟浩然的《過故人莊》,自然體現了五言律詩的短小精簡,且詩人近乎客觀地把自己的心境融于自然;陸游的《游山西村》則充分體現了七言律詩作為詩人內心世界外顯的媒介,詩中有詩人獨具慧眼的思考和見解。
2.創作視角不同
既然寫山水田園之景,那么必然有一個創作視角使眼前之景映入詩人眼簾。孟浩然寫《過故人莊》時,是在去往故友莊園的路上,看到了“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村外風光;在與故友坐于屋內,酒酣耳熱之際,打開軒窗,由室內向外所見的“開軒面場圃”之景,然后與友人有“把酒話桑麻”的親切絮語。但不管由院內還是由室內所見,其共同點都在于詩人寫的乃是靜中所見之景。
而陸游所作《游山西村》卻不同。從題目“游”字可知,詩人所見之景乃是自己且行且觀且感之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詩人明白地向我們作了解釋,自己行游于看似相同的山水之間,疑似迷路其中,但再走幾步,眼前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之間村戶掩映,別有一番景致。繼續前行,可以看見村民們為迎接春社日的到來擊鼓吹簫做著準備,這種古老的風尚如今依然保留,讓人心生別樣的激蕩、生機之感。整首詩緊扣詩題中的“游”字,既如此,那我們不難看出,陸游創作時乃動中觀景。
通過對兩首詩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過故人莊》寫到了村外綠樹成蔭,城墻之外有蒼青的山巒橫臥;而《游山西村》則一直寫的都是在村內游覽,由此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據此可得,這兩首詩在空間范圍上有一個擴大的過程。另外,《過故人莊》中“把酒話桑麻”中的“酒”,是一個籠統的名稱,詩人并沒有解釋是什么酒。而《游山西村》中說了“莫笑農家臘酒渾”,詩人清楚地說明了所飲之酒為渾濁的臘酒,那么我們可以看出,由唐到宋,詩人所用意象有一個由籠統到具體化的過程。
3.藝術風格不同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這樣說道:“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見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這也就揭示了唐詩和宋詩兩種不同的創作風格。
也許,孟浩然的《過故人莊》不能完全代表唐詩“以豐神情韻見長”的創作風格,但與宋詩相比,其藝術風格卻有自己的獨到之處。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中評價孟浩然的詩《聽鄭五愔彈琴》《游精思觀回王白云在后》等,評論道:“諸作簡直像沒有詩,像一杯白開水,惟其如此,乃有醇味。”又舉了其四首代表作《峴潭作》《晚泊潯陽望香爐峰》《萬山潭作》《傷峴山云表上人》,并進一步論斷說:“這四首詩寫得平淡極了,幾乎淡到沒有詩的地步,可是這的確是最孟浩然式的詩。”當我們真的讀了這些作品后,會發現聞一多先生的這些形容并非言過其實,而用“淡到看不見詩”來形容《過故人莊》,也是很恰切的。沈德潛先生評價孟浩然的《過故人莊》道:“通體輕妙,末句‘就字作意,而歸于自然。”確實,讀《過故人莊》就像是作者與你閑話家常一般,將自己所見、所經、所感娓娓道來,顯得如此之平易自然、樸實無華。
在“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中,理趣詩可以說是其中別開生面的一極。張毅先生在《宋代文學思想史》中闡釋“理趣”這一概念時精辟指出:“理趣是由形與神、情與理結合而產生出來的,已不是單純的物理,更不是二程所說的那種除情去欲的抽象性理。”也就是說,所謂“理趣詩”體現出的鮮明特征即是形神兼備、情理結合,針對作詩就是詩中有景、景中有情,情與理和諧統一。陸游的《游山西村》是宋代理趣詩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詩的頷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被錢鍾書先生認為是“陸游這一聯才把它寫得‘題無剩義”。表面上看似是寫自己行走于山重水復之間,迷失方向,但再走幾步就會出現柳暗花明與屋舍儼然的景象。但實際上這又何嘗不是陸游在遭受貶謫之后的一種心理狀態呢?詩人的一腔報國熱情被政敵當作排擠打壓的借口,仕途的受挫使得詩人苦悶不堪,甚至產生自我懷疑,猶如跌入深淵之中,眼前迷霧重重,看不到出路。但詩人卻并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通過鄉村生活的洗禮與時間的沉淀,詩人漸漸從中官場受挫的苦悶中脫將出來,又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這種將情景與道理結合的寫作風格,充滿了理趣意味。這便形成了陸游這首詩寓理于游、委婉別致的藝術風格。與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類“理趣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4.創作心境不同
孟浩然創作《過故人莊》時,正隱居于山野村莊,潛心苦讀,以求得淵博的學識,好去長安求得功名,爭取入仕的機會。這時候的孟浩然受邀去老朋友家里做客,與友人談論的也都是田園村莊這類極為平常、平淡的事情,他此時的心境是平和的,他是抱著一種欣賞的態度去看待周圍的一切。
《游山西村》時的陸游又是怎樣的境況呢?乾道二年(1166)春天,還在隆興府通判任上的陸游,被彈劾罷職:“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此時,他正被罷官,閑居在家。雖是閑居,但他的心境卻極為復雜。有被政敵排擠打壓的苦悶,有被皇帝毫不留情罷官的憤懣,“山重水復疑無路”就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但還不僅限于此種情緒。從“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我們分明看到了詩人對未來的期許。看“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一句,在蘇軾《蝶戀花·密州上元》中也有此類描寫:“擊鼓吹簫,卻入農桑社。”這說明此種風俗一直被保留下來。詩人對這種古老風俗的贊許,也折射出他對社會的一種認同。詩人的愛國熱情并沒有熄滅,他用鄉居生活的閑適來對抗官場攻訐的紛爭,而他也確實在農村生活中獲得輕快與放逐、蘊蓄著力量與希冀。
綜上所述,孟浩然與陸游二人雖處于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著相同的創作上的默契,這是由于兩位詩人當時都處于田園山水之間,都有著與民同樂的經歷,因此都用了熱情淳樸、風景優美的田園生活這一相同題材。又因為作者被閑適自然的農村生活所吸引,所以同時經歷了由被動變為主動的心境轉變過程。相應地,創作手法和表達的情感也有了不謀而合之處。然而,二者在創作時畢竟跨越了四百多年時空,在此期間,詩歌的體式經歷了由五言律向七言律的轉變。且由不同作者創作出的詩歌,藝術風格存在差異這也順理成章。同時,又由于作者的不同境遇,因此有了孟詩為單純的平和、欣賞,陸詩為被貶的苦悶、對未來的期許等不同心情交錯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創作心境。
參考文獻:
[1] 柯寶成.孟浩然全集[M].武漢:崇文書局,2013:86.
[2] 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5060.
[3] 周項林.隱讀、隱居與隱逸——孟浩然《夜歸鹿門歌》一處注釋商榷[J].語文知識,2016(11).
[4] 朱東潤.陸游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
[5] 鄒志方.陸游詩詞選[M].北京:中華書局,2018:18.
[6]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12058.
[7]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193-194.
[8] 朱光潛.詩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7.
[9] 陳鐵民.王維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7:3.
[10] 周振甫.李商隱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9.
[11] 陳伯海.唐詩學引論[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160.
[12] 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3:2.
[13] 聞一多.唐詩雜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5:283.
[14]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13.
[15]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5:114.
[16] 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159-160.
[17] 王水照.蘇軾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58.
作 者: 沈芳,陜西理工大學2019級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學;通訊作者:付興林,文學博士,陜西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