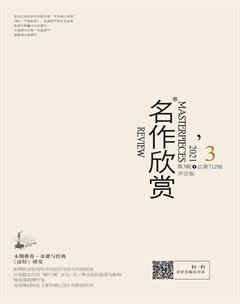論《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道德主題的復雜性
陳思鈺 王芳
推 薦 語
如果把人文教育的理想,設定為塑造總在成長的個體,那么,重讀經典作品無疑是達成這一理想的必要途徑之一,對于善于閱讀的個體來說,每一次閱讀就像每一次經驗,都會增添獨特的滋味和意義;但是,成長不能止步于閱讀,還需要學會闡釋和表達,就是說,不僅要讀懂文本內涵,還要把閱讀理解的收獲用文字清楚地表達出來,這是我這些年一直在課堂上堅持的,也得到了學生的支持和認可。這次推出的六篇學生小論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感謝《名作欣賞》 對我工作的一貫支持,得以展示學生的成果。
(王芳,紹興文理學院教授)
摘 要:作為一部被認為帶有道德意義的社會風俗喜劇,奧斯汀這部宣示其創(chuàng)作成熟期到來的作品給予那些嚴肅的考察者的不僅僅是充滿巧合與沖突的戲劇化情節(jié),多面的圓形人物,還有其美學鋪陳背后的道德主題。奧斯汀即使在創(chuàng)作那些被視為最具有道德教育傾向的作品時,仍然忠實于道德原則的現(xiàn)實性遭遇。
關鍵詞: 《曼斯菲爾德莊園》 范妮 道德主題
《曼斯菲爾德莊園》是簡·奧斯汀特定時期的作品,與其他作品比較而言,本書情節(jié)更為復雜,突發(fā)性事件更加集中,社會諷刺意味也更加濃重。然而國內外對《曼斯菲爾德莊園》乃至簡·奧斯汀小說的研究大多以婚戀主題、人物刻畫等為主,鮮少談及小說中的道德論題。簡·奧斯汀在自足的文本小世界里構建的一個道德價值判斷體系所反映出的道德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一、道德行為的意愿性
羅伯特·施佩曼在《道德的基本概念》一書中明確指出了意愿和行為之間的縫隙:“當人做某件事會傷害到別人時,我們完全能使自己不依賴于客觀的眼前利益,完全能夠想象對我們行為至關重要的一些價值的客觀等級,但也只限于理論”a。在實踐層面上,當面對選擇困境時,每一個個體都必須擺脫無止境的思考,做出行動,這種行動最終取決于個體的信念。
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主人公范妮在兩位表姐離家后,終于從無人關注的灰姑娘處境中來到聚光燈下,無所事事的克勞福德先生對她打起了如意算盤。克勞福德先生運用人脈關系來提拔范妮深愛的哥哥,希望以此博得范妮的好感,進而俘獲她的愛。此時,范妮就被迫面對克勞福德先生一改其往日輕浮面貌而帶有真誠色彩的求婚。我們注意到,這個情節(jié)非常容易落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感激大于愛戀的窠臼:男方在追求動機指導下的投入最后得到了女方的雙重認可,即對物質幫助的感激和在精神層面上的愛戀,而奧斯汀在這里卻嘗試在這種理想化的模式中引入新的現(xiàn)實性的變量。克勞福德先生給范妮的前期印象是極其糟糕的,他同時撩撥范妮的兩個表姐,大表姐在當時還已經有了婚約,這導致了范妮對他求婚的真誠性的懷疑。但同時范妮又不得不承認他給威廉帶來了光明的前途,承認他的幫助的確帶來了喜悅,承認他在這件事上必須值得自己的感激。如果拒絕用愛戀彌補這種愧疚,范妮不可避免地面臨良心的折磨,而如果以身相許來回報別人的施恩,這樣的道德又是否合理呢?奧斯汀在此處寫得很曖昧。她以苦苦乞求的方式逃避克勞福德先生的求婚,面對姨夫的指責,她這樣說:“但是我完全相信,我絕對不能使他幸福,我自己也會變得很悲慘。”b以受害者看待自己,以最大的努力賦予自己選擇的道德正當性——但始終無法抹殺在某種就事論事意義下她選擇的道德失范。基于這個道德意義,我們甚至能夠懷疑:范妮對克勞福德先生的成見如此執(zhí)著究竟是不是恰當?shù)模吭诳藙诟5孪壬幌盗凶非笙拢覀兪遣皇且苍鴦訐u過?也許他真的改變了以前的品性,對待范妮是認真且堅持的?
至此,我們不能不承認范妮身上體現(xiàn)的自欺。一直到離開曼斯菲爾德莊園,她始終認定克勞福德先生的求婚是一種誘惑,其光鮮的求婚預示的必然是于己不幸、于人可憐的婚姻生活。范妮的行動看似不合情理,其實是符合她自己的信念的,她乃是首先基于自我幸福的考慮做出了選擇,她心里早已有了埃德蒙,但由于埃德蒙對克勞福德小姐的癡迷,她的情感幾乎難以得到回應,因此,她也無法徹底忽視克勞福德先生的追求。從這個角度講,范妮是將私利當成了目的,將道德當成了手段。
考慮到范妮作為正面人物出現(xiàn)以及奧斯汀具有的新教信仰,我們可以這樣把握作者的意旨:正是由于兩難處境中做出的不完美道德選擇,救贖的前提——凡人——才得以成立,并賦予整個救贖歷程以意義。凡人才需要拯救,才有拯救的希望,但并非所有的角色都擁有救贖的可能。這種可能只限于那些預先保有上帝恩典的幸運者——對文學而言,就是作者選定的“喜劇命運角色”,在這里就是范妮。
從藝術性上來說,被動的兩難選擇的確增添了故事的趣味與懸念。同時,這樣的處理手法又削弱了作者預定的道德原則作為一種莊嚴律令的至高性。奧斯汀的作品擁有一切文學作品共有的敘述時間自覺,在敘述速度上施加有意的控制,這部作品使奧斯汀封閉的傳統(tǒng)觀念領域能透過具體生活背景在讀者腦海中拓出嶄新的空間。
二、道德斗爭的雙重性
古往今來,不少圣賢哲人都注意到了人世間的善惡之爭,“對‘善與‘惡、‘好與‘壞這些詞義的探尋屬于哲學最古老的問題”c,“每個人都在做他所意愿之事,誰遵從某些道德標準,他就喜歡做合乎這些道德標準之事” d。人物之間的性格沖突表面看來是“善”與“惡”的斗爭,但實際上,人物所意愿之事反映了他們選擇的道德標準。“此外,僅僅通過所謂的善意來辯解行為是偽善的學說”e。
道德斗爭是一條貫穿全書的主題線索,其在情節(jié)展開中主要以人物間性格沖突的方式呈現(xiàn)。總的來看,《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道德斗爭具有雙重性:趨向完美道德理想的“善”的力量,既要同趨向反道德的“惡”的力量斗爭,又要對具有潛在破壞力的“偽善”力量提高警惕。前者是“非善”與“善”的對抗,是本性同原則的交鋒;后者則是“偽善”與“善”的攻防,是自然情感與欲求同自由意志中道德理性成分的優(yōu)先爭執(zhí)。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善”與“非善”的斗爭較為昭明開朗,而“善”與“偽善”的斗爭則略顯隱晦。但正是這較隱蔽的斗爭根本性地展示了奧斯汀在作品中對于道德主題的探討。
小說中“偽善”性格的展示集中體現(xiàn)于諾利斯太太的每次登場。諾利斯太太的虛偽顯然比克勞福德小姐的更加惡劣,后者的虛偽僅僅是有意欺騙,前者則已經欺人不知、自欺不覺。勸托馬斯爵士收養(yǎng)范妮的時候,光出主意不出力的諾利斯太太甚至能夠為此自我感覺良好,“她相信她是全世界最慷慨無私的姐姐和姨媽”(曼,6)。事實上,她不會關心范妮能否適應新的環(huán)境,能否獲得真正有益于她的成長條件,卻會深深沉浸于這件事帶給她的道德滿足感,充分地展現(xiàn)了其自私蒙蔽理智下的道德自欺。她看似合情合理,回應了托馬斯爵士所有的顧慮,實則自私、狹隘、愚蠢,只考慮收養(yǎng)孩子對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影響,煞費心機提防表兄妹間的愛情,最后事與愿違,枉費心機。
“奧斯汀在描繪諾利斯太太時依靠反復使用‘叫這個動詞,暗示了其令人討厭的吵吵嚷嚷的特點”f。其實不難看出,諾利斯太太的大嗓音是她焦慮心態(tài)的外在呈現(xiàn):她擺脫不了掌握話語權的欲望,以及對脫離話語中心的恐懼,因此希望通過提高嗓門來加強存在感,以這種自欺的方式減緩焦慮。諾利斯太太的焦慮是廣泛的,既包括財務上的焦慮,也包括社會地位的焦慮。這些焦慮無不出于她天生的虛榮心。正是她強烈的虛榮心取代了她的道德理性,支配著她的行為。
諾利斯太太的“偽善”,擁有特定的社會背景:她愛慕士紳階層的頭銜與地位、尊貴與富足,完全缺乏普萊斯太太與上流社會決絕的勇氣;同時,她又沒有伯特倫夫人的好運與美貌,始終缺乏釣得金龜婿的機會與實力。她最后落嫁的,是一個地位與收入中等偏下、疾病纏身的牧師。諾利斯太太在現(xiàn)實的殘酷與內心的虛榮中掙扎,擁有極其強烈的不安全感與自我本位觀:二者都壓抑了她自由意志中道德理性的呼喚,而聽任猥瑣庸俗的品質瘋狂生長。由此可見,奧斯汀在深刻挖掘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了諾利斯太太這個偽善的代表者,并憑借該形象富有的社會歷史內蘊成功超越了她生活的十九世紀英國鄉(xiāng)村。
最終諾利斯太太選擇了去照顧不幸的瑪利亞,“在那里,可想而知,她們的心情成了彼此折磨的根源”(曼,441)。諾利斯太太離開曼斯菲爾德莊園,也代表著對道德具有潛在破壞力的“偽善”的與“善”之間斗爭的失敗。
三、道德問題的社會性
簡·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創(chuàng)作于1814年。18世紀末19世紀初,是傳統(tǒng)貴族與地主士紳階層逐漸衰落、新興資產階級日益崛起的年代,工業(yè)革命正在悄悄地改變英國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英國人的道德準則和社會關系自然也發(fā)生了變化。
小說中的瑪麗·克勞福德就是社會變遷的縮影。以這個人物從倫敦(城市)遷徙到了曼斯菲爾德莊園(鄉(xiāng)村),反映出了資本主義道德觀與傳統(tǒng)道德觀的矛盾沖突。瑪麗來自現(xiàn)代化的大都市——倫敦,當時的倫敦是一流金融與商業(yè)大都市,揮金如土、紙醉金迷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瑪麗在充斥著消費主義的環(huán)境中長大,所以,她深受城市道德的影響,破壞了原有的道德秩序,資本主義道德觀在她心中扎根生長,并隨著她住處的遷徙,企圖腐蝕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道德秩序。
“資本主義道德觀,通常被視為是一種以拜金主義為價值核心的道德膜拜,換言之,金錢與權力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志或象征”g。瑪麗的道德問題就是凡事都以金錢為中心,選擇婚姻、逼迫埃德蒙選擇其他高薪職業(yè)、期盼湯姆死訊以順利繼承家業(yè),樁樁件件都不難看出她是個不折不扣的拜金女,并且始終沒有絲毫的動搖。她最初來到莊園的時候,最先選擇的是托馬斯爵士的大兒子湯姆,因為他才是莊園未來的主人,大筆財富的繼承人。在選擇金錢的前提下,她把婚姻看成是物質結合而不是精神結合。她的理性選擇,或是深思熟慮的婚姻安排,足以說明她那倫敦大都市化般的記憶,即所謂的“門當戶對”或是“凡是單身的女子都應該有一個富有的丈夫”h。但隨著時間推移以及與人的相處,她逐漸發(fā)現(xiàn)湯姆是個紈绔子弟,并不值得托付終身。她暫時性地忘記了自己的道德身份,愛上了爵士的二兒子埃德蒙,但是資本主義道德觀馬上就以另一種方式在她身上體現(xiàn)。她要的只是權力與金錢,如果自己愛的人也擁有金錢那豈不是錦上添花,她多次嘲諷牧師的年薪低并竭力勸說埃德蒙可以選擇別的職業(yè),在她看來,“獲得幸福的靈丹妙藥便是大量的收入”(曼,202)。但是埃德蒙明確自己的職業(yè)志向,即使對方是心愛的瑪麗小姐,他也不會動搖。瑪麗在此碰壁,但是她的資本主義道德觀的火焰并沒有在此熄滅。在湯姆病危時,瑪麗又覺得自己得到了機會,只要湯姆一死,那么曼斯菲爾莊園的繼承人就將變成埃德蒙,她始終認為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財產是她應得的,她寫信詢問范妮此事,范妮卻也看得明明白白。“看來,埃德蒙在擁有財富的條件下當一名教士,是可以得到諒解的;他朝思暮想要慶賀自己在征服偏見方面的勝利,那么這恐怕是唯一的途徑。她只能這么想,金錢是一切中最重要的”(曼,412)。其淡薄的道德觀念令人嘆息,連善良的埃德蒙都無法忍受。埃德蒙曾說:“這就是她那個時髦社會所干的事……我們還能在哪里找到天賦這么豐富的女人?可是它葬送了她,葬送了她!”(曼,431)在小說的結尾,瑪麗的資本主義道德觀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入侵宣告失敗。以范妮、埃德蒙為代表的傳統(tǒng)道德觀阻止了資本主義道德觀的對其的瓦解。但是“瑪麗不應單純看作是‘惡的代表,這一人物明明光彩照人、魅力十足,卻缺乏基本的是非觀,連奧斯汀都透露出惋惜,暗示她在城市的浮華墮落中迷失了本性”i。
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資本主義道德觀與傳統(tǒng)道德觀是當時社會道德觀的兩大陣營,它不僅僅是反映在人物之間的價值觀念沖突,更是代表了當時社會中拜金主義的風氣正在悄然腐蝕著人們的內心。在當時女性的婚嫁選擇中,婚戀觀必然依附于同時代的社會道德觀,而瑪麗婚戀觀的背后則是暗含了資本主義道德觀骯臟的拜金主義。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曼斯菲爾德莊園》道德主題的豐富方向與同一旨趣。無論是兩難選擇的道德困境,還是特定人物的道德分析,抑或是社會造成的道德問題,都蘊含著人的動機層面不純潔性的道德批判。對奧斯汀而言,現(xiàn)實的復雜性要求道德已不能用情感去體驗,而要用理性去認識。但這勢必引發(fā)道德的功利化解讀,并被日后興起的邊沁主義證實。
acde〔德〕羅伯特·施佩曼:《道德的基本概念》,沈國琴、杜幸之、勵潔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第1頁,第8頁,第66頁。
b 〔英〕簡·奧斯汀:《曼斯菲爾德莊園》,項星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版,第302頁。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這個版本,為了行文簡潔,后文所引文本只隨文注出頁碼,不再另行作注。
f 〔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三種》,申慧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gh姚楠:《“記憶與遺忘”之間平衡化交替》,載于《大眾文藝》2014年第12期,第37頁,第37頁。
i 陳秀淵:《〈城市與道德〉——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瑪麗·克勞福德的道德觀解說》,載于《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129頁。
作 者: 陳思鈺,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漢語言師范本科在讀;王芳,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教授,當代文學評論家,研究方向: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
編 輯: 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