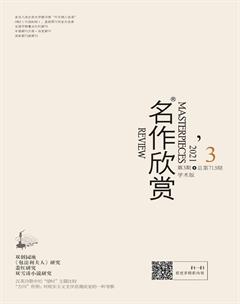《牽風記》女主人公汪可逾論
摘 要:徐懷中在《牽風記》的創(chuàng)作中融合了戰(zhàn)爭與人的超驗敘事,打破了往日戰(zhàn)爭文學略有僵化的套路,完成了一次新的審美建構(gòu)。汪可逾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爭背景下,始終保持著她的純真與無暇,雖被愛情中的負面因素所摧殘,但最終破繭成蝶,回歸生命的原點。汪可逾是美的化身,她的毀滅是對其自身人格的升華,是對美的超越,因此,她的死具有豐富而沉重的拯救意義。汪可逾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了徐懷中對于戰(zhàn)爭中人性的探索和對美的熱愛與追求,也凸顯了其精神容量的豐富與寬廣。
關鍵詞:徐懷中 《牽風記》 汪可逾
一、《高山流水》覓知音
汪可逾是徐懷中所塑造的一個美的象征。正如她的名字,“可不可以的可,逾越的逾”a,在軍隊中,汪可逾絲毫沒有改變她固有的人生姿態(tài),一直從心所欲,似乎是逾越了軍隊的紀律,但并沒有逾越美的本身。
汪可逾是人與自然的化身,她有兩次可以說是經(jīng)典的“裸身”場面。第一次是在狂風暴雨下的連續(xù)強行軍后,汪可逾把唯一的一塊軍用雨布包了她心愛的古琴,任憑大雨將自己澆了個透,隨后在一家門洞里支起門板,光著身子睡下了。不想一覺睡過了頭,被起早的齊競遇到,學過人體攝影的齊競覺得這是一幅絕美的畫面,拿出相機一陣狂拍。當齊競從取景框里看到汪可逾正睜大了眼睛,默默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時,一下被“定格”在那里。“首長,照片沖洗出來,不要忘了送照片給我”,這個場景正如這一章的標題《一名女八路一只灰鴿一簇蒲公英》,可以看出徐懷中在創(chuàng)作中想要展現(xiàn)的內(nèi)在蘊涵,其實是屋檐下的一只灰鴿抖落羽毛上殘留的雨水;門墩旁生長的蒲公英,在陽光下淋干了莖葉上的雨水,漸漸挺立起來,花瓣兒在悄悄地張開。一個裸身少女,一只灰鴿和一簇蒲公英沒有什么區(qū)別,生息與共,感受一同。大家一起經(jīng)歷了一場暴風雨的洗禮,又一同迎來了一個空氣清新的早晨。第二次是部隊接到命令渡黃河北返,這里作者將時空切換到四百年前,卻與當下的連接十分緊密。汪可逾與近百名婦女裸身同乘一船,集體的動作使她們彼此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從她們與汪可逾的交談中可以看出,從裸身到現(xiàn)在不過剝一根大蔥的時間,她們已經(jīng)有習以為常的感受。 “人類穿起獸皮,大約是十七萬年前的事。而踏上直立人的進化歷程,至少有四百萬年了。相比之下,穿起衣服才有幾天的事兒?正如你們講的,不過是剝一顆大蔥的功夫。所以一點也不奇怪,我們現(xiàn)代人,很容易找回赤身裸體無拘無束的那種初始記憶。”這兩個場景充分展現(xiàn)了汪可逾與大自然的協(xié)調(diào)與融合,在殘酷的戰(zhàn)爭之中,她仍保留了那顆最純真的赤子之心,猶如一朵出水芙蓉,從自然中來,終要回歸自然。
汪可逾的芳華與才情,通過古琴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彈奏古琴,是要感情從內(nèi)心出發(fā),不需要外物的介入。每個人對音樂的理解不同,自然在演奏每首曲子時所表達出來的情感也不盡相同。而汪可逾在演奏古琴時,她的情感是從生命的源頭出發(fā),借古琴所表達出來,情與心在樂聲中融合為一體,自然可以說是一個人的性情道德品質(zhì)的外現(xiàn)。初次登場,一曲《高山流水》不做過多緩急變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讓人領略到“不舍晝夜”的意味,讓琴音更有內(nèi)在神韻。在與齊競的交談中,她追尋古琴中最本質(zhì)的單音——空弦音。她練習《關山月》想報答戰(zhàn)馬“灘棗”,“灘棗”心有觸動,掙脫束縛,跑到汪可逾所在之處,將兩扇窗戶拱開,鼻孔還在噴出薄霧一般的白沫。從《高山流水》她覓得齊競這個知音,到《關山月》她覓得“灘棗”這個知音,可以說,汪可逾是音樂的化身,她自身的美融入了自然,結(jié)合了音樂,她本身所具有的人格美和理想美,都深深地感染著這場戰(zhàn)爭中的人們。
二、“空弦音”中的溫愛與悵恨
汪可逾出身于北平知識分子的家庭,當她攜古琴出現(xiàn)在“夜老虎團”的慰問演出舞臺上,齊競一眼便認出這是一張宋代古琴,隨即吟誦出白居易的《廢琴》:“絲桐合為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而汪可逾以“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即聲談,其間無古今”作為回應。近五年后,汪可逾再次出現(xiàn)在齊競的面前時已長成一位翩翩少女,那雙美麗的眼睛直接望進了齊競的心里。古琴是汪可逾與齊競相愛的起點,它一直貫穿著兩人感情的始終。在渡黃河時汪可逾也因船翻而失蹤,齊競要求曹水兒一定要帶上汪參謀的古琴,如果找不到人,就把古琴系上石塊沉下河去,小汪去到那個世界,不能沒有這一張宋代古琴的陪伴,這足以見得他對汪可逾的了解,兩個人的感情進入了更深層次的境界,可謂奏響了這曲充滿浪漫氣息的“戰(zhàn)地戀歌”。
可令汪可逾萬萬沒想到的是,她所追尋的理想和信念遭到了革命者自身的負面因素的深刻制約。汪可逾所在的工作隊遭遇襲擊,她與其他六名女同志跳崖赴死未果,在昏迷中被俘虜。被救回后,齊競旁敲側(cè)擊地借璞玉試探汪可逾的清白。如果不是他本人親自說出口,汪可逾怎么都不會相信封建思想的毒瘤還存在于這個留洋歸國,令她如此欣賞的首長身上。此時齊競的解釋使他的虛偽暴露得徹徹底底:“我自己也不理解,一旦接受了某種陳舊觀念,要從意識中去除很難。總還是認為,所謂‘初夜落紅,是最潔凈最珍貴最神圣的一種紀念物。我設想,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應該用一整包藥棉保存下來,裝在一個鐵匣子里……”
汪可逾用她的真誠去對待每一個人,去對待她的愛情,當她的真誠與尊嚴受到質(zhì)疑時,她便奮起反抗:“我的履歷表上增添了最污濁的一頁,不能指望別人使用優(yōu)美的詩行和我談話。不過我要請問,是誰賦予你這樣的特權?憑什么我應該被你所籠罩?憑什么我只能受你的擺布?憑什么我必然要為你占領?而且還要預先簽立城下之盟,保證自己白璧無瑕?”戰(zhàn)爭帶給汪可逾的是身體上的創(chuàng)傷,而齊競的封建思想使汪可逾的內(nèi)心和精神遭受重創(chuàng)。兩個人曾經(jīng)的美好被齊競內(nèi)心深處的陳腐所摧毀。“齊競!我從內(nèi)心看不起你!”a汪可逾用她所能說出的最嚴厲的一句話對傷害她的人進行批判,最后兩人以“零溫度握手”結(jié)束了這一場充滿奇幻卻又足夠凄苦的戰(zhàn)地戀歌,一切就此煙消云散。戰(zhàn)爭無法毀滅美好純粹的事物,但精神的摧毀往往毀滅了所追求的美好。
三、向死而生
汪可逾離開了令她精神受創(chuàng)的地方,開始逐漸回歸她一直追尋的理想。汪可逾與曹水兒安置在紅軍游擊隊住過的天然溶洞中,她久久環(huán)顧著高大的巖壁對曹水兒說:“我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么,總覺得這巖洞似曾相識。不!又何止是似曾相識,就如同重歸故里,目光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這個溶洞的面積,應該還要大得多。”這里汪可逾有著超越時空的記憶,她本人雖沒有經(jīng)歷過,但是人類在演變的過程中,時代的印記不會隨著社會的日益進步而消失,這些最初始的記憶都印刻在人類的內(nèi)心深處。汪可逾不僅僅有過去的記憶,還有感知未來的能力,她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終點,便開始整理自己,褪去衣物,同時拒絕進食,不住地飲山泉水,喝一兩口下去,能嘔吐出一碗,將呼吸系統(tǒng)和消化道及口腔內(nèi)的所有污物都清理干凈,如此九天九夜的重復,排便也開始出現(xiàn)異常,腸道系統(tǒng)得到了徹底的清理。人在出遠門時,總會想想自己還忘記帶什么,汪可逾卻不同,她講求所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她取下固傷的夾板,又要求曹水兒用冷水給她擦洗全身,直到完全潔凈,她對著陪伴她數(shù)日的騎兵通信員說:“曹水兒!我的好兄弟!我困得要命,我要睡了……”令人驚訝的是,汪可逾的遺體未見任何腐敗跡象,反而有一系列的生機,面容如初,自然安詳。《辭海》對“汪”這個姓氏的注釋為:“深廣貌。汪然平靜,寂然澄清。”汪可逾便如這般,她的內(nèi)心深而廣之,如一汪清泉,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又寂然不動,明凈透徹。這個年僅十九歲的古琴女孩經(jīng)歷了戰(zhàn)火的洗禮,仍舊保持著她本來的樣子。她走向了生命的終點,給自己畫上了一個美麗的永不腐朽的句號。她的死,是對她自身那種堅強、純潔的人格的成全,也是對亂世紅顏命運的寫照,又具有豐富而沉重的拯救意義。
汪可逾的一生,用她自身的品質(zhì)影響了很多人,齊競與曹水兒便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面對流言蜚語,汪可逾毫不在意,使曹水兒對這位女八路充滿敬畏;曹水兒聽汪可逾講星空的時間是以光年所計算的,他無限感慨道:“我們這個世界上槍啊炮的,打來打去,比照你講的光年來看,磨磨唧唧的這點事情,算得了什么?”曹水兒為她找回了埋藏在地下的古琴,琴身雖損壞,但汪可逾將琴弦取下,就勢在無弦琴上彈奏著那起承轉(zhuǎn)合的韻律。古人云:“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弦可也。”汪可逾這種狀態(tài)可以用人琴合一來形容,到達了一種至高的境界。汪可逾一生都在追求“空弦音”:“古人寫《琴賦》,開篇就講,萬物有盛衰,唯音聲無變化……如果能給我一次機會,只要一次,領略一下曠世以來第一個原生的古琴單音,我死而無憾!”回歸即是超越,這是汪可逾追尋的意義所在。在曹水兒被執(zhí)行槍決前,他接受處決卻拒絕五花大綁,這也體現(xiàn)了曹水兒的尊嚴感。
如果說汪可逾對曹水兒是一種啟迪,那么對齊競來說便是一種拯救。汪可逾的死,可以說是對齊競最嚴厲的懲處,她用至高無上的人格反襯出齊競的自私與虛偽,齊競無論多么優(yōu)秀都無法與汪可逾高貴的靈魂相比較。晚年的齊競雖功成名就卻拼命讀書來彌補自己的精神空缺。在讀到一本沒有封面的書上寫著這樣兩句話:“被揉皺的紙團兒,浸泡在清水中,會逐漸平展開來,直至恢復為本來的一張紙。人,一生一世的全過程,亦應作如是觀。”這使齊競對自己與汪可逾的關系有了一個頓悟,這正是對汪可逾一生的總結(jié),而齊競也完成了為汪可逾起草悼文的心愿,并定名為《銀杏碑》:“與她相識的人,無不希望以她為藍本,重新來塑造自己。實則她一以貫之的人生姿態(tài),在她本人純屬無意識,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復制,別人永遠學不會的。只要你著意仿效,便已經(jīng)什么都不是了。所幸的是,她的那個標志性微笑總是會隨著一縷春風浮現(xiàn)在我們面前。”最后,齊競選擇了安樂死,通過死亡卸下了他所背負的精神上的重擔,散發(fā)出人性的光芒。
結(jié)語
汪可逾的一生是從被揉皺的紙團兒,浸泡在清水中,逐漸展開為一張白紙的過程。她以古琴覓得知音,在烽火歲月中歷經(jīng)了磨難,體會了愛情卻又從愛情中受到創(chuàng)傷,這些溫愛與悵恨也沒有使她停止對理想的追尋。她雖死猶生,同時也富有深刻的拯救意義。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符合徐懷中先生一貫的寫作風格,在他眾多的作品中,相對于正面渲染戰(zhàn)爭的宏大場面,他更多的是從側(cè)面切入,淡化戰(zhàn)爭色彩,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描寫戰(zhàn)爭中戰(zhàn)士們的日常生活與情感之中。通過對戰(zhàn)爭中人情、人性、道德上的挖掘,又將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自然地融入其中,完成了戰(zhàn)爭的詩意化書寫,為讀者呈現(xiàn)出烽火歲月中的另一番天地。《牽風記》的出版可以說是在這種寫作風格上的又一次突破,在殘酷的戰(zhàn)爭景深中,著重表達愛情,同時也體現(xiàn)出他對生命哲學的感悟。徐懷中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還體現(xiàn)了超驗敘事,“超驗主義”強調(diào)人性中的神性,直覺和人的價值。汪可逾一直在追尋生命的原點,她身上所散發(fā)的人性光輝不會因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
a 徐懷中:《牽風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參考文獻:
[1] 徐懷中.當代長篇小說選刊《牽風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4.
[2] 劉大先.返歸本心——徐懷中《牽風記》的意象敘事與哲思境界[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11):15- 27+64.
[3] 徐懷中,傅逸塵.戰(zhàn)爭敘事的“超驗主義”審美新向度——關于長篇小說《牽風記》的對話[J].小說評論,2019(5):4-20.
[4] 張志忠.酷烈而旖旎的戰(zhàn)爭風情畫[N].中華讀書報,2019-01-30(011).
[5] 陸文虎.徐懷中長篇小說《牽風記》:一部“國風”式的戰(zhàn)地浪漫故事[N].文藝報,2019-01-11(003).
[6] 徐懷中,張志忠.抒情體式嶄新人物生命氣象——關于長篇新作《牽風記》的對話[J].當代文壇,2019(1):141-145.
[7] 關于徐懷中長篇小說《牽風記》的通信[N].文藝報,2018-12-07(002).
[8] 劉紹穎.透過彌漫的硝煙[N].新華書目報,2020-01-16(015).
[9] 王坤寧.徐懷中:書寫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9-08-23(008).
[10] 叢子鈺.小說應該是生機盎然的[N].文藝報,2019-01-21(001).
[11] 殷實.戰(zhàn)爭文學的新時空[N].解放軍報,2019-02-02(008).
[12] 舒晉瑜,徐懷中.我希望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N].中華讀書報,2019-02-11(011).
作 者: 許光照,中南民族大學在讀本科生。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