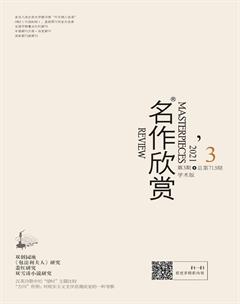英譯宋詞的情感美賞析
摘 要:以劉宓慶的《翻譯美學理論》為依托、許淵沖英譯宋詞《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Tipsy in the FlowersShade)為例,探討英譯宋詞所富含的情感美。研究發現,譯者通過把握英語語言的陽剛之美、動態之美和自然美可以將詞人深切的思夫之情精準傳達給讀者,引起共鳴。
關鍵詞:情感美 宋詞 英譯
“詞這種文學樣式,其主要題材都與女性有關,傳統婉約詞的藝術特征也頗具女性的文學色彩,但是在詞史上女詞人卻甚為罕見。”(謝桃坊:298)李清照卻以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真切的情感表達贏得了中國第一女詞人的地位。我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將她的《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翻譯成Tipsy in the Flowers Shade,運用了英語語言的三個情感美學特質來塑造女子因思夫而孤寂的美學形象,傳遞真切的情感之美。
一、英語陽剛理性美下孤寂的情感美
首先是陽剛理性美,“主要指英語嚴謹的語法規則性、嚴密的形式規范式和從句法結構到語篇結構的高度法治和有條不紊的組織性”(劉宓慶:59)。此譯文嚴格遵循英語句子書寫的規范,每個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謂賓結構。同時,全篇采用一般現在時,開篇“From golden censer incense smokes all day”中的“all day”指的是在白天思愁如香煙裊裊縈繞不去,“Feeling the midnight chill invade”中的“midnight”指的是夜晚孤寂冷清,下闋“At dusk I drink before chrysanthemums in bloom”中的“dusk”是傍晚的觸景生情。從白天到黑夜到傍晚,時間本該是混亂的,因為詞人的生活已經被打亂了,體現出思夫至深,不知是什么時間。但英譯版本卻全篇用一般現在時。這是因為“英語具備由形式決定意義的規范”(劉宓慶:60),一般現在時暗示這個孤獨寂寞的思夫情感不是某一天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種日常的情思,詞人混亂的生活不僅僅是寫下這首詞的那一刻,而是每一天過的都是這樣因思念而含混的生活。此外,英譯版本的書寫也很符合詩歌的規范,英語以單詞為單位,長短不一,無法做到像漢語的版本一樣,上下闋結構一致,字數對應,格式工整。譯者只能通過工整的韻腳來營造富有節奏感的美學效果。上句與下句形成雙行詩節,如“stay”和“day”、“again”和“remain”、“jade”和“invade”、“bloom”和“gloom”、“bower”和“flower”,是英語詩歌中完全韻,甚至比漢語版本的韻腳出現在上闋的第一、二、五句,下闋的第一和五句更加工整和符合詩歌的規范。英語是符號語言,單詞(word)的結構有長有短,不像漢語能夠形成形式優美的對仗結構。許淵沖的翻譯多數都是用押韻的方式來體現韻律上的節奏感,主要是句中韻和尾韻。格式整齊,韻律感強烈。
二、英語動態感性美下心緒變幻之美
英譯版本也具有高度的動態感性美。譯文采用了多種句型來體現詞人層次豐富的心緒變化。“Thin is the mist and thick the clouds, so sad I stay”和“Alone I still remain”這兩句為倒裝句,都是將“sad”和“alone”兩個表示情感的詞提到前邊,突出強調詞人因孤獨而傷懷的情感。前一句還將“thin”和“thick”提前,強調天氣沉悶給人的壓抑之感,完全對應了漢語版本通過天氣來暗含心情的寫作手法,極具美感。后一句“Alone I still remain”是英譯版本增補的內容,增添之后能夠與上一句的“sad”形成呼應,也能渲染下一句“In the curtain of gauze, on pillow smooth like jade, Feeling the midnight chill invade”中夜晚凄涼的氣氛。“invade”用的是動詞原形,按照英語語法規則,invade在句中是非謂語,需要變形為invading,但譯者為了押韻采用了原形,說明英語語言具有“容許說話者主體的‘意對形態選擇起某種決定作用”(劉宓慶:63)這一富有“包容性”的動態之美。“Say not my soul Is not consumed”是雙重否定句,比起一般的肯定句,更強調了自己內心深處清醒的認知,完全符合漢語版本中詞人對思念傷神的清晰認識。“Should western wind uproll The curtain of my bower, Twould show a thinner face than yellow flower”使用的是虛擬語氣,比起漢語版的“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更能點明這一句是虛實結合的寫法,實寫眼前清瘦人兒與淡雅黃花的對比,虛寫菊花高潔的象征含義和詞人人淡如菊的高貴品格之間的緊密聯系。最后一句也使用了英語中最常見的修辭手法“提喻”(synecdoche),用“face”指代“人”。譯文不只是直接的翻譯,也是一種“再書寫”和再創作,用目標語的修辭手法能夠更加符合讀者的期待。
三、英語自然美下高潔的形象美
最后,通過準確性、清晰性和流暢度等“自然美”的特質,英譯版本也將詞人思親的情感體現得更加深刻而細致。為了符合英語語言的準確性要求,譯者將漢語中省略的內容都進行了補充,首先就是人稱。漢語全文不著一字寫人稱,具有意蘊深遠的模糊美,漢語的“模糊美在古代叫作‘隱美,‘隱秀之美,漢語是充滿‘隱秀的語言,尤其是詩歌,將‘隱美視為一種高格調的審美情趣”(劉宓慶:56)。《醉花陰》作為婉約派詞人李清照的代表作之一,格調高雅,通過描寫天氣的沉悶來暗示內心的愁苦,通過佳節團聚的意義反襯內心的孤獨,通過夜寒無眠來暗含無人關懷的凄冷,極具詩歌的模糊美。與之相反,英譯版本全篇使用了第一人稱,直接表明這是詞人思夫的自畫像,意思明確,行文直白。英譯版本的第一句,“so sad I stay”就非常直白地點明自己難過的心情。下兩句“Alone I still remain”更是直接點明了漢語版本隱含的主題,即與丈夫分離后的孤獨寂寞。這句是譯者額外補充的句子,但并不顯得煩冗,反而讓意思表達變得完整,有助于幫助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理解詞人的情感態度與佳節、夜半風涼之間的關系。“At dusk I drink before chrysanthemums in bloom”這句中的“chrysanthemum”也是譯者補充的信息,看到“東籬”,我們就能很自然地聯想到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從而能容易就理解到李清照看到的應該是“菊花”。這屬于中國文化的“語碼”,“文化的語碼在西方被稱作是cultural code,就是一個語言,一個語言就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在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中,被使用得很長久了就成為一個code,它就變成文化的語碼”(葉嘉瑩:28)。后文中的“人比黃花瘦”是詞人自比菊花高潔的品格,但外語讀者并不具備理解這些中國文化語碼的知識儲備,譯者的補充能夠消除這些疑問。對必要信息的補充也保證了譯文的清晰性和流暢度,使詞人的情感表達更為順達。這樣的藝術形象塑造與情感表達和她自身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李清照生長的家庭相對開明,婚后的夫妻生活美滿幸福,這養成她開朗、熱情、活潑的個性,也養成她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的人生態度”(戴建業:129)。對天氣的敏感捕捉和賞菊的高雅生活情趣都是基于她對生活的熱愛和敏銳感知。英語自然美的特質也幫助譯者強化了詞人高潔的藝術形象,能讓讀者理解李清照為何能從極盡鋪墊的孤寂形象轉化為高潔的藝術形象。
結語
“易安有活躍的生命,繁復的生活,廣博的涉覽和實際的情感經驗。”(胡云翼:157)通過結構美、音樂美和意象美,漢語將婉約精純的情感營造到極致,是極具美學欣賞價值的情感表達。而譯文Tipsy in the Flowers Shade則充分體現了我國優秀的翻譯家在兩種文化之間尋求恰當的轉換方式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通過把握英語語言的陽剛理性美、動態感性美和自然美,許淵沖對這兩首詞進行了“再書寫”和“再創作”,正如他所提倡的那樣,“再創作要發揮譯語的優勢,和原文競賽,才能建立新的世界文化”(許淵沖:72)。也促使英語母語國家的讀者能夠從譯文的詩歌節律和修辭手法中找到熟悉感,從熟悉的詩歌規范中理解中國詞人的情感表達,從而達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目的。
參考文獻:
[1] 戴建業.兩宋詩詞簡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
[2] 胡云翼.宋詞研究[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3] 劉宓慶.翻譯美學理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4] 謝桃坊.宋詞概論[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5] 許淵沖.再創作與翻譯風格[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5).
[6] 葉嘉瑩.詞之美感特質的形成與演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 葉嘉瑩.南宋名家選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基金項目: 本文系廣東省普通高校創新人才類青年創新人才類(人文社科)項目 “《許淵沖經典英譯古代詩歌1000首之宋詞》的情感美學賞析及在藝術類高職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中的應用》”(編號:2017GWQNCX035)
作 者: 賴宇琛,碩士,廣東文藝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外文學、翻譯學。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