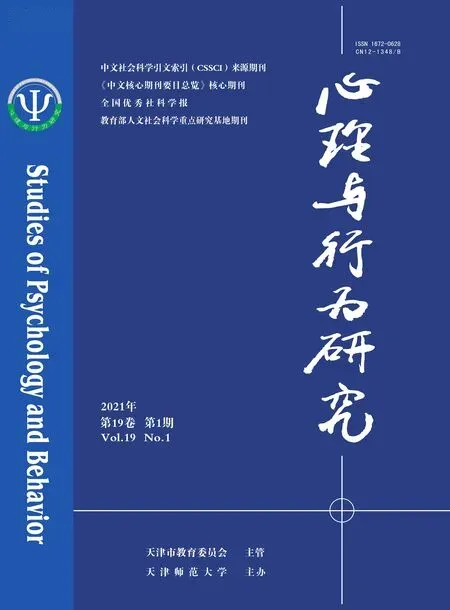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職業認同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別差異 *
魏淑華 趙 健 董及美 陳功香
(濟南大學教育與心理科學學院,濟南 250022)
1 問題提出
中小學教育作為國家基礎教育,其教育教學質量決定了未來的國民基本素質水平,而中小學的教育教學質量受到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顯著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度是其對教育工作和教師這一職業以及工作條件與狀況的一種總體的、情緒性的感受(陳云英, 孫紹邦, 1994)。研究表明,教師的工作滿意度不僅能顯著正向預測其工作投入和工作績效(李新翠, 2016; Ostroff, 1992),顯著影響職業成熟度(劉天娥, 海鷹, 2017;彭文波, 呂琳, 劉電芝, 2017)、職業倦怠(Skaalvik & Skaalvik,2009)和離職傾向(魏淑華, 宋廣文, 2012),還能夠顯著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Patrick, 2007;Tek, 2014),并對其身心發展產生全面影響(沈學珺, 2019)。因此無論是從教師的工作狀態提升角度還是從學生的發展成長角度來看,提高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對于提高基礎教育質量都是非常必要的。
探討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可能前因變量,并對其影響機制進行實證研究,可為探尋提高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有效途徑提供重要的理論與實證依據。以往對教師工作滿意度前因變量的探討,關注較多的是學校管理因素和教師自身因素兩個方面。學校管理因素主要有教學文化(You, Kim, &Lim, 2017)、學校組織氣氛(Ghavifekr & Pillai, 2016)、校長領導風格(Bogler, 2002)和組織支持(王琪,2018)等,教師自身因素包括人格特質(Li, Wang,Gao, & You, 2017)、心理資本(Larson & Luthans,2006)、工作動機(Arifin, 2015)和自我效能感(Caprara, Barbaranelli, Steca, & Malone, 2006)等。
近年來,我國勞動人口結構與家庭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如何處理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系”成為大部分工作者面對的難題,中小學教師亦然。按照關系性質,工作-家庭關系可劃分為“工作-家庭沖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在工作-家庭關系對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方面,已經有研究者基于傳統視角對教師的工作-家庭沖突與其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比如,林頤宣(2020)發現小學教師的工作-家庭沖突與工作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王衛平(2015)發現中學骨干教師的工作-家庭沖突可顯著負向預測工作滿意度。但對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家庭增益狀況與工作滿意度關系的研究還比較缺乏。
工作-家庭增益,是指個體在某一角色(工作/家庭)中積累的資源被應用到另外一個領域(家庭/工作),進而提升另一個領域(家庭/工作)的生活質量或績效(Powell & Greenhaus, 2006)。按照“增益”發生的方向,工作-家庭增益分為“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對工作的增益”。其中,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是指個體的工作角色扮演對其家庭生活質量與家庭績效提升的積極作用。基于為探尋提升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有效教育管理策略而提供實證依據的研究出發點,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是,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是否對其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作用;如果作用顯著,那么其作用機制是什么?
1.1 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當個體在工作經歷中獲得的技能、機會、積極情緒等資源滲透到家庭領域,提升了個體的家庭領域角色體驗并對其家庭系統發展產生貢獻時,個體會以積極的工作態度(例如對工作更滿意)對工作組織進行積極回應(Blau, 1964;Tang, Siu, & Cheung, 2014)。以企業員工為調查對象的研究發現,員工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其工作滿意度(Baral &Bhargava, 2010)。對護士群體的研究也發現,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工作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章雷鋼, 馬紅麗, 王志娟, 金婷婷, 蔣懷濱, 2016)。基于以上理論與實證依據,本研究提出假設1: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其工作滿意度。
1.2 職業認同的中介作用
對中小學教師來說,其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包括薪酬、人際和職業素養三個維度(吳梅寶,2010)。即教師在工作過程中獲得的薪酬、建立的人際關系、提升的職業素養,有助于其承擔家庭責任、提高家庭角色績效。已有研究發現,薪酬是反映教師職業聲望的重要因素,會影響其工作熱情和職業認同(周國華, 吳海江, 2016)。而教師職業認同是指教師對所從事職業及內化的職業角色的積極認知、體驗和行為傾向的綜合體,是由職業價值觀、角色價值觀、職業歸屬感和職業行為傾向四個因子構成的多維度結構(魏淑華, 宋廣文, 張大均, 2013)。有研究發現,不同薪酬水平的教師在職業認同各個維度上的得分存在顯著差異(曾麗紅, 2016)。
除了薪酬外,中小學教師在工作中獲得的人際關系與職業素養狀況也會影響其職業認同。比如,教師在工作中積累的人際資源,有助于解決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教師在與同事和學生相處中獲得的人際關系處理技能可以使夫妻關系、親子關系等更和諧;教師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提升的職業素養可以用來促進子女在學業等方面的成長。以上這些資源對教師的家庭和生活是有益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師的家庭角色績效和家庭生活質量。根據交換理論和互惠原則,當個體感受到工作對家庭帶來的積極影響時,必然會對自己的職業角色產生更加肯定的評價,職業認同水平也會上升。由此本研究推斷,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狀況可以正向預測其職業認同水平。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對其職業的認同水平會影響其對工作的態度,職業認同水平高的個體會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滿意度(羅杰, 周瑗, 陳維,潘運, 趙守盈, 2014)。教師對其從事的工作滿意與否取決于一些激勵因子,這些激勵因子首先來自個體內部,而職業認同即是其中之一,它能使教師對其從事的工作產生滿意的情感(Moore &Hofman, 1988)。已有研究表明,幼兒教師和高校體育教師的職業認同與其工作滿意度存在顯著正相關,職業認同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工作滿意度(胡芳芳, 仇云霞, 桑青松, 2012; 湯國杰, 2009)。依據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設2: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可能通過職業認同的中介作用對工作滿意度產生間接影響。
1.3 性別的調節作用
雖然我國目前的家庭結構已然發生變化,但傳統的家庭分工觀念依然影響著人們的家庭角色價值觀。長期以來,多數家庭的角色分工都是“男主外,女主內”:男性負責出門工作賺錢、養家糊口,是保障家庭經濟收入和物質生活條件的主要責任人;女性則負責在家相夫教子、孝敬老人,承擔更多家庭內部事務的處理任務。個體在家庭責任分工上表現出較大的性別差異,相對于女性,通常男性花費在家庭的時間和精力較少,男性為家庭的付出更多是通過辛勤工作、不斷提高工作回報來實現的。
傳統家庭觀念也影響了人們的工作價值觀。對中小學教師來說,雖然男教師和女教師都要履行教育教學職責、承擔教師工作責任,但對于不同性別的教師來說,其工作價值觀可能不同,特別是在看待工作對其家庭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方面。對于男教師來說,能否從所承擔的教師工作任務中獲得更多有助于其家庭責任承擔和家庭關系處理的薪酬、素質、人際、自尊、自信等方面的增益,可能更為重要,從而對其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自己所從事的教師職業的影響力更大。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對于本研究的假設2 提出的中介模型,性別通過調節其前半段路徑(即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職業認同之間的關系)而調節整個模型。
綜合以上三個假設,本研究的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

圖 1 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對山東省部分中小學的教師進行施測。分兩次進行,2018 年11 月(T1)測查人口學變量和工作對家庭的增益,發放問卷920 份,獲得有效問卷855 份。2019 年11 月(T2),測查職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發放問卷855 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760 份,男、女教師分別占比31.6%和68.4%;小學和中學教師分別占比43.2%和56.8%;已婚和單身教師分別占比92.1%和7.9%;主科和非主科教師分別占比61.2% 和38.8%;30 歲及以下、31~40 歲、41~50 歲、50 歲以上年齡教師分別占比13.3%、37.6%、41.2%和7.9%。對最終所得樣本與流失樣本進行卡方檢驗和t檢驗,發現在性別、學段、婚姻狀況、科目、年齡和工作對家庭的增益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說明本研究的被試不存在結構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問卷
采用吳梅寶(2010)編制的中小學教師工作-家庭增益問卷中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分問卷,包括3 個維度,共15 個題目,采用Likert 4 點計分,1 為“極少發生”,4 為“總是如此”,得分越高表明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
2.2.2 職業認同量表
采用魏淑華等(2013)編制的中小學教師職業認同量表,包括4 個維度,共18 個題目,采用Likert 5 點記分,1 為“完全不符合”,5 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職業認同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
2.2.3 工作滿意度量表
采用Tsui,Egan 和O’Reilly III(1992)編制的工作滿意度量表,測查被試對工作性質、領導、同事、報酬、晉升機會等方面的滿意度,共6 題,采用Likert 5 點計分,1 為“非常不符合”,5 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工作滿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
2.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23.0 進行數據整理與分析,采用SPSS 中的PROCESS 宏程序(3.0)進行中介和調節作用檢驗。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共有7 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6.73%,小于40% 的臨界標準。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將學段、年齡、科目、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對各變量進行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1),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職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間呈兩兩顯著正相關。

表 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矩陣
3.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將虛擬化處理后的學段、年齡、科目、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將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職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進行標準化,采用偏差矯正的Bootstrap 法進行模型檢驗。
3.3.1 職業認同的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Hayes(2013)開發的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4 進行檢驗,結果表明(見表2),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對工作滿意度的總效應顯著(b=0.39,p<0.001),假設1 得到驗證;放入中介變量職業認同后,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對職業認同的預測作用顯著(b=0.44,p<0.001),職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作用顯著(b=0.36,p<0.001),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對工作滿意度的直接效應顯著(b=0.23,p<0.001),說明職業認同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檢驗表明,職業認同的中介效應95%CI [0.12, 0.21],中介效應為0.16,占總效應的41.03%,假設2 得到驗證。

表 2 職業認同中介效應檢驗
3.3.2 性別的調節效應檢驗
使用PROCESS 的模型7 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和工作對家庭的增益的交互項對職業認同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b=-0.20,p<0.01, 95%CI[-0.36, -0.06]),說明性別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預測職業認同的過程中起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教師的職業認同的中介效應,如表3左邊部分所示,對于男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通過職業認同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中介效應為0.21,95%CI 為[0.15, 0.29];對于女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通過職業認同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中介效應為0.14,95%CI 為[0.10, 0.18]。對判定指標INDEX 進行檢驗(Hayes, 2015),結果如表3右邊部分所示,性別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職業認同中介效應中的調節判定指標INDEX 為-0.07,95%CI 為[-0.13, -0.02],說明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是顯著的,即職業認同的中介效應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假設3 得到驗證。

表 3 職業認同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檢驗
為了更直觀形象地描述職業認同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按照Dearing 和Hamilton(2006)的方法對不同性別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正負一個標準差對應的職業認同分值繪制交互效應圖。簡單斜率檢驗發現(見圖2),相較于女教師(簡單斜率為0.39,t=9.99,p<0.001),隨著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得分的增加,男教師的職業認同表現出更顯著的上升趨勢(簡單斜率為0.59,t=9.73,p<0.001)。

圖 2 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職業認同關系中性別的調節作用
4 討論
4.1 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工作滿意度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表明,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能夠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以往研究也發現,工作對家庭領域的積極溢出是員工工作滿意度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Baral & Bhargava, 2010;Lapierre et al., 2018;Larson & Luthans, 2006),個體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對其發出領域(即工作領域)積極心理特征的提升效力甚至大于接收領域(即家庭領域)(Zhang, Xu, Jin, & Ford, 2018)。因此,提升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是提高其工作滿意度的有效途徑。
在本研究中,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平均分為2.74(SD=0.69),表明其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一般,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政府可通過提高教師的職業聲望、薪酬和福利,學校可通過創設良好的人際氛圍、優化晉升機制、拓寬晉升路徑等方式,為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得以發生提供更多的工作領域資源。在教師中開展如何將工作領域中獲得的積極資源更好地應用于家庭生活領域的研討會,并鼓勵教師主動探尋提高其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的個性化有效方式。
4.2 職業認同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過程中的中介作用
相比之下,探討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對工作滿意度影響的內在機制,更具生態學效度,中介效應分析可進一步揭示二者關系的內在本質。本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的職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且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職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三者間的內在作用機制,即中小學教師體驗到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越多,就會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產生更高的認同,進而對所從事的工作本身以及所處的工作環境感到更加滿意。此研究結果提示,在提高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的措施中,在積極提高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的同時,還需重視教師的職業認同水平提升。通過提高教師的職業價值觀、角色價值觀和職業歸屬感等方式,從提高教師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職業認同兩個方面提高其工作滿意度。
4.3 性別對職業認同中介作用的調節效應
本研究還發現性別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與職業認同關系中的調節效應顯著,中小學教師的職業認同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的中介作用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具體而言,相較于女教師,職業認同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過程中的中介效應量在男教師中更高,其原因是男教師的職業認同水平受到工作對家庭的增益狀況的影響更大。這說明,與女教師相比,男教師能否從工作領域中獲得有益于家庭責任承擔的資源,對其職業認同水平的影響更大。當從事教師工作能夠為家庭角色績效帶來積極增益時,將為男教師的職業認同水平帶來更大程度的提升,從而也能夠更大程度上提高其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的結果還提示,男教師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對其職業認同及工作滿意度有更高的預測效力,因此在幫助女教師解決其面臨的工作-家庭關系現實問題的同時,還需積極關注男教師的工作-家庭關系問題,努力提高男教師的工作對家庭的增益水平,這似乎能夠為男教師個人和事業帶來更大的“收益”。
5 結論
中小學教師工作對家庭的增益顯著影響工作滿意度,職業認同在工作對家庭的增益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過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且這一中介作用存在性別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