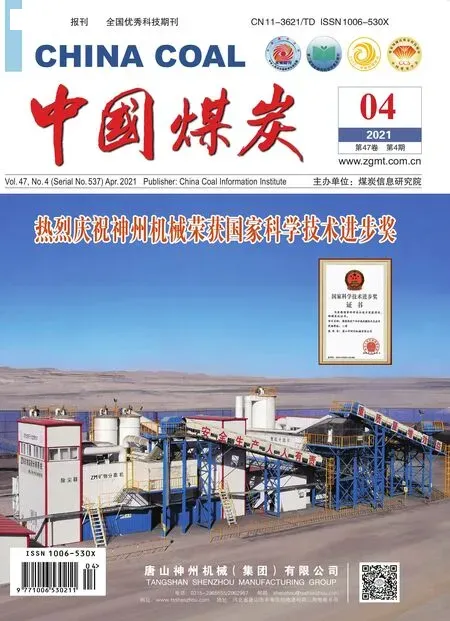我國露天煤礦無人駕駛及新能源卡車發展現狀與關鍵技術
趙 浩,毛開江,曲業明,付恩三
(1.應急管理部研究中心,北京市東城區,100013;2.應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北京市朝陽區,100029;3.內蒙古吉林郭勒二號露天煤礦有限公司,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026200)
露天開采具有資源回收率高、安全條件好、勞動效率高、生產規模大等優點,近年來我國煤礦露天開采取得了較大發展,產量比重由2000年的4%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8%左右,為我國煤炭穩定供應提供了重要保障。運輸是露天礦開采工藝中主要的生產環節之一,運輸系統投資約占礦山總投資的40%~60%,運輸成本約占礦石成本的30%~40%,我國露天煤礦普遍采用單斗-卡車間斷工藝,自卸卡車是我國露天煤礦的主要運輸工具,卡車運輸環節是露天礦用人最多的環節,露天煤礦最容易出現的事故也是運輸事故,如:內蒙古自治區2015-2018年露天煤礦各類事故14起,其中運輸事故10起,占71.4%。若露天煤礦自卸卡車能夠使用新能源作為動力,并且實現無人駕駛,則可以實現降本增效、節能環保,達到本質安全。
1 我國露天煤礦發展概況
1.1 分布及規模情況
露天煤礦是我國煤炭工業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資源回收率高、安全條件好、勞動效率高、生產規模大等優點[1],對國內煤炭穩定供應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目前,我國共有露天煤礦376處,產能9.5億t/a、占全國煤礦總產能的17.8%,產量占全國的比重由2000年的4%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8%左右。其中:生產露天煤礦283處,產能7.51億t/a;在建露天煤礦87處,產能1.98億t/a。
(1)露天煤礦分布。我國露天煤礦分布在內蒙古、新疆、山西、云南、黑龍江、寧夏、陜西、青海、遼寧、甘肅、貴州、廣西、湖南共13個省(區),其中:內蒙古、新疆、山西和云南4省(區)露天煤礦326處、產能9.04億t/a,分別占全國的86.70%和95.16%。
(2)露天煤礦規模。全國產能400萬t/a及以上的大型露天煤礦53處、占全國露天煤礦總數量的14.10%,合計產能6.37億t/a、占全國露天煤礦總產能的67.05%。其中:生產露天煤礦37處、產能4.98億t/a,建設露天煤礦16處、產能1.39億t/a。千萬噸級特大型露天煤礦26處、占全國露天煤礦總數量的6.90%,產能4.93億t/a、占全國露天煤礦總產能的51.90%。其中:生產露天煤礦19處、產能3.97億t/a,建設露天煤礦7處(含改擴建)、產能0.96億t/a。產能100萬t/a以下的小型露天煤礦207處,占全國露天煤礦總數量的55.00%,產能1.17億t/a,占全國露天煤礦總產能的12.30%。其中:生產露天煤礦151處、產能8730萬t/a,建設露天煤礦50處、產能2 826萬t/a。
1.2 工藝設備情況
近20年來,我國露天煤礦在開采工藝及設備方面取得了一定進步,以黑岱溝、元寶山、安太堡、伊敏、霍林河南露天煤礦等為代表的國有大型露天煤礦引進了連續、半連續、吊斗鏟倒堆工藝,單斗挖掘機斗容最大已達75 m3,自卸卡車載重最大已達400 t,破碎機(站)能力最大可達12 000 t/h[2]。我國露天開采工藝裝備發展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問題。露天煤礦企業為節省投資和運營成本,普遍采用剝離工程外包運營模式,新疆所有露天煤礦采煤、剝離全采用外包運營方式,有的露天煤礦只有三四十人負責日常運營和安全管理,外包單位“小、散、弱”導致露天開采工藝及裝備步入“低端化”發展歧途。
(1)工藝由半連續、連續向間斷工藝倒退。20世紀80年代以及21世紀初期開發的露天煤礦均為自營,不存在工程外包,引進了連續、半連續工藝。2002年以來,我國煤炭產能急劇擴張,煤炭企業為減少投資,新開發露天煤礦基本都采用單斗-卡車工藝(間斷工藝)。與連續、半連續工藝相比,單斗-卡車工藝具有投資成本低、生產靈活的優點,但設備多、用油多、安全風險大。
(2)生產設備由“大型化”向“小型化”發展。由于承包方門檻低,又層層轉包,設備均屬于個人購買、掛靠運營,大量露天礦卡車噸位只有20~30 t(有的甚至不是礦用卡車),挖掘機斗容只有1.2~5.0 m3,導致坑內設備數量多、相互影響、安全風險大,而且油耗驚人。如某特大型露天煤礦剝離高峰期坑內車輛800余臺,單班坑下作業人數超過1 000人,年耗油量6.87萬t。同時,一些露天煤礦設計要求寬泛、標準低,一些露天煤礦則專為小設備設計,路面寬度、轉彎半徑不夠,升級大型設備困難。
2 無人駕駛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的重要性
我國露天開采工藝及裝備向單斗-卡車工藝發展有一定的經濟性,但也存在能耗大、污染重、風險高的問題,與我國貧油、少氣、富煤的國情不相符,與推進藍天保衛戰的大局不相符,與推進安全發展的大勢不相符,因此,亟需推動我國露天開采工藝及裝備變革,加快礦用無人駕駛卡車及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等智能型、環保型、安全型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
2.1 必要性
(1)提升本質安全水平的需要。當前,我國多數露天煤礦承包單位卡車噸位普遍只有20~30 t,坑內運輸卡車數量多,有的特大型露天煤礦高峰期坑內車輛800余臺,運輸車輛之間相互影響、安全風險極大。近幾年全國露天礦運輸事故不斷,2019年11月國家能源集團寶日希勒露天煤礦發生較大運輸事故,死亡4人。加快研發應用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能夠減少現場作業人員數量,實現少人則安、無人則安。
(2)解決招人難、留人難問題的需要。當前,露天煤礦外包單位寬體車司機工資8 000元/月左右,其工資水平不及公路物流卡車司機工資水平,且工作環境惡劣。內蒙古某露天煤礦700名卡車司機,僅1年內流動達500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露天煤礦卡車司機平均年齡約52歲,多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安全素質不高。加快研發應用無人駕駛礦用卡車,可以有效解決人員流動性大、招工難、從業人員素質低等問題。
(3)促進降本增效的需要。無人駕駛系統替代駕駛員,不僅可以節省人工成本、后勤成本(一名百噸級礦用卡車司機年薪20萬元左右,一輛卡車年人工費用超過84萬元)[3],降低燃油消耗、輪胎損耗,而且可以實現整個作業區域內車輛集群調度,有效提高車輛的利用率、作業效率和維護效率,降低卡車故障率。據淡水河谷公司統計,無人駕駛可以使燃料成本下降10%以上,使車輛維護費用降低10%,輪胎磨損降低25%。澳大利亞鐵礦石出口商福蒂斯丘金屬集團(FMG)表示,無人運輸的效率比傳統人工運輸提升30%[4]。據統計,礦用新能源卡車每公里使用成本相當于燃油車的1/3,電動機功率比燃油車增加近40%[5]。
(4)提升節能環保水平的需要。近年來露天礦山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露天煤礦卡車耗油量大,且卡車排放尾氣含有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氣體,嚴重污染礦區周邊環境。山西某特大型露天煤礦卡車年耗油量高達7萬t。因此,有必要加快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的研發及應用,解決露天煤礦燃油消耗大、污染環境問題。
2.2 可行性
(1)露天煤礦作業場景適于開展無人駕駛技術。現階段,無人駕駛技術的應用僅限于低速與限定場景。露天開采的實質就是大量礦巖的移運過程,將土巖運至排土場,將煤運至地面生產系統進行破碎,屬點對點的運輸,車輛運行速度較低,且運輸線路基本固定,作業場景單一、封閉,交通狀況相對簡單,交通參與元素的數量和種類均較少,具備采用無人駕駛技術的可行性。
(2)新一代通信技術發展為無人駕駛提供技術保障。當前,我國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了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虛擬現實、無人駕駛、人工智能、5G等高新技術與現代露天采礦技術深度融合,特別是5G技術的發展,加速了無人駕駛的落地,為無人運輸提供了催化劑,為開展礦用卡車無人駕駛技術研發及應用提供了技術保障。
(3)國外礦山無人駕駛方面已有成功經驗借鑒。國外礦用無人駕駛卡車的研究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21世紀以來,全球各大礦用卡車供應商都在進行無人駕駛礦用車的應用與研究。2008年以來,日本小松公司和美國卡特彼勒公司陸續在智利、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等國的礦山投入近460臺大型無人駕駛卡車,累計運輸物料超過40億t。卡特彼勒公司的無人駕駛卡車已經安全行駛6 760萬km,生產效率比傳統人工運輸提升了30%[3]。
(4)動力電池及氫能發展為礦用新能源卡車研發提供基礎保障。動力電池是新能源汽車的“心臟”,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動力蓄電池產業體系。隨著電氣化的發展,動力電池技術漸趨成熟。在同樣裝機、相同工況條件下,氫燃料電池與鋰動力電池相比,具備續航里程更長、充電時間更短、重量更輕、性能提升空間更大等優點。我國露天煤礦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新疆等地區,這些地區太陽能、風能資源豐富,電力充沛、價格低廉,因此,可以利用太陽能、風能發電,建立制氫站,發展氫產業,既消納了送不出去的電力,又提供了清潔能源,有助于解決棄風、棄光問題。
3 我國無人駕駛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進展
3.1 無人駕駛礦用卡車
我國無人駕駛礦用卡車研究起步較晚。2017年以來,踏歌智行、慧拓智能、易控智駕、百度、躍薪智能等十余家科技公司開展了無人駕駛技術研發,為礦山企業和礦用卡車生產廠家提供露天礦山無人駕駛系統整體解決方案。北方股份、同力重工、徐工集團、三一重裝、航天重工、濰柴集團、臨工重機等國內礦用卡車生產廠家也在開展無人駕駛卡車研發。遼寧工程技術大學、中國礦業大學等高等院校正在開展露天煤礦無人駕駛工藝重塑和設計標準適配研究。
2018年8月,包鋼集團聯合踏歌智行、北方股份等單位在白云鄂博礦區進行國內第1輛無人駕駛礦用卡車測試,目前已實現4臺無人駕駛卡車協同2臺挖掘機進行編組測試,與其他車輛混編運行,累計完成約9.55萬t礦物運輸量和1.78萬km的運輸里程。2019年5月,內蒙古蒙新煤炭公司杭蓋溝露天煤礦聯合易控智駕等單位,開展無人駕駛研究測試,投入4輛同力重工無人駕駛寬體車。2019年9月,大唐集團寶利露天煤礦聯合慧拓智能、中國聯通、華為等單位開展基于5G網絡智慧礦山無人礦車駕駛示范項目,投入4輛無人駕駛系統寬體自卸車。2019年11月,國家電投霍林河南露天煤礦與踏歌智行公司開展無人駕駛項目研究,完成2輛108噸級礦用自卸卡車無人化改造,效率達同型號人工駕駛運量的75%以上,且實現了夜班作業,目前項目已通過驗收,下階段將新投入10輛186噸級礦用無人駕駛卡車。2020年初,華能伊敏露天煤礦與百度Apollo公司合作,對2輛在用的172噸級礦用自卸卡車進行線控化改造,實現無人駕駛,目前已進入動態調試階段。2020年5月,國家能源集團寶日希勒露天煤礦與航天重工公司聯合開展“5G+無人駕駛”示范應用,總投資2 350萬元,對5輛220噸級礦用自卸卡車進行無人駕駛改造。
總體上看,我國無人駕駛礦用卡車正處于試驗測試階段,應用場景比較簡單,多為對礦山已有設備進行編組改造,運行效率為有人駕駛情況下的60%~80%左右。
3.2 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
目前,新能源礦用卡車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純電動、油電混合和氫能源。在油電混合和氫能源方面,2018年10月,國家能源集團、氫能科技公司及濰柴集團聯合開展了200噸級以上氫能重載礦用卡車研發,首臺國產200噸級以上氫燃料-鋰電池混合能源礦用卡車于2019年4月成功下線。2019年10月,山西諾浩集團研發的百噸級礦用汽車油電混合動力系統首次亮相。總體看,我國在油電混合、氫能源礦用卡車研究方面較少,還處于實驗室研發階段。
我國純電動新能源礦用卡車研究與應用始于2018年左右,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各類露天礦山共有200余臺純電動礦用卡車,主要核心研發單位為徐工重工、宇通重工、北奔重汽、宏威新能源、河南躍薪、北方重工、三一重裝、濰柴集團等設備制造廠商。2018年以來,宏威新能源在湖南岳陽、山東曲阜、陜西富平、西藏華泰龍、浙江湖州等地及礦山投運了60多臺純電動礦用寬體車,單車里程已經超過3萬km。2018年4月,北工重工40噸級純電動礦用卡車在烏海石灰石礦山交付試運。2018年6月,洛陽鉬業集團聯合躍薪科技研發的SY系列純電動礦用卡車在三道莊礦區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累計投入純電動礦用卡車30臺,無人駕駛純電動礦車5臺。2019年8月,山西諾浩集團純電動90噸級寬體礦用卡車在山西朔州交付。2019年12月,宇通集團首批純電動礦用卡車應用于中國黃金集團西藏華泰隆礦業公司。2020年6月,三一重裝集團研發的2臺SKT90E純電動無人寬體車應用于紫金礦業青海威斯特礦業公司。目前,純電動礦用新能源卡車主要應用于砂石礦山、水泥礦山和金屬礦山,在露天煤礦還沒有得到廣泛應用,僅華能伊敏露天煤礦進行了極寒條件下礦用電動卡車運行測試。
總體上看,我國新能源礦用卡車剛剛起步,依然處在產業化前期,受電池重量、循環壽命、充電速度及電池性能等因素制約,目前的純電動新能源礦用卡車主要為總重量90 t、載重60 t左右的寬體車。
4 無人駕駛礦用卡車關鍵技術研究方向
4.1 無人駕駛礦用卡車
目前,我國礦用卡車無人駕駛應用場景簡單,僅實現了小批量編組運行。礦區雨、雪、霧等惡劣天氣給視覺傳感器帶來嚴重的探測障礙,道路多出現轉彎盲區等不可檢測區域,僅依賴車載傳感器和車端算力,車輛的感知范圍和決策控制能力受限,無法適應礦區群車規模化作業運行以及道路多坡、多彎道及狹長路段的惡劣環境,安全保障低,作業效率低,亟待解決以下關鍵技術。
(1)非結構化道路無人駕駛感知融合技術。目前,非結構化道路感知準確性和可靠性還無法滿足礦山無人駕駛要求,亟待開展基于動態融合機制的車端多傳感器感知方法、分布式邊緣計算的路側危險狀態注意力感知方法、路車多源信息層次性主動融合感知方法研究,提高車端感知范圍,解決礦山惡劣環境下卡車盲區不可檢測問題,提高礦用卡車運輸作業安全保障。
(2)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規模化運營智能調度技術。以露天礦山復雜場景下無人駕駛卡車規模化運營的智能調度技術為主攻方向,開展高精度和高可靠性路徑規劃和車輛控制技術,路權決策分配技術,無人駕駛卡車實時調度多目標優化模型及求解算法研究,高精度地圖高效采集、制作、發布技術研究,實現無人駕駛礦用卡車的智能調度。
(3)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規模化運營智能協同控制技術。研究群體智能與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自主協同的一致性問題,基于群體智能理論的多車協同控制方法以及無人駕駛礦用卡車隊列分布協同控制方法,同時還要解決V2X(Vehicle to X,X代表任何可能的“人或物”)信息傳輸穩定性、位置定位漂移、域控制器成熟度和周期等問題,實現全礦高效協同的無人化運營。
(4)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與露天礦山時變場景匹配關鍵技術。露天煤礦采剝、排土工作面動態變化,且道路復雜多變(上坡、下坡、轉彎等),亟待研究露天礦時變場景下的5G固定基站匹配問題,無人駕駛卡車與露天礦山裝載、卸載設備的配合問題,有人/無人駕駛混合作業的安全機制和技術方案問題等,解決露天開采動態衍變與無人駕駛的匹配問題。
(5)高可靠性、高算力無人駕駛計算平臺研發。目前,車規級嵌入式無人駕駛計算平臺尚無突破,該領域的可量產計算平臺尚屬空白,亟待開展高可靠性、高算力無人駕駛計算平臺研發,實現車規級、高可靠性、高算力無人駕駛計算平臺的量產。
(6)大型礦用卡車關鍵部件研發。目前,我國在100噸級以上大型礦用卡車大扭矩變速器、200噸級以上大型礦用卡車電動輪方面尚屬空白,無對應產品,亟待開展技術攻關,研發100噸級以上大型礦用卡車大扭矩變速器、200噸級以上礦用卡車大型電動輪等大型礦用卡車關鍵部件。
(7)基于數字孿生的設備健康管理技術研發。目前,我國數字孿生技術的準確建模和數字同步技術還沒有實際應用案例,亟待開展基于數字孿生的設備健康管理技術研發,實現對設備故障及維修保養狀態進行預測維護,提升設備使用壽命,降低使用成本。
4.2 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
礦用新能源卡車僅在礦內運行,可依托礦區充沛的電力資源,建設充電場地,解決新能源礦用卡車的充電問題。而續航和載重量是困擾純電動礦用卡車的另外兩個難題,續航里程越長需要消耗的電量越多,需要更大容量的電池;電池容量越大,車輛自重就越大,裝載能力就會受到影響。續航、載重量、電池容量是限制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研發及應用的關鍵因素,亟待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如下。
(1)高電量、大功率、長壽命動力電池研發關鍵技術。目前,純電動礦用卡車動力電池大倍率放電及壽命無法滿足礦山持續爬坡等工況使用要求,亟待開展高電量、大功率、長壽命動力電池研發關鍵技術研究,實現4C以上大電流充放電、頻繁充放電、使用壽命滿足5年等要求。
(2)極端天氣下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關鍵技術。我國多數露天煤礦位于內蒙古、新疆等偏遠地區,屬高寒地區,氣候惡劣,冬季氣溫達到-35℃以下,亟需開展極端天氣下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的關鍵技術,研究動力電池的低溫充放電特性及電池保溫措施,解決駕駛室冬季取暖問題及冬季車廂粘料等問題。
(3)載重100 t以上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關鍵技術。目前,我國純電動新能源礦用卡車載重僅60 t左右,亟需開展載重100 t以上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關鍵技術研究,研發大功率電動機,并滿足礦用卡車持續爬坡的需要。
5 結論與展望
近年來露天煤礦企業普遍采用剝離工程外包運營模式,外包單位“小、散、弱”導致露天開采工藝及裝備步入“低端化”發展歧途,工藝由半連續、連續向間斷工藝倒退,設備由“大型化”向“小型化”發展。通過無人駕駛及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可以實現無人則安,提升露天煤礦本質安全水平,解決招人難、留人難問題,促進降本增效,提升節能環保水平。露天煤礦作業場景適于開展無人駕駛技術,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礦山無人駕駛方面已有成功經驗借鑒,新一代通信技術發展為無人駕駛提供技術保障,動力電池及氫能發展為礦用新能源卡車研發提供基礎保障,因此我國露天煤礦具備應用無人駕駛及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的條件。
通過研究總體上看,我國無人駕駛礦用卡車正處于試驗測試階段,亟待開展非結構化道路無人駕駛感知融合技術、規模化運營智能調度技術、規模化運營智能協同控制技術、高可靠性高算力計算平臺研發、大型礦用卡車關鍵部件研發、基于數字孿生的設備健康管理技術研發等關鍵技術攻關。我國新能源礦用卡車剛剛起步,依然處在產業化前期,亟待開展高電量、大功率、長壽命動力電池研發關鍵技術,極端天氣下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及應用關鍵技術,載重100 t以上純電動礦用卡車研發關鍵技術攻關。建議高等院校、礦用卡車設備制造廠家、智能化科技公司等多方面聯合攻關,解決卡脖子問題。國家有關部門大力支持無人駕駛礦用卡車、大型礦用新能源卡車研發,提高露天煤礦智能化水平,減少作業人員、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國家能源集團、中煤能源集團、國家電投集團等中央企業做好表率,開展露天礦山無人駕駛礦用卡車試驗,條件成熟后進行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