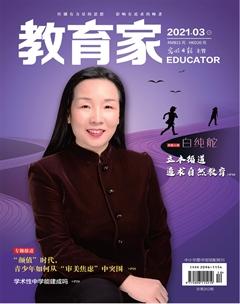互聯網如何重塑青少年的審美想象
曹華威
在醫美整形方興未艾的21世紀初,大眾媒體便已左右中國人的審美想象。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文華在對整容醫院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坐在醫院等候整容的女性常常翻看《ELLE》《VOGUE》等時尚雜志。雜志上白皙、苗條的明星照片無疑保留著對于“何為美”的解釋權。
在這種將自己與明星對照而產生的審美焦慮之下,人們不可避免地通過雜志上的醫美整形廣告來獲得宣泄與救贖。彼時,通過醫美整形改造身體盡管并不被大眾廣泛接受,但在媒體中仍然被詮釋為一種自由意志指導下的對于身體的積極改造,即使這種美麗的標準是被高度規訓的。
2018年10月5日,“高中某班32人幾乎都接受過整形手術”的新聞經由央視財經《第一時間》欄目報道后引發了社會對于青少年審美焦慮的關注。人們曾寄希望于互聯網的出現能打破媒體機構的壟斷,從而帶來更為多元和平等的觀念市場。然而如今看來,資本只是進一步放大和極化了審美焦慮。
A4腰、鎖骨放硬幣、反手摸肚臍……近些年層出不窮的審美新標準顯然比從前更為苛刻,從女性到男性,從網紅到普通人,從成年人到青少年,借由互聯網,這種單向度的審美想象如病毒一般在人群中傳遞。青少年仍處在價值觀不斷變化的人生階段,這既意味著他們更容易受到影響,也意味著他們存在改變的可能。青少年的審美焦慮并不能簡單歸因為涉世未深,而是一種互聯網加速下的時代癥候。
作為儀式的自拍
在所有表露青少年審美焦慮的行為中,自拍是最為明顯且頻繁出現的。自2013年11月18日“自拍”(selfie)被英國牛津大學評為年度熱詞,到今日,自拍已經從小眾的亞文化變為流行的大眾文化。但嚴格來說,自拍技術只是人類自我凝視歷史的延續,而非突破。從顧鏡自盼到自畫像,人們從未放棄通過各種與自我對話的儀式來審視身體,并借此宣示對于身體的自主權。
從 1839 年化學家羅伯特·科尼利厄斯拍出人類第一張自拍開始,自拍便成為攝影技術中極為特殊的存在。不同于傳統的攝影,自拍過程中拍攝的主體和客體均為攝影器材的使用者。自拍的出現使得人們可以更為方便地進行自我觀看。在此后的一百年里,自拍技術仍然僅僅停留于藝術家進行自我表達的小眾亞文化中。然而,隨著互聯網移動通信設備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被賦予了自拍的權利。
“自拍”(selfie)具有鮮明的社交屬性,它最初指向的便是用戶通過攝像頭拍攝照片并上傳到社交博客的行為,無論自拍者承認與否,今天流行的自拍游戲都有著潛在的公共性。換言之,觀看自拍照不再是私密的個人行為,而越來越成為公共空間中的展演。根據極光數據研究院的統計,青少年是通過社交媒體發布自拍的主要群體。除此之外,在修圖軟件的使用上,55.6% 的用戶不到 30 歲。由于“自拍”所附帶的社交屬性,青少年希冀從自拍中得到的并非真實的自我,而是一個更為美好的形象,或者可以說是更符合他人期待的自我。
如果說早期的自拍技術仍符合福柯對于“自我技術”的定義,即個體可以借由這種技術來構成主體,確認自我的主體性。那么今天流行的自拍技術無疑已經演化為一種新的規訓,在這一反復聲張自我的儀式中,自我卻被遠遠地驅逐出去,成為被他人凝視的客體,繼而引發廣泛的焦慮情緒。
在一項針對四所瑞典學校的13歲學生的自拍現象的研究中,學者邁克爾·福斯曼發現:青少年群體的自拍行為不能被簡單理解為一種自戀行為,而是充滿互動性的社交行為。為了獲得更多的點贊和更積極的評價,青少年們會讓自己更符合主流審美的要求。自拍不再是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反而是審美刻板印象的庸俗回聲。
網紅的階層符碼
網紅,一度被認為是青少年審美焦慮的始作俑者。2017年,新華網一項針對青少年的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將網紅、主播等職業選為理想職業。在整容醫美手術和修圖技術的合力下,千人一面的網紅被大量炮制出來。這一群體的出現既迎合又引導著青少年的審美想象。在傳統媒體時代,普通人的生活往往以底層群像的方式出現。隨著基于互聯網的新媒體形態的涌現,媒體賦權讓介于社會名流和普羅大眾之間的網紅群體,獲得了自我展示的空間。
網紅群體的出現帶給青少年的,不只是單純局限于外貌和身材的審美焦慮,而是更為廣泛的階層審美焦慮。重要的不是網紅,而是網紅講述的故事,是和這些精致面孔出現在同一取景框中的其他景觀。青少年與其說是在模仿網紅,不如說是試圖模仿網紅所代表的中產階層審美。
網紅起初作為一個名詞出現,而后衍生出形容詞詞性。網紅臉、網紅穿搭、網紅店、網紅景點,通過與其他詞匯的聯結,“網紅”迅速構建出一個指涉龐大而復雜的能指集合,日常生活用語被大量“網紅化”。它們共同的所指,則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一線城市新興的中產階層生活方式。
1999年,一本名叫《格調》的譯作風靡中國大城市的圖書市場。盡管其初衷在于諷刺,卻也為中產階層確認自我身份提供了有效的指南。有趣的是,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Class,即階層。如今的網紅群體,是互聯網時代無處不在的“格調”。他們將中產階層審美,簡化為一套物質符號和外在編碼。
當個人的審美風格和生活趣味成為劃分階層的標尺,網紅符號的出現提供了一條捷徑——只需要通過對符號的消費及對編碼的模仿,就可以扮演一種中產階層的生活。這對于尚沒有工作收入的青少年群體來說,顯然具有更為切實可行的吸引力。更為關鍵的是,當這樣的中產階層審美被資本指認為是有品位、有追求的美好生活范式時,也意味著另類想象的可能性被消除了。當網紅審美被追捧為唯一值得踐行的審美,青少年便因此不能甚至不敢去想象更為多元的審美。
顏值經濟,景觀的拜物教
青少年對于自拍和網紅的熱衷催生了顏值經濟,在這種高度依賴互聯網的虛擬經濟中,“美”被異化為一種標簽、一種符號。顏值經濟的興起反映出當代消費文化審美語境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拜物教,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一書中所闡釋的“偏愛圖像而不信實物,偏愛復制本而忽視原稿,偏愛表現而不顧現實,喜歡表象甚于存在”。
根據2017年1月QQ社交指數發布的《年輕洞察白皮書》,“顏值”名列當下年輕人媒介使用習慣的首位。當顏值成為“正義”,個體價值的評價維度就會變得單一。青少年群體正處于最渴望得到承認和肯定的生命階段,單一的評價體系讓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個體不可避免地陷入焦慮。這時,一個聲稱可以讓人變美的行業,一個由品牌和醫美技術構成的消費主義符號系統就成了幫助青少年緩解、消除焦慮的新宗教。
然而這種焦慮是無止境的,消費主義的特征就是以提供個性的名義抹除個性。在顏值經濟中,更多的欲望被發明,更少的審美被肯定。青少年一旦放棄了對于自我身體和審美的主體性,而甘愿將自己放置在消費主義的評價體系中進行改造,那么等待他們的只能是在未來越來越苛刻的審美標準中迷失自我。
青少年的審美焦慮,是互聯網時代下的結構性困境,無法寄希望于個體成長后的自然覺醒和突破。因此,在資本輪盤高速運轉的今天,教育不能再局限于對于課內知識的學習和運用,更不能為審美設立標準答案。教育工作者除了要發揮好自己守望者的功能,關注消費主義對青少年造成的審美焦慮,更應該扮演好引導者的角色,幫助青少年樹立多元審美觀念。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責任編輯: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