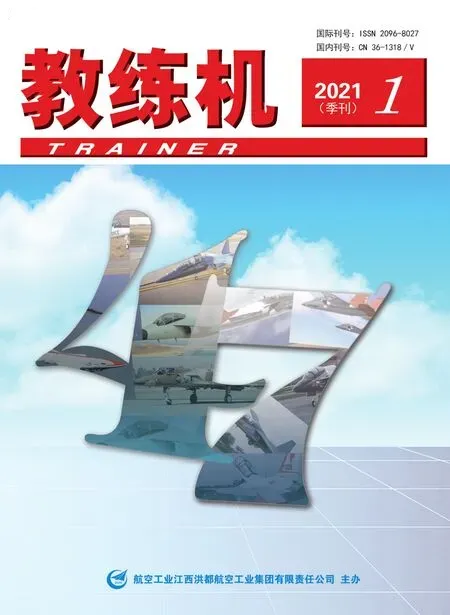軍用旋翼機對地支援與近距空中支援比較研究
徐 輝
(海裝駐南昌地區軍事代表室,江西 南昌,330024)
0 引 言
近距空中支援誕生于一戰,當時航空力量還是服務于陸軍的陸軍航空隊,陸軍在最初對陸軍航空隊的定位是:1)作為一種信號標識方法;2)進行火力支援;3)進行偵查與反偵查。具有主動性的飛行員很快就發現,飛機作為一種新興的航空力量遠不止完成陸軍規定的三項簡單任務,反偵查很快就發展成為奪取空中優勢,通過攻擊地面目標和空中目標來影響戰場的能力創造了戰略轟炸、空中遮斷和近距空中支援。 近距空中支援作為空軍的一項傳統任務,在后面的發展中地位也多次起伏,而空軍與其他軍兵種也正是在近距空中支援任務上存在諸多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這段時間,各軍種之間的辯論焦點集中在陸軍航空兵與軍種是否地位平等。傳統上,地面指揮官希望能保持對戰術航空兵的控制。1941 年在路易斯安那州開展二戰前的演訓,有限的訓練強調了飛機對步兵的近距離空中支援的戰略能力。在那些訓練期間,第一本關于空對地作戰的理論出版物出版了——野戰手冊(FM31-35),FM31-35 專注于陸軍保持對航空隊的控制,而不是空對地的整合,它也是第一本關于航空力量對地面部隊進行支援的條令性手冊。 二戰期間,近距空中支援首先在北非開展,期間的火炬行動(Operation torch) 和北非戰役就是對FM 31-35 的檢驗,不幸的是,盟軍在卡塞林山口戰役中遭到了慘烈的失敗。卡塞林山口的失敗推動了空軍總司令馬歇爾領導下的近距空中支援重組。 依據FM 31-35 開展的地面和空中的整體整合失敗,陸軍和陸軍航空兵認識到用新理論取代FM 31-35 的必要性。 于是以艾森豪威爾根據在突尼斯和卡塞林山口的行動而提出的新理論代表FM 100-20 替代了FM 31-35,成為地空一體化的核心文件。FM 100-20 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陸軍和空軍之間創造了一個理論上的平等關系,換句話說,這是美國空軍的“獨立宣言”。 FM 100-20 的發布,有效地簡化了空對地一體化流程,確保了空中力量應用的靈活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是一個摸索的過程, 作戰指揮官 “開發一種全新的空戰方法”,例如使用飛機控制組(aircraft control parties)、空中前進控制員以及用待戰飛機提供近距空中支援(計劃內和計劃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空對地作戰和關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空軍和陸軍各自將對方作為在己方的延伸。 不幸的是,二戰的慘痛教訓和取得的經驗很快就被遺忘了。
陸軍和空軍忘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進入了朝鮮戰爭,空軍戰略應用不可行。由于朝鮮戰爭,陸軍認為得到的支持不夠,基于朝鮮戰爭的教訓,陸軍計劃發展自己的飛機,以滿足近距空中支援的需求。
進入越南戰爭之前,空軍又忘記了朝鮮戰爭的教訓,出現了同樣的情況,這就要求在另一場戰爭中學習近距空中支援。越南戰爭中陸軍第一次使用了陸軍的近距空中支援(或者說是空對地支援),同時也見證了空軍支援水平的大幅提升。 越南戰爭之后,空軍和陸軍在對待空中力量對地面部隊的支援問題上,似乎找到了一種雙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美軍特別開發了A-10 來提供近距空中支援和反裝甲能力, 陸軍發展AH-1“眼鏡蛇”直升機,并在1973 年開始開發AH-64 阿帕奇(Apache)直升機,旨在填補陸軍近距離空中支援的角色和反裝甲能力。
越南戰爭和“沙漠風暴”之間的時期見證了以聯合作戰為重點的理論和政策的發展,越戰與“沙漠風暴”之間主要是形成條例時期,主要聚焦在空軍與陸軍作為一個整體而戰,而不是各自為戰。 “沙漠風暴”驗證了空陸作戰理論下的聯合軍事行動。在向全球反恐戰爭過渡的過程中,在阿富汗的行動重申了綜合規劃和發展陸軍近距戰斗攻擊的重要性。
總的來說,從某種程度上單一軍種并不完全擁有空對地支援任務,空軍是執行近距空中支援,其他軍種如陸軍幾十年來用直升機支援地面部隊,只是他們叫“近距戰場攻擊(CCA)”或者是“陸軍航空支援”等等;陸軍陸戰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也是用直升機開展對地面部隊的支援,他們也叫“近距空中支援”。各個軍種都不會放棄空對地支援任務,就像空軍理所當然不會放棄近距空中支援任務,陸軍也不會放棄空對地支援。每個軍種都在用適合自己的飛機開展空對地支援任務。 也正因此,陸軍與空軍在空軍獨立后開始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各自的空對地支援體系。本文也正是對美國陸軍與空軍建立在這兩個體系上旋翼機空對地支援及近距空中支援的運用進行梳理、分析和研究,為我國發展近距空中支援(固定翼及旋翼機)相關的體系、裝備和運用提供參考。
1 近距空中支援作戰
近距空中支援是飛機針對敵對目標實施的空中行動,它需要地面部隊與提供支援的空軍部隊進行詳細的規劃和協調,以確保安全有效地執行近距空中支援。它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實施,此時友軍部隊通常非常靠近敵軍部隊。“近距”一詞并不表示飛機與目標距離近,而是地面敵我態勢處于膠著狀態,決定性因素主要是由距離、火力以及調動引起的周密集成工作。
近距空中支援從請求的角度進行劃分,可分為預先計劃式近距空中支援和即時近距空中支援。
預先計劃式近距空中支援。因提前預見而被包括在首批空中任務指令分發文件中的近距空中支援需求作為近距空中支援預先計劃的空中支援請求提交。一旦近距空中支援需求在規劃流程得到明確,規劃人員將根據聯合空中作戰中心的作戰節奏提交近距空中支援的空中支援請求。只有那些在提交后有足夠時間被納入聯合空中任務周期規劃階段并得到空中任務指令支持的請求才被視為預先計劃請求。
即時近距空中支援。即時請求近距空中支援源于聯合空中任務周期規劃階段之外的情況。 需要認識到,可以用于滿足即時空中支援請求的空中資產已經存在于發布的空中任務指令中。由于這些需求無法提前識別,定制的彈藥載荷、傳感器或平臺可能無法用于特定的目標。為提供資源給批準的即時請求,較高層級的地面部隊(例如,軍、師)的空軍軍官/空軍聯絡官可以建議重新調整預定的近距空中支援任務、安排待命任務或將請求提交給聯合空中作戰中心。聯合部隊空中組成部隊指揮官的參謀部(例如,空中支援作戰中心)可能需要重新調整任務,以支持近距空中支援的即時空中支援請求。
近距空中支援作戰主要分為三階段 (即規劃、準備和執行):
1) 規劃
規劃主要分為接受任務、任務分析、行動方案制定、 行動方案推演和命令生成幾個階段,如圖1所示。

圖1 近距空中支援任務規劃
2) 準備
準備包含部隊在執行前提升自身作戰能力的活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動:演習、運動和觀察。

圖2 近距空中支援準備
3) 執行
近距空中支援的執行始于來自受援指揮官的目標提名,并涉及兩個在本質上連續而重疊的流程:聯合末端攻擊控制員/作戰中心協調和近距空中支援目標打擊。
2 陸軍空對地作戰
陸軍在FM3-04 條令中,將原來陸軍航空兵作戰相關內容統一到陸地作戰中的空對地作戰 (Airground operation ,AGO),AGO 是指同時或者同步在使用地面部隊和空中行動,奪取、保持空對地的主動權。AGO 的主要目的是支援地面作戰部隊。 AGO 主要意圖是將空中行動和地面行動進行全面整合。

圖3 近距空中支援執行

圖4 陸航空對地支援作戰框架模型
陸軍空對地作戰主要分為三種作戰框架,第一種是縱深打擊、近距作戰和安全維護;第二種是決定性、前鋒和持續支援作戰; 第三種是定點定時支援作戰。陸航空對地支援表現在作戰實施上,主要有以下作戰模式:
①機動接觸行動(Movement to Contact):集中力量搜尋敵軍;在指定時間以少量兵力對敵軍實施空中偵查監視;保持接觸并鎖定敵軍;根據指揮官意圖破壞、挫敗、瓦解、驅離和拖延敵軍。
②攻擊(Attack):陸航攻擊通常執行支援與敵軍近距交戰或尚未直接交戰的地面友軍。
③偵查搜索(Reconnaissance):通過航空目視或偵查設備獲取戰場上敵軍信息, 以及特定區域的氣象、水文、地理特征等可靠信息。
④安全性行動(Security):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域內對敵人行動提供早期的精確預警,這種作戰通常在安全區域與地面的負責區域安全的部隊進行同步整合。
⑤空中打擊(Air Assault):空中打擊是打擊兵力(戰場、戰場支援、軍種支援)使用旋翼機并集成可用的其他火力,在地面指揮官或空中指揮官的控制下奪取或控制關鍵區域。陸航實施空中打擊可支援主動攻擊作戰,也可以支援防守作戰。
⑥空中運輸(Air Movement):空中運輸是指利用旋翼機對部隊、人員、物資、裝備進行轉移。
⑦醫療疏散撤離(Aeromedical Evacuation):醫療疏散撤離提供直接支援、一般支援(GS),或在聯合作戰區域與聯合救援力量與陸軍衛生醫療系統開展支援。
⑧任務指揮支援 (Mission Command Support):為地面和空中指揮官增強戰場的任務指控能力支援。
⑨人員救援(Personnel Recovery):是在軍事、外交、國內事務上救援孤立狀態的人員。
美國陸航主要的空對地支援作戰任務,2015 年之前, 美軍在 2007 版 FM 3-04.126 以及 2011 版ATTP 3-18.12 中闡述的近距戰場攻擊 (Close combat attack,CCA) 與近距空中支援作戰樣式也極為相似。CCA 的定義是陸軍的飛機對與友軍近距交戰的敵軍進行的有計劃的空對地打擊,由于敵軍與友軍犬牙交錯,需要詳細的整合。 CCA 與CAS 不同之處是CCA作為陸軍的一種直接火力系統,發射武器的機載成員需要對火力打擊效果負責。 對于CAS,呼叫飛機進行支援的那個人需要對火力打擊的效果負責。 2015 年之后,美軍條令刪除了CCA 這一概念,在后續的條令中攻擊任務 (Attack) 中的近距攻擊任務(Attacks against enemy forces in close friendly contact) 與近距空中支援較為相類似。 根據美軍2015 版FM3-04 及2016 版ATP 3-04.1 闡述,近距攻擊任務主要攻擊與友軍近距離直接交戰的敵人,敵友距離從幾百米到幾千米范圍。
陸軍近距攻擊任務主要作戰流程是:
1) 支援任務規劃
陸軍空對地近距支援任務,由執行支援任務的機組直接與地面的火力支援組(FIST)、火力支援官(FSO)或前觀(FO)等機構進行協調。 協調的內容包括:
①態勢信息:含友軍位置、在支援區域的敵軍的防空威脅布局、任務請求程序、作戰區域坐標信息
②支援部隊的控制系統:作戰計劃系統,通信上的重要簡語,火力控制措施等
③火力協調信息:位置、BCT 野戰炮兵呼叫標識和電臺頻率,其他地面支援力量
④到作戰區域的進出路線:含途經點,到控制區或著陸點的航線
⑤與地面連級對接部隊的呼號及聯系頻率
⑥時統:全球定位系統,機載電臺與地面部隊電臺的時間基準,確保所有作戰單元時間的統一
空中任務指揮官和地面部隊的核心指揮官需要考慮在武器選擇投放之前對地面友軍的風險、對直升機的風險距離。
2) 實施交戰
在交戰過程中,機組要與地面受援部隊保持持續協調,確保受援部隊指揮官的意圖得以正確理解和實施。 需要對要打擊目標進行正確識別和標記。
火炮和迫擊炮是標記目標的常用和有效手段。但在用火炮或迫擊炮標記前要考慮支援力量暴露在敵人間瞄火力范圍內的風險,并要做好相應的協調措施。
注意:標記友軍時要特別注意,以防產生誤傷。
目標標記可幫助攻擊機組成員獲取目標位置,地面指揮官應盡量進行目標標記,目標標記可以是直接或間瞄火力,也可以是空中的FAC 進行標記。為了更有效,標記工作必須及時、精確并容易識別。在戰場中也要考慮到不同火力、不同目標、不同炸點對目標標記產生的混淆。 盡管目標標記不是強制的,但它的確可以幫助飛行員精確獲取地面態勢和目標信息,減少誤傷的風險。
3 )毀傷評估
空中機組需要為地面指揮官提供毀傷評估報告,便于地面指揮官判斷是否需要開展二次攻擊。
3 旋翼機與固定翼CAS 對比分析
盡管固定翼(FW)和旋翼(RW)機都可以執行近距空中支援, 但是二者的戰術運用和注意事項有所不同,并且在各軍種之間可能也會有所差異。主要體現在:
1) 執行近距空中支援程序的熟練程度不同。
陸軍通常不將其攻擊直升機(AH)視為近距空中支援系統,盡管他們可以在支援其他部隊的行動中使用近距空中支援戰術、技術和程序(TTP)實施攻擊。某些陸軍空勤人員可能精通近距空中支援戰術、技術和程序,但是,他們的熟練度將是有限的,除非他們有作為特種作戰部隊的一部分進行訓練,或近距空中支援戰術、技術和程序事先經過協調。 聯合末端攻擊控制員/機載前線空中控制員不應該例行要求陸軍飛機在沒有進一步協調和訓練的情況下執行近距空中支援戰術、技術和程序。
2) 機組編隊組成不同。
與固定翼飛機不同,旋翼機分隊或小隊可以多種飛機類型混編。例如,一支陸軍旋翼飛機小隊可能包含一架AH-64 和一架CH-47;而在陸軍陸戰隊,一支混編分隊將包含一架AH-1 和一架UH-1。 混編小隊賦予旋翼飛機近距空中支援單位最靈活的傳感器、通信能力、機動性、火力和相互支援組合。
3) 作戰高度不同
旋翼機的作戰高度分層為:
(1)高空。 離地 3000 英尺以上。
(2)中空。 離地 500 至 3000 英尺。
(3)低空。 離地 500 英尺以下。
固定翼飛機則是全高度均可實施近距空中支援,其中空/高空戰術的適飛高度在約8000 英尺以上。
4) 飛行途中通信難度不同
旋翼機近距空中支援平臺的通信往往是困難的,因為它們的飛行高度可能妨礙視距連通性。旋翼機起飛后,應盡一切努力,利用空中指揮控制資產、地面中繼節點、系留陣列或擴展低空通信覆蓋范圍的其他方法,維持對旋翼資產的指揮控制。
5) 途中戰術不同
旋翼機利用其低空優勢,途中地形跟蹤飛行剖面分為三類:低空、沿地形和貼地。
①低空。以恒定高度(離地100 至200 英尺)和空速進行低空飛行。低空飛行減少或避免敵方偵測或觀察。
②沿地形。沿地形飛行借助地貌或植被隱匿飛機,使之不被敵方觀察或偵測。空勤人員采用沿地形飛行,直至飛抵更高威脅區域。沿地形飛行的高度通常為離地50 至100 英尺。
③貼地。 貼地飛行,即飛行時在植被和障礙物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貼近地表,同時跟隨地貌。 地形和植被提供難以被敵方觀察和偵測的掩護和隱蔽。根據地形、天氣、環境光線和敵情,貼地飛行采用不盡相同的空速和離地高度。
但需要注意的是,旋翼機在低空需要特別注意地面武器的威脅(如肩扛式導彈,火炮等)
6) 飛入戰術不同
雖然近距空中支援固定翼飛機控制點和出發點可以用于旋翼飛機航線設置,但攻擊直升機空勤人員在近距空中支援目標區域采用旋翼飛機專用空域協調措施:等待區域(可以在整個戰場上建立等待區域,以供等待目標或任務的直升機使用。這些等待區域在使用時充當非正式的空域協調區。等待區域向旋翼資產空勤人員提供盤旋的區域)和戰斗位置(戰斗位置是包含旋翼資產射擊點(FP)的機動區域。與等待區域一樣,戰斗位置在使用時充當非正式的空域協調區)。
旋翼飛機空域協調措施(等待區域和戰斗位置的定位和指定)應在規劃過程中確定。這將有助于聯合末端攻擊控制員/機載前線空中控制員、空勤人員和機動部隊的整體態勢感知,以及確保航空計劃支持地面戰術計劃。
7) 任務簡報方式有所不同
旋翼機的近距空中支援,主要應用的還是CAS的9 行簡令。 在特定的條件下,陸航旋翼機用CAS 的TTP 實施CAS 時,如果飛得較低,有較好的態勢感知,其視角與JTAC 相差不大,并且在攻擊時目視不容易丟失目標的情況下,也會使用旋翼機的5 行CAS簡令(如圖5 所示)。

圖5 旋翼機的5 行CAS 簡令
8) 攻擊戰術不同
旋翼機由于其懸停特性,在攻擊戰術上與固定翼飛機有所不同的是可進行懸停射擊。懸停射擊是空勤人員從掩蔽位置解除隱蔽后或保持處在安全區域進行懸停射擊。為防止被敵方武器瞄準,空勤人員只在短時間內保持懸停射擊位置。需要注意的是,旋翼機在懸停過程中可能會不穩定。
4 結 語
自從空軍從陸軍分離出去后,在對待空對地支援的問題上,美國陸軍與空軍一直充滿矛盾,空軍的重心一直很難聚焦到近距空中支援上,并且在歷次戰爭中不斷的忘記上次戰爭的經驗教訓;陸軍也一直認為空軍沒有為地面部隊提供充分的支援。 越戰之后,陸軍開始發展自己的旋翼空中力量,空軍也開始發展專用的近距空中支援飛機,兩個軍種在近距空對地支援作戰上,也開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二者在指揮控制、作戰實施和程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陸軍從CCA 到空對地作戰(AGO)中的近距戰場支援,一直用自身的旋翼機特點探尋適合支援地面部隊的戰術技術與程序。 空軍在2000 年之后開始發展數字輔助近距空中支援,2010 年之后開始發展數字化近距空中支援(PCAS 項目),利用數字化網絡化的手段縮短空對地支援的時間、提升打擊的精度、降低誤傷和附帶損傷。未來,無論是近距空中支援還是陸軍的近距戰場支援,都會向著數字化、軟件化方向發展,并在JP 系列條令框架和聯合作戰的思路牽引下,在指揮控制、作戰程序上進行不斷的整合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