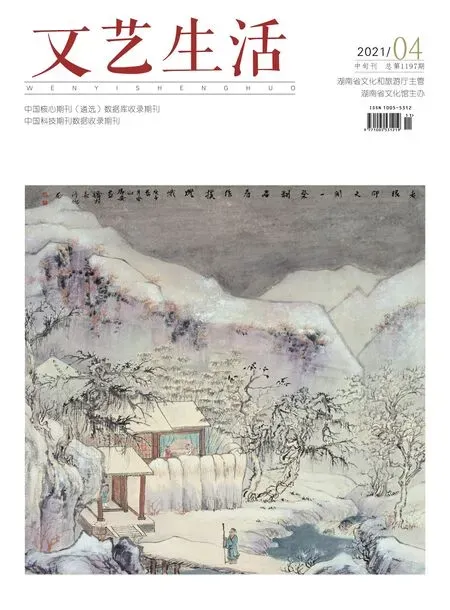啟蒙立場下“地之子”的雙重心態
——《地之子》中的批判性與眷戀性
董春曉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一、前言
臺靜農小說集取名為《地之子》充分揭示農民與大地的關系,所寫所述便立意于此并不斷延伸至農民群體的精神特征,寄寓人性探索。作者長期漂泊在外,接受科學理性的思想教育,同時又飽受羈旅漂泊的懷舊之情,造就了縈繞于懷的生命原鄉與相背而行的精神家園的交織互存的思想狀態,因而筆觸下的“羊鎮世界”展現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世界時,有著情與理的矛盾、糾纏,有著對痼疾的批判與鄉土的眷戀,從而成為小說集的特征之一。
二、對人性負面的揭露批判
以現實主義的視角觀照傳統農業鄉村世相時,作者見證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上的悲歡離合,辛酸苦楚,更見證了舊中國的農民群像與其精神世界,其中不免麻木愚昧的人性劣根。作者以啟蒙主義的立場再現古老鄉鎮的閉塞愚昧,披露人性負面,探索農民心理的動態發展。
魯迅曾言:“在爭寫著愛戀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到紙上的,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位作者的了。”[1]臺靜農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以人文關懷的態度觀照下層社會百態,面對故鄉的種種,以溫情精準的筆觸介入到農民生活中去的,文思凝聚的《地之子》中十篇鄉土小說的故事敘述構成了新的“魯莊”。在數千年來,封建傳統農業社會的隔絕中,作者強調典型環境的營造,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常從社會批判深入到人物內心揭露與批判,抒發人道主義的理想。
《天二哥》塑造了一身俠氣卻又欺軟怕硬的復雜酒徒形象——天二哥,他的身上內在精神世界里充滿奴性,同時又自大狂妄、自欺欺人,帶著些許阿Q精神。作者在贊揚他的俠氣品格時,也濃墨重彩的批判了身上的落后性。面對警察不合理的盤問時,他沒有畏畏縮縮反而動手打了警察。面對弱者時,天二哥絲毫無悲憫之心,反以強者的姿態霸凌,與小柿子打斗過程中受傷時倍感屈辱時認為,“只能縣大老爺和蔣大老爺可以打他”[2]。天二哥的思維與阿Q的自欺欺人、欺軟怕硬頗為相似,固有的奴性與麻木可見一斑。此外,值得深思的是,“喝尿解酒”的傳統藥方與天二哥的死是否有必然的聯系。答案毋庸置疑。這一細節的刻畫與當時人們的愚昧與社會的落后相呼應,將毫無科學依據的解酒方式奉為至寶,而這種陋習的產生的根源在于羊鎮的經濟水平低下,缺少經濟基礎便無法產生正確的意識形態。開篇敘述的鬼魂之談也在映襯羊鎮的軌跡止步不前,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浸淫。作者并不止步于此,繼續圖解思想根源——以地為載體的生活受限于如死水般難以流通的傳統農業社會的封閉性、閉塞性,而“地之子”便被賦予此般色彩。在描摹真實的鄉土畫卷時,作者采取新奇而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為切入點,著力于細節的渲染以剖析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再現病態鄉土的陋習與愚昧,往往有著舉一反三的效果。
另一個典型環境與事例的選取體現在《蚯蚓們》和《負傷者》中,不同程度的描繪了“典妻”的民俗現象。早在漢代,“典妻”的現象已被記載“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但尚未形成真正的典妻制度。五四運動后,啟蒙風氣盛行,“典妻”便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在臺靜農的筆下卻是閉塞落后的鄉村中的典妻制度的發展圖景。《蚯蚓們》開篇敘述了荒災連年,虹霓縣卑微渺小的蚯蚓們力求反抗而又無果的狀態,主人公李小借貸不成功遂而決心賣掉妻兒求得生存,四十文錢便斷送割裂與妻與兒的親緣關系。而在《負傷者》中敘述的卻是被動“典妻”的故事,主人公中吳大郎因自身力量弱小,面對蠻橫強霸的張二爺無法守護妻子與房子,只得依著幾串錢落魄他鄉。
《蚯蚓們》和《負傷者》中都提到了“典妻”這個傳統的制度,雖有主動和被動之分,卻是在同一語境中多重因素影響產生的結果。他們都處于傳統封建的鄉村社會,都處在男權體制與無視規則的弱肉強食中,其中婦女的命運權為他人掌控、成為男性的私有財物,遂而如同商品般任人交易。作者以批判的眼光揭示的陋習指向其產生的深層根源:
其一,數千年來的男權社會鞏固發展、對婦女的歧視導致女性地位低下且毫無發言權與自主權,也側面揭示女性的自我意識尚未覺醒,處于封建倫理觀、夫婦觀中麻木狀態,體現“典妻”制度受多重因素影響,從個人到整體、從當下回溯歷史皆默許此種現象的發生,是整個男權體制對整個社會的禁錮的直接結果。
其二,反映倫理觀念與基本生存需求沖突的矛盾,當男性個人的基本需求無法保障時,常常選擇將妻兒買出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認為是順理成章的流程,意在批判人性在與現實的較量中退步的抉擇,而這種抉擇是“人”的意識覺醒后所不能認可與容忍的。
臺靜農“從熟悉的生活中取材”[3],力求展現數千年來的價值觀下的鄉土圖卷,以文為戟,直批羊鎮世界里種種不合情理的陋習,這世界里有李小的“典妻”的行為、有《新墳》里說書先生等“中國式看客”的麻木冷血、有《燭焰》里吳家少爺“娶妻沖喜”的宗法制度、有《紅燈》里得銀娘鬼節祭拜的迷信思想。作者以啟蒙者的立場展現最真實的鄉土生活,揭露故土鄉民的文化心態,希冀刺破長夜難明的生存狀態,求得內在思想的進步、生命原鄉的發展。
三、對鄉土生活的多重眷戀
小說《地之子》是臺靜農濃厚的家國情懷的在文化形態上的抒發與寄托,是其批判與眷戀多重情感因素疊加的文學作品。作者一方面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熏陶,民主意識與人文意識逐步覺醒;另一方面,長久的漂泊旅居生活促進其對故鄉文化保留的價值觀、生活習俗重新審視。于是,能夠以帶有溫情色彩的理性思維看待“大地之子”的前行軌跡,以新穎犀利的目光探尋鄉土所保留合理的思維理念與生活習俗。
作者在敘述中并非如魯迅那般“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絕對客觀、犀利到底的冷嘲熱諷,也并非茅盾那般力求改革、銳意顛覆的激烈情感,而是思維構架始終回旋于故土一方,遂而那濃重的鄉愁融合了批判,混入了理性,更多的是對現象的揭露,注重“喚醒”沉睡的靈魂,具有“理智上面向未來,情感上回歸傳統”矛盾的懷鄉心態[4]。
以《拜堂》為例,故事的講述圍繞民俗“轉房”這一病態畸形生存模式展開,長兄去世后只留下了寡嫂,弟弟汪二便迎娶了汪大嫂。汪大嫂與汪二的婚姻雖建立在無可奈何的基礎上,但仍注重儀式感、敬畏感,“既然丟了丑,總得圖個吉利,將來日子長,要過活的”[5]。拜堂儀式雖然簡陋但完整,但對來日生活充滿了期待與希望,表達了在貧苦環境下謀生的堅韌之心。注重儀式感的“轉房”婚姻也表達著對傳統倫理觀、貞節觀的叛逆、挑戰。汪大嫂一方面直呼“丑事”,另一方面重視拜堂儀式感;一方面做著無奈的選擇,另一方面有著堅定的決心。文章中有著對偏僻閉塞鄉土的哀嘆,對底層人民悲苦生活的憐憫;有著對汪大爺整日醉酒等不思進取之人的批判,更多是對堅韌謀生之人的贊美。同時,汪大嫂等著力進取的人成為作者意圖的載體,企圖“喚醒”麻木懶惰的人,探求新的發展道路。
在《吳老爹》中側重展現吳老爹的傳統忠義觀念,吳老爹因受恩于油鹽店主人便用一生來堅守主人一家的起起伏伏的命途,雖有愚忠之心,但其忠誠、義氣仍不失為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美德,亦或是可認同為解決普遍存在的“看客”心態的方式之一。作者僑寓式的人生經歷,飽受他人冷眼,參悟鄉村陋習乃是普遍性的社會負面的縮影,于是在關照故鄉時產生精神依賴并感懷寄托,體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效性與積極性,表達個人情感歸屬,因而在賦予筆下作品批判性的同時,也極具眷戀色彩。
此外,《負傷者》中塑造了雖懦弱無知但初步覺悟的吳大郎形象,是對其覺醒抱有希望;《蚯蚓們》作者的意圖更為明顯,贊美無數個“蚯蚓們”的奮力反對不公平的佃農制度,反抗腐朽強權的封建統治階層,認可底層人民力量的潛力以及對新的人性化制度的期待。《為彼祈求》中則帶著人道主義的情感關照勞苦的下層人民,對命運的挫折與撥弄發出挽歌,逝去的人的一生則是故鄉無數個農人的剪影概括,是作者溫情遙望與救世情懷的自然流露。
作者的多重眷戀里既有淑世救世情懷的抒發,也有人道主義的關照;既有精神寄托的回歸,又有探求新路的嘗試;所寫既具有溫情,有涵帶理性的光輝。此種飽滿情感正如蹇先艾所言:“據我所知,“五四”時期的鄉土文學作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學或者被生活驅逐到那里,想找個職業來糊口的青年,他們熱愛他們的故鄉,大有‘月是故鄉明’之感,偏偏故鄉又在兵荒馬亂之中。‘等是有家歸未得’,不免引起一番對土生土長的地方的回憶和懷念。”[6]
四、結論
臺靜農是生活忠實的記錄者,他將舊中國整個鄉土生活濃縮在羊鎮世界里,將生活的辛酸與苦楚清晰載入寸寸方絮,為數千萬個底層人民探求大地與“地之子”無法割舍、相輔相成的關系。如其所言“人間的辛酸和凄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么?”[7]遂而寫作中,作者始終在感性與理性的交織悖行中前行,以溫情的眼光重新審視生命原鄉、以冷靜的心態重新認知精神根基,既有冷靜批判的思維展現,又兼具眷戀依托的心理結構。于是,作品破舊立新共存、批判眷戀相融于啟蒙思想,造就了立體化的羊鎮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