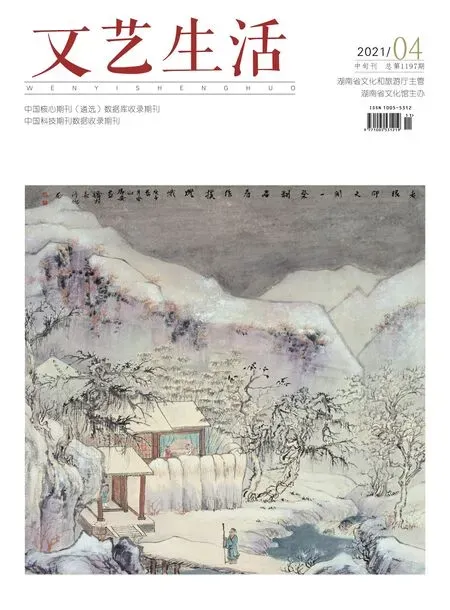從解構視角看海納·米勒的《電梯里的男人》
童 城
(廣州商學院,廣東 廣州 511300)
一、前言
1929年生于德國薩克森州的海納·米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年)是德國重要的戲劇家之一,他一生創作了30多部戲劇,為德國戲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電梯里的男人》是米勒1979年創作的短篇故事,在1980年被作為獨白插曲收入到米勒的戲劇《任務——關于一場革命的記憶》中。在這場荒誕的電梯之旅中,時間、空間、語言和文明發生了延異和消解,人這個身份被解構了。
小說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來講述故事的。非常焦慮的“我”,因為要去見領導,而坐上了里面都是陌生人的電梯,領導要親自布置任務給“我”。但是問題是,“我”連領導在第幾層都不確定。于是在不斷上升的電梯里,“我”經常看手表,希望自己不會遲到還能早到一會兒,但是事與愿違,“我”的手表顯示的時間亂掉了,“我”不知道具體時間,而電梯還在一直上升,因為“我”沒有按時趕到,領導在隔音的辦公室里開槍自殺。于是“我”責怪自己疏忽大意,在讀書時因相信“文學勝過物理”而不能利用物理知識解決電梯運行速度和時間之間的問題,導致領導自殺,而這個任務的內容也隨著領導的葬禮而成為了謎。最后,我隨著電梯降落到了秘魯,這里的秘魯不具有具體的地理意義,是一個陌生荒蕪的世界。
“我”走在泥巴路上,街道兩邊是一幅破敗的景象,還看到兩個野蠻的巨人。在這樣的陌生文明里,“我”感到害怕,因為“我”不能通過語言和當地人交流,也不能通過降落傘、飛機或者破汽車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很絕望,甚至懷念起之前像監獄一樣的電梯。“我”在想,或許假裝是個聾啞人還能博取當地人的同情,并得到救助。然而“我”想錯了,這里的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之前的兩個巨人化身成了沒有眼珠子的金屬人,好像沒有看見“我”一樣從我身后經過,這讓“我”失望的感慨“難道我都不值得被捅上一刀子或者被他們的金屬手勒脖子嗎?“我”被忽視了,在這個處在文明世界另一端的荒蕪區域。在“我”如釋重負地放下對“任務”的執念后,我歡快地繼續前進,路上遇到裸露的女子,還有在廢棄鐵軌上徒勞倒弄蒸汽機和火車頭的小男孩。除了在這里等待著人類的消失,“我”什么也做不了,當“我”明白了我的命運后,我脫光了衣服。在故事結尾,“我”甚至遇到了大寫的它者“DER ANDERE”,一個和我有著一樣面孔的對駝者(der Antipode),但臉是雪白的,我們當中只有一個能活下去。
二、時間的延異
男主角已經穿戴整齊坐上電梯,要去領導那里接受任務,那么肯定是約定好了具體時間的(Termin)。文章里第一次提到時間是描述男主角的心理活動“比約定時間提前5分鐘到才是真正的準時”,心理想完這件事他就馬上看手表,顯示的是10點。他心理充滿著輕松的感覺,因為離和領導約定的時間還差15分鐘,也就是說,10點15分是約定的見面時間,但是全文沒有一處直接提到這個約定的時間,而是用其他時間表達來代替這個時間,在這里約定的時間被延異了,散播在這一連串時間的符號上。正如德里達說到的延異令在場成為可能,同時也令在場跟自己本身產生偏差。再次看表時又過了5分鐘,也就是10點過5分。當電梯運行到八樓到九樓之間時,手表顯示10時14分45秒,他感到要準時是談不上了,因為時間已經不再為他服務。當他思考怎么盡快趕到領導那里期間,他又快速瞟了一眼手表,指針指向10點50分,而至于多少秒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感到他的手表出了問題,而他也沒有時間去算手表指示的時間離約定時間的差距了。這時他發現他已經是獨自一人在電梯里,之前和他一起在電梯里的幾個人都不知道什么時候下去了,于是他恐慌的目不轉睛的盯著自己的手表,發現表盤上的指針轉的越來越快,眨一下眼睛,就能過去好幾個小時,這時他才意識到時間已經混亂了。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我們會不自覺的和男主角一同通過這些時間表達來算出離約定時間還有多久,當在場的事物不能被表現的時候,我們就利用符號,我們就采取符號的繞彎方式來予以實現。這個在場的約定時間被播散在這些增補的時間符號上,這種通過增補實現的延異使時間的運作和運行變得可能,但條件是每一項“在場”的元素都要跟它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產生聯系,這樣就形成一個時間的鏈條,以至于它永遠都不能真正完全在場。
三、空間的延異
在故事一開場,男主角穿戴整潔出著汗站在被其他男士圍繞的電梯里,所以他首先進入了電梯這個空間。那么他要去幾樓呢?他說領導的辦公室在四樓或者第二十樓,而他還沒想清楚到底是哪一層,他就不確定起來。所以從故事的一開始,領導的辦公室這個空間就沒有被確定,是不在場的。而當電梯停下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到了8樓,因此男主角覺得自己要么已經超過了約定樓層(4樓),要么就是還沒到達20樓的一半遠。同時他感覺到時間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空間也在發生變化,當到達八樓到九樓之間時,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按時趕到領導的辦公室,于是他考慮在下一次電梯停下來時,出電梯并一步三臺階的從樓梯往下跑,一直跑到4樓。如果辦公室不在4樓,那他打算繼續坐電梯升到20樓,如果領導不在20樓,那么他打算回電梯坐到4樓,前提是電梯沒有停止運轉,若電梯壞了,他就得再次一步三臺階的跑下去4樓。他甚至想起著因為跑來跑去而斷斷腿扭到脖子,而在自己的要求下被人抬到領導的辦公桌前。他對任務的強烈渴望,驅使他孜孜不倦的尋找這個不在場的辦公室,他對“任務”的尋找構成了他人生的意義,以確定自己作為人的存在,但是那個我們可以找到的“我”,總是占據著“某個不可能搜索出來的位置,那是一個總是指向其他地方的位置”。通過“任務”,主人公才能確定“我”的身份,但是這個“任務”占據的位置——領導的辦公室正是一個不可能搜索出來的位置,這個空間在4樓和20樓之間來回飄移,永遠都無法在場。
四、語言的不在場
為什么男主角一心要坐電梯找領導的辦公室呢?因為領導要親自告知他這個任務的內容。這正符合了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和索緒爾語言學將演說(語言)等同于在場,因為言說伴有活生生的說話人的在場。說話人的在場必然聯系起聲音和感官,并指向理解:人們通常能相當好地理解說出的話。但是在時間和空間的延異之旅中,男主角永遠都不能按時到達辦公室,這導致了領導絕望而開槍自殺,而這個任務就永遠保存在領導的腦袋里,言說就無法實現,無法在場。而書寫卻是在場的,比如辦公室墻壁上掛著的領導的肖像是一種書寫,領導因開槍自殺而在右邊太陽穴留下的黑邊的洞口也是一種書寫。在男主角下電梯到了秘魯之后,他甚至決定要裝扮成聾啞人,以求獲得當地人的同情,聾啞人既聽不到聲音也發不出聲音,在這個無人之地,語言不在場,也失去了在場的意義。
五、文明的延異和消解
《電梯里的男人》這個標題就說明了,這個男人是存在于文明世界中的,因為電梯是人類的發明,但是電梯這個文明空間缺沒有把他帶到證明他身份的領導辦公室,確把他帶到了蠻荒的秘魯,而在電梯里他不停的看手表,手表也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但是最后手表確瘋狂了,不能再發揮它的功能。男子為了見領導,穿戴整齊,穿得像職員或者工人一樣,甚至還系了領帶。從電梯出來后,他看到的是一幅破敗的景象,窗戶玻璃都碎掉了的被遺棄的窩棚,充滿黏土和稻草的村子,文明來過這里,但是又拋棄了這里。在這個無人區,怎么證明自己的存在呢,男人開始擔心,因為他沒有降落傘,沒有飛機或者一輛破汽車來證明給別人看他是從文明社會掉到這里來的,而他身上帶的一點點錢在這里也起不了作用。接著他想起來那個讓他脖子闖不過氣的領結,他想讓這個文明社會的象征消失,他差點就把它扔掉了,因為這是文明留下的一抹痕跡(eine Spur),而到了故事結尾,男人甚至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脫下來扔掉了,因為在這里,外表已經不重要了。在路上,他還遇到裸露的女子,在文明的社會里,人類是不會在公共場合裸露的,還有在廢棄鐵軌上,兩個小男子在搗弄蒸汽機和火車頭,而男人則從歐洲人的視角出發否認了他們工作的意義性,也就否認了文明在這里的作用。在這個故事里,“文明”通過電梯、手表、領帶、窩棚、村子、降落傘、飛機、破汽車、金錢、衣服、蒸汽機和火車頭這些符號延異和播散出去,并最終消解。雖然在這個荒蕪的地方有兩個金屬巨人,但是他們卻是沒有眼珠子的人,無視男主角的存在,這正是對文明的巨大諷刺,因為金屬制品是文明的象征,但是眼珠子作為一種增補卻不在場,這樣就消解了文明的意義。
而男主角也最終發現,在這樣荒蕪的風景里,除了等待人的消失,什么也做不了,人的身份在這個故事里通過時間、空間的延異、語言的不在場,隨著文明的消解而一起消解掉了。而德里達在《他者的單語主義》里也曾說到“身份從來不是既有之物,它不可接收,也不可獲得;有的只會是永不休止、模糊不定、虛無幽幻的身份認同”,“身份并不存在,只有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