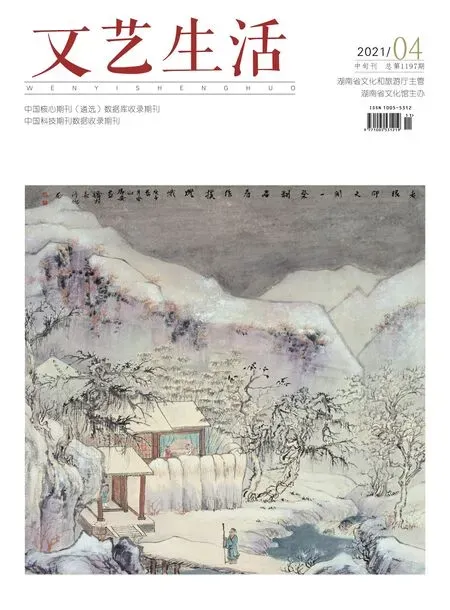楚舞審美特征的自然人文成因研究
楊木子
(鄭州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0)
一、引言
屈原在《離騷》開篇中寫道“帝高陽之苗裔”,由此印證了楚人的中原身份。當我們站在21世紀回首過去,從沉睡在地底千年的文物以及那位文學巨匠所留下的偉作中窺探歷史遺留下的痕跡,不禁驚嘆,這個曾被商王朝從中原地區驅逐的小小部落,歷經了千百年的“南遷”后,成長為八百年不倒的戰國七雄之一,并形成了同時期與羅馬文化相并論的文化。一個時期的樂舞如同該時期文化的藝術符號,必定是對于該時期文化的反映。同時,一個地區的文化必定會受到該地區自然環境、歷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
二、水的孕育
楚國特殊的生態環境勢必會孕育出楚人樂水的情懷。楚人在歷經千百年的南遷后,最終在今湖北荊州地區定居下來,開始繁衍生息、開疆擴土。從戰國時期楚國疆域來看,楚地東臨黃海,幅員遼闊,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常年氣候濕潤,雨水豐盈,中國兩大河流黃河、長江都流經楚地,形成縱橫交錯的自然水系。這個被水孕育的國家必然在其骨子里就帶有“樂水”的情懷。楚人樂水的思想自然也影響了楚舞。由于楚樂舞的藝術形態是高要求的模仿水態,因此對舞蹈表演者有著極高的要求,便出現了“風肉嫩骨”、“小腰袖頸”的要求[1],對水的模仿促成了楚舞的輕盈飄逸之感。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古文獻中找到證明,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谷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2],楚人祭水,不祭山。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河伯”、“湘君”均是與水相關的水神形象,但有關于祭山神的僅有《山鬼》一篇。漢成帝之后趙飛燕是漢代著名的皇室舞人,此女“腰骨尤纖細,善禹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他人莫能學也”[2],其中所談到的“禹步”就是流傳于戰國時期的一種舞步,其動態模仿大禹治水時的動作。由此可見,水的意識廣泛存在于每一個楚人心中。同時,水意識在楚舞的舞姿風格上也有所體現,“楚王好細腰,百姓多餓死”,楚王對于細腰的癡迷,影響了楚人對女子體態身形的審美。屈原的作品常提到“偃蹇”、“連蜷”這樣的詞匯,《九歌·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2],其中的偃蹇形容的是女舞者腰肢纖細的樣子,《九歌·云中君》曰“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2],“連蜷”所形容的便是女舞者長袖高拋的動態形象。舞者飄渺輕盈的長袖猶如波瀾的水浪,與楚王所好細腰形成的S型三道彎體態更是象征著煙波渺渺的水形象。
因此可以說,楚舞長袖細腰,輕盈飄逸的風格特征正是在楚人的“樂水”意識之上形成的,又或是說長袖細腰、輕盈飄逸的楚舞在這種特殊自然地理環境所孕育而成的水意識之下形成,這是水意識在楚人思維意識作用下的實際產物,是楚人對于水波蕩漾的水形態的模仿。
三、鳳的尊崇
自古以來就有龍鳳呈祥之說,龍和鳳一直以來作為人們作為尊崇的兩大圖騰。楚人崇鳳,傳說楚人的祖先火神祝融便是九鳳神鳥的化身,被尊奉為火神,掌管與火相關的事宜。漢代《白虎通》曰,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卞鴉·絳鳥》曰:“鳳凰屬也”,《楚辭》中有著關于“九頭鳥”的記載。因此可以說楚國的鳳圖騰崇拜是自其祖先開始一直延續的。
楚文化遺存中大量存在的“鳳鳥”形象和“人首鳥身”的圖案表明,楚人對鳳的崇拜超過了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而且先秦時期,以鳳喻人的唯有楚人[3]。從戰國楚墓中出土的含有大量鳳圖騰以及鳳獸合一的漆器、絲織品等文物中深刻的體現了楚人的尊鳳意識,如2002年湖北荊州天星觀2號戰國楚墓出土的“虎座鳥架鼓”,虎座鳥架鼓作為楚人鳳崇拜的代表象征我們可以對其形進行進一步分析,基本結構為在一對重心后靠仰頭卷尾的臥虎之上站立著一對背向而立的鳴鳳,鳴鳳氣宇軒昂,英姿颯爽,其間駕著一面大鼓。從這站立于虎背的鳳鳥形象反映出鳳凰在楚人心中的地位以及鳳凰這一圖騰符號所象征的降服猛獸之意,同時從側面印證了鳳形象在楚人中崇高的地位。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湖北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鳳龍虎紋繡羅禪衣”,鳳、龍、虎的形象共同出現在這件絲織品上,鳳紋肆意灑脫,此禪衣上出現了鳳腳踢龍,鳳翅擊虎的動態構圖,所形成的S型鳳體態與楚舞的S型三道彎體態讓我們不禁想到了楚舞的S型三道彎體態,我們可以推斷出楚舞的S型三道彎體態是對于鳳體態的模擬,也是人們對于崇鳳思想的舞蹈體現。
楚人的尊鳳意識還影響了楚舞“長袖飄逸”的審美特征,楚人崇天重巫蠱祭祀,認為上天具有一種神秘力量,它主宰著世間的萬物,而鳳凰作為神鳥,如鯤鵬能扶搖而上九萬里,能翱翔于天,有著“通天”的本領,鳳鳥能翱翔于天地之間,是因其有著一對豐滿且飄逸的羽翼,這一思維方式影響至楚舞之中,便出現了了與鳳鳥羽翼相對應的長袖,長袖不僅彌補了舞人上肢的缺陷,使舞姿更顯輕盈飄逸,更是一種模擬鳳鳥羽化成仙思維的體現。楚國的巫師作為與上天意志的傳達者,其通天的方式便有著模擬鳳鳥飛翔的動作以及姿態。楚人的尊鳳意識體現在舞蹈中促成了其長袖飄逸的審美特征,同時更為其蒙上了一層神秘、羽化登仙之意境。
四、楚國的巫文化
早在原始時期,由于知識的匱乏,人們對世間很多現象都無法解釋,于是在人們意識之上便構建起一種萬物有靈的崇拜,認為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主宰著世間的萬物。在此基礎之下“巫”產生了,它是人們祈求平安幸福、祛災逐難的關鍵人物。《漢書·地理志》中談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荊楚之地自遠古以來便有著尚巫的風氣,楚人熱衷于占卜術,大到國家命運,小到家人健康,都重巫術祭祀,因此,楚文化又被稱為巫文化,其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表現出濃厚的巫風色彩。
楚國舞蹈中以巫舞最盛,其中所透露出的詭秘、浪漫的審美特征便是受到了巫文化的影響。但其浪漫不是指代我們現今理解的浪漫主義流派,不是對于古典主義的反叛,而是基于楚國巫蠱祭祀盛行的巫文化而形成的特殊的浪漫,是一種夾帶著詭秘巫術的浪漫。巫文化對于舞蹈最直接的產物就是巫舞,楚地民間、宮廷巫舞盛行,在楚國的巫師的地位極高,在楚國男巫稱之為“覡”,女巫成為“巫”。巫與舞從本源上就存在某種關聯,甲骨文中最早出現的“舞”字與巫就有著某種象形關系。作為人神之間的傳達者溝通者,舞蹈就是巫師們通神時的手段。每逢祭祀神靈時,巫師通過如癡如醉、極盡癲狂的舞蹈動作來通神,傳達神的意志。
屈原的《九歌》便是對楚國巫文化以及巫舞最好的例證,全文共十一篇,每一篇都有相對應的神靈形象,“巫”在其中作為神意志的傳達者,巫舞作為巫師通神、娛神的主要方式自然也存在于每一篇章之中。同時《九歌》中存在著大量對巫舞的描述。
“神靈”是人們對未知世界恐懼產生的萬物有靈崇拜下形成的一種思維意識概念,是人對世間萬物未知的精神寄托,凡是與神靈相關的事物自然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巫作為人神之間溝通的傳導者,那么作為通神手段的巫舞自然也就帶有著詭秘、恣肆之審美,同時還折射出楚人渴望羽化登仙的審美心理,這一審美心理至今還影響著編導家們。
五、結語
楚舞藝術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藝術瑰寶。楚地多水的自然地理環境、對鳳鳥的圖騰崇拜以及盛行的巫文化孕育出楚舞“翹袖折腰”、“輕盈飄逸”的風格特征、詭秘浪漫的基調以及羽化登仙的審美意識,從而形成了S型三道彎的體態。而其長袖細腰的舞姿造型和和神秘、浪漫、羽化登仙的精神氣質沖破了時間的巨浪,一直影響至當今的古典舞表演體系及舞蹈創作。不僅是以舞姿動態而存在,更是一種精神層面的追求。當然,影響楚舞審美特征的因素遠不止此,楚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瑰寶,具有極高的人文精神境界和極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對當今社會建設文化自信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