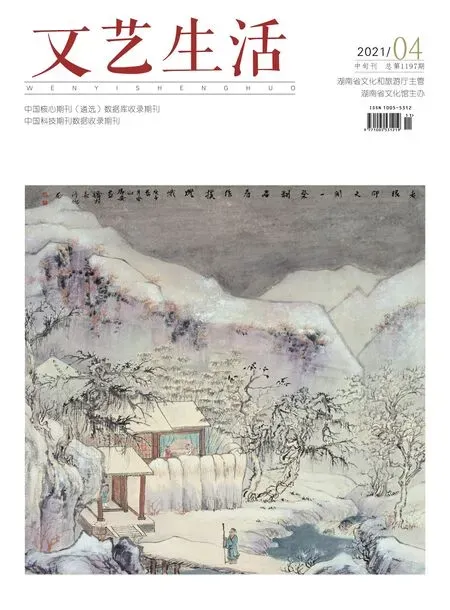淺析影片《小丑》中影視聲音的運用
韋夢媛
(南京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電影聲音包括音樂、音效、人聲。三種聲音互相交織,與視覺造型一起構成了電影的美學形態,起到了敘事信息的傳達、環境再現與主觀表意等作用。在影片《小丑》中,聲音不僅配合畫面的色彩與構圖,勾勒了環境氛圍,更是作為獨立的元素推動了敘事,延伸了影片內涵。本文將從以上兩點對《小丑》的聲音進行鑒賞解析。
一、聲音對環境的塑造
(一)鮮明的音樂風格奠定影片基調
《小丑》這部影片的故事獨立于DC宇宙主線,建構在一個虛構的環境當中。根據哥譚市的風貌與生活環境來看,這與美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社會風貌相似。當時美國遭遇經濟危機,政府投入社會福利領域的財政大量減少,人們逐漸對政府的公共服務不滿。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群,他們之前依賴的政府服務或救濟在削減甚至停止,小丑亞瑟便是其中之一。[1]因此,整部影片的基調是昏暗、蕭條、壓抑、陰暗的。
在背景樂的選擇上,除了以交響樂,影片的一大特色是使用了爵士樂。爵士樂起源于底層人群,帶有悲傷的底色,在表現形式上卻又有滑稽、跳脫之感,與歡樂融合。這與小丑的命運與性格相契合。影片最開始,亞瑟身著小丑服裝轉廣告牌時,就在環境中設置了彈鋼琴的街頭藝術家角色。這暗示了亞瑟身處社會底層,人民生活困苦。蕭條的環境也與歡快的音樂形成了鮮明對比,充滿了對亞瑟人生的諷刺。這里的爵士樂既是環境聲,也是背景音樂,將場景布置與氛圍烘托進行了完美的銜接融合,通過視覺與聽覺的結合達到電影美學效果。
此外,從爵士樂的發展時間開看,八十年代是爵士樂走向衰落的時間段,很多街頭的爵士酒吧都面臨倒閉。這對亞瑟滯后、封閉的生存環境起到了影射作用,傳遞出一種下沉的情緒。隨著人物的心理變化,體現環境氛圍的音樂風格也發生了改變。影片的后半段以搖滾樂居多。搖滾樂是在七八十年代開始發展興盛的音樂,其核心就是墮落、發泄與反抗。在亞瑟轉變為小丑后,跳著舞去莫瑞秀的路上,就選用了搖滾樂,表現出此時亞瑟情緒上的高漲,人格轉變后的性格變化,也使整個影片情緒被推向爆發與高潮,傳遞出一種上揚的情緒。
從聲音特性的角度來看,音質、音調、音長、音量變化、器樂的選用等是把控音樂整體情緒的幾大要素。影片背景樂的主要樂器為大提琴,其音色十分低沉,且并不悠揚、連貫,而是緩慢、跳躍、不規則、無節奏的。其音量忽大忽小,音調忽然低沉、又忽然高亢。弓在琴弦上的拉奏非常的毛糙,常常有“吱吱”聲傳出,仿佛拉琴人的手失去了控制,使音樂顯得無力、疲憊又怪誕。這樣的音樂破壞了影片的節奏感與流暢度,奠定了影片頹廢、虛弱與病態的底色。
(二)音效對環境的塑造
除了為影片奠定悲劇、恐怖底色的音樂外,音效的運用使得電影對社會環境的描繪更加立體完善、細致真實。電影開場時,聲音先于畫面出現,強調了聲音內容的重要性。這里的聲音是廣播里播報著城市垃圾成堆、已經到了近十年最嚴重的情況,直接指出了哥譚此時破敗、蕭條的景象,也暗示著亞瑟的心理狀況——他殘破的人生與人格已經被逼到了最為緊張的時刻。這樣充當環境敘事的播報后面還在不斷地出現。比如電視里播放的“鼠滿為患”的新聞。“鼠”象征著哥譚底層卑劣的人民,“超級鼠”則暗示著上層社會的資本大鱷,他們本質上也不過是造成社會黑暗的大老鼠。
尖銳的警報聲也是影片重要的音效元素,并且貫穿全片。在亞瑟獨自在家寫筆記時、回家遇到母親被送去醫院時、從女鄰居家出來時,都或近或遠地存在著消防、警察或是醫院急救的鳴笛聲。這不僅暗示著社會治安的混亂、危機四伏,其高頻聲急促的效果也使觀者的神經更加緊繃,豐富了聲音的層次與維度。在亞瑟通過信件,看到了自己的父親是韋恩的時候,外面響起了警報聲,這里警報也是亞瑟精神緊繃的線索。
地鐵行駛的聲音也是音效中的一大亮點。如亞瑟被老板質問、在路上對著垃圾袋發泄時背后行駛過的列車;跟蹤女鄰居時,第一次殺人時,乃至成為小丑后在地鐵上的逃竄時,都運用了地鐵的音效聲。地鐵在軌道上行駛時的金屬聲,和與空氣摩擦發出的尖銳聲音,營造出了沉悶又懶散的感覺,高頻的顫動使得影片氛圍與亞瑟更加神經質。
二、聲音的敘事與符號化
(一)特定選曲對劇情的推動
影片中很多歌曲選用的是以前的一些老歌,這種選曲并不是空穴來風,其中有很強的象征性意義。
在地鐵上,面臨失業危機的亞瑟遇上了三個調戲女生的小混混。這時,亞瑟不合時宜地狂笑病再次發作,引起了三個男人的注意。他們向亞瑟走來,嘴里哼唱的歌正是萊尼斯·瓊斯的《小丑進場》。這里三個混混的走近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正是為了放緩影片的節奏,突出強調這首歌,推動氣氛劇情。亞瑟實際上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他的體內寄存著亞瑟與小丑兩個靈魂,影片講述的也正是他從低聲下氣的亞瑟轉變為無惡不作的小丑的過程。這里的是亞瑟第一次殺人,第一次開始以小丑的身份去與世界對抗,《小丑進場》既暗示著此時他身份的轉換,也象征著他即將開啟人生的全新篇章。
鄰居蘇菲的出現使亞瑟對生活短暫地充滿了希望。在家中,他拉起母親翩翩起舞,此時音樂選用了弗蘭克·西納特的《That’s life》(這就是人生)。其旋律與歌詞既蘊含了對人生的無奈與嘲解,也展現出了一種樂觀向上的狀態,表達了人生的困難只是暫時的,成功會在不久后被奪回的信念。蘇菲這個角色本身就是精神病人亞瑟在兩重人格斗爭中,為了排解主人格亞瑟的悲慘陰郁,自己的妄想出的角色。這首歌反映了亞瑟此時精神的舒緩,對人生抱有短暫的希望。也因為這種希望的虛假性,更蒙上了一層悲哀色彩。而精彩之處,在影片的末尾,亞瑟人格已經完全淪為小丑人格時,影片亦是以這首歌結尾,形成了呼應,使影片在縱向上產生遞進關系。畫面中,被追逐的小丑四處逃竄,卻再次翩然起舞,使前后兩次在不同人格狀態下的舞蹈形成了對比。這里歌曲表達的不是對負面情緒的排解,而是凌駕于人生的釋然感,在敘事上暗示著此刻成為小丑的亞瑟,才完全達到了他心目中的人生頂峰。
在脫口秀俱樂部表演時,亞瑟失敗的表演隨著音樂《Smile》的響起而噤聲,臺下的觀眾笑聲不斷,這也是亞瑟的精神妄想,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這里的音樂有一個環境現場聲與背景音樂聲主次的轉換,這是亞瑟在現實與想象中的世界切換的標志。歌詞的第一句就是:“當你的心在疼,但還是要微笑。”這象征著,對于失敗,亞瑟選擇了以幻想進行自我麻痹。此外,《Smile》這首歌出自于影片中頻頻出現的《摩登時代》。這部影片對資本家們進行了批判與諷刺不言而喻。影片選用的歌不僅形成了橫向上的聯系,也在敘事層面上賦予了影片深度,對現實進行了影射。
(二)小丑之笑
小丑的笑在其中是很特別的一個單元。其怪誕尖銳,切持續極長的難聽的笑,既破壞了敘事節奏,將影片的氛圍塑造的凝滯逼仄;也作為線索,表現了精神分裂的亞瑟雙重人格的不斷轉換。
在公交車上,亞瑟被小孩的母親惡語相向時,他忽然爆發出了止不住的大笑。亞瑟每次控制不住笑,都是在遭受不公正、不友善的待遇時。這時作為社會底層的亞瑟是沒有辦法進行反抗的。笑聲是他第二人格“小丑”的象征,暗示著他心里其實住了一個時刻想要挑事的小丑。控制不住笑,說明此時小丑人格還是里人格,且不受亞瑟人格管控。當蘭道爾嘲笑侏儒蓋瑞時,亞瑟跟著哈哈大笑起來,在走出化妝間的瞬間又止住了笑。侏儒蓋瑞象征著和亞瑟一樣的弱勢群體,亞瑟對他只有同理心。但同時亞瑟為了擺脫弱者身份,又努力去合群。這里的笑是可以控制的假笑,是亞瑟的一種被動的“迎合”。而在地鐵上,亞瑟遇到小混混欺負女孩,第二次開始止不住哈哈大笑。這是人格轉化、體內挑事的小丑即將登場的標志。第一次殺人后,他出現了耳鳴與錯亂。這里的聲音暗示著他體內的兩個靈魂在打架,產生了矛盾,轉換還不完全。在亞瑟弄明白自己的身世后,他再次控制不住大笑起來。但這一次除了小丑人格之笑,還有滿臉的眼淚。這種半哭半笑的表情,代表了在“亞瑟”與“小丑”人格的碰撞斗爭中,“亞瑟”的人格的失敗,小丑人格逐漸掌控了他。到影片的最后,亞瑟與充當兩種人格調和者的臆想的心理咨詢師會面時,毫不費力痛苦、放肆地大聲笑著。這里的笑已經可以控制了,象征著此時他已經完全淪為了小丑人格。
三、結語
作為一部傳記式的故事片,《小丑》的聲音運用賦予了影片更豐富的視聽體驗與內涵價值,在塑造環境與人物形象的功能上起到無法替代的作用。通過獨具年代感的音樂,影片對時空進行了精準的定位;特殊曲目的選用與極具符號意味的音效又是推動劇情、塑造人物的重要線索。在陰冷的音樂下,環境更加地冷酷了,悲劇意味也得到了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