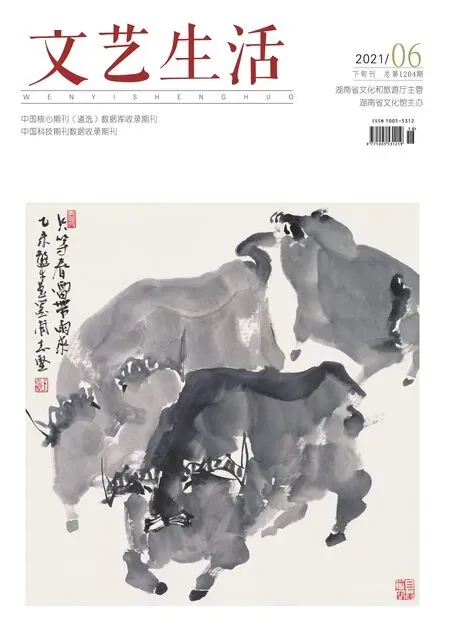中國戲曲舞臺的觀演關系變遷
——以《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為例
劉兆霏
(中國藝術研究院 科研管理處,北京 100012)
一、迎神賽社禮節的整體程序
1986 年,山西省潞城縣發現了《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其中比較詳細的記載著當地的賽社習俗,所記載多為官辦賽神社,其由管家統籌,聯合村社,舉行大型的祭祀活動,主要祭祀“土地神”,目的為酬神許愿,驅邪祈福,以求生活富足,人丁興旺等。官賽的規模很大,每五年舉行一次,村民把此祭祀活動看作是能夠保證家人平安的重要活動,幾乎全村的男子都會參加。因而,對于村民來說,他們不但是此祭祀活動的觀者,同時更是此祭祀儀式的參與者,甚至在此儀式的某些環節,更充當了表演者。
“官賽一般在正月初八,初九和初十舉行,即分為‘頭場’、‘正賽’、‘末賽’三天的演出。在頭場之前,有上香會的迎神儀式,主要是一種臺神游街的巡行活動,將各廟的神袛迎至辦賽的主廟內。在正式的三天賽期,每天一早由‘維首’(辦賽總負責人)和‘主禮生’等主祭唱禮,向神袛供盞七次,并同時由樂戶獻上樂隊和隊戲。而在七次的供盞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表演項目。供盞完畢,則在神殿外的舞臺上演正隊戲,院本和雜劇等戲劇。”①因此,在整個賽社的程序中,大抵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即:供盞前的祭祀活動、供盞儀式中的供奉儀式同演出并行,以及供盞完成后正式的戲劇演出。馮俊杰先生曾說:“《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中記載的三天賽社演出,實際上走完了戲劇史的千年里程。從拜殿到舞臺的節目轉換,則完成了戲劇生命的創造。浩大的演出場面與新劇種的及時吸收,又預示著戲劇在當時的廣闊前景。
可以說,賽社本身就是一部運動著的戲劇史。”②在整個賽社程序中,參與的村民們在其中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戲劇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由“演者”至“觀者”的演變。
二、由祭祀到演出之觀演關系的變遷
(一)供盞前迎神儀式的“演者”
供盞前的迎神活動中,村民里“觀”這個角色是不存在的,他們所扮演的是“演”的角色,觀者則為村民要迎接的神。充滿儀式感的祭祀迎神活動滿足了人對神的精神寄托也滿足了自己的精神慰藉。就好比現在北方地區每年的農歷新年,人們要在除夕夜前用燒紙錢,祭酒等方式將家中故去的親人迎至家中共同過年,都是為了滿足人的心理慰藉和對親人情感的寄托。因此在祭祀環節,其目的即為娛神,使用“上香會”、“巡游”等具有儀式性的方式迎接神的到來,所有賽社的參與者共同扮演的均是“演”的角色,村民用祭祀儀式的方式虔誠的將神請至此處,才可以延伸出接下來的供盞環節和戲劇表演環節,而供盞后的戲劇演出劇目,也是同供盞前迎神的目的,儀式相呼應,或是驅妖,或是保平安。
(二)供盞中觀演關系的變遷
在整個賽社程序的中心部分——供盞中,“觀者”與“演者”的定義其實是模糊的,參與者既是賽社的“演著”,為所迎來的神供奉酒食,是祭祀儀式的重要參與著,同時又扮演了“觀者”的角色。“在七次供盞中,有不同的表演項目。在供盞前先由人扮星宿出場,然后奏樂,陳列隊戲,開始供盞。
供第一盞時,樂隊獻上《萬壽歌》、《天凈沙》、《長壽歌》等樂曲;獻第二盞時則靠樂演唱;供第三盞時獻曲破;由第四至第六的三次供盞,則獻演供盞隊戲,例如有《尉遲洗馬》、《關公斬妖》、《古城聚義》、《目連救母》、《天仙松子》等。在第七次供盞時,則合唱收隊。”③自“扮星宿出場”,村民是“演者”,“演”的目標群體為參與供盞儀式的其他村民,此時扮演星宿的人已不是他本人,更像是巫者,是溝通人與神之間的媒介。在供盞儀式時,村民為神敬奉酒食,此時星宿的扮演者同供盞者又互為觀演關系,也同時滿足了對方的心理慰藉需要。
不同于供盞前的迎神儀式,在供盞時,儀式的觀賞性和娛樂性逐漸加強,從第一盞至第七盞,從音樂演唱到隊戲和隊舞,表演性也逐漸增強,供盞過程亦經歷了娛神性減弱,娛人性增強的的過程。參與者則為“演者”,既演給神靈,表達對神的敬畏,又是“觀者”,觀看了供盞中演出。雖然此時“觀”與“演”在參與者本身同時存在,但其更多承擔的是之于神的“演者”角色,供盞儀式是以祭祀為主體的過程,參與者更多的是在供盞程序中祈神求福,供奉神靈。
(三)戲劇演出中的觀演關系
供盞儀式結束后,則開始了正式的戲劇演出。賽社活動中的演出節目始于隋唐,終于明清,戲劇演出也經歷了正隊戲-宋金雜劇-院本-雜劇-傳奇的歷史演變。在正對戲的演出中,《過五關》是經常演出的劇目,亦屬“關公戲”。關公戲本為驅邪趕貴的儀式性戲劇。在此,關公的形象并非三國故事中的關羽,而是人們所賦予的類似驅邪除妖的角色而出現,具有神性,關公戲跟整個官賽迎神——供盞——戲劇演出達到祭祀禮儀上的相互呼應。而作為隊戲,即有一個不同于一般戲曲的表演特點。因賽社禮節中迎神,供盞等祭祀禮儀活動的地點往往是在一個地方舉行,但是其影響是涉及到很多村落的。因此,隊戲在表演過程中的所謂舞臺是不停轉換的,往往不是限定在舞臺上,甚至不是限定于同一個村落的。其隨著劇情的發展和情節的變化不斷變換演出地點。如在《過五關》的演出中,“就是由村民裝扮成關羽,甘糜夫人,部將等人物,騎馬乘車,沿路表演。每到一關,即登上舞臺與敵將對壘開打,然后又車騎驅馳,再到另一個舞臺。如此路上往復表演,甚至過了五關斬了六將才告結束。”④早期供盞后戲劇演出中的正隊戲似乎同供盞儀式中第三盞至第六盞的儀式性演出差別不大,甚至在供盞演出中,亦有《關公斬妖》等關公戲,似乎一樣講述的關公除妖的故事,但《關公斬妖》的存在形式更有可能的是“啞隊戲”,即民間歌舞或隊舞,其無唱詞和念白,演出時間較短,相對正隊戲而言,戲劇性和可觀賞性偏弱。因此,在功能上,供盞后的關公戲——《過五關》戲劇性更強,增加了唱詞與念白,更加貼近了戲曲以歌舞講故事的特點。其表演娛人性增強,娛神性減弱,從觀演關系上,參與者更多的是“觀”的角色。但是《過五關》演出中,觀眾對演出的參與性極高,如在演員騎馬乘車、沿途表演,從一個舞臺到另一個舞臺的過程中,如何分辨哪里是舞臺?演員從一個舞臺下來,騎馬至另一演出舞臺之間的這段演出,也是戲劇表演的一部分,而在此過程中,之前的“觀者”同時又成為了這場戲劇的參與者即“演者”,演員一定伴隨著“觀者”的追逐,甚至扮演敵將或者其他劇目中扮的被驅逐的“妖”極有可能也要面對“觀者”的打罵驅逐。因此,此時的戲曲舞臺或許并不是僅僅設定于舞臺之上,他包含了祭祀的空間甚至包含了與觀者互動的空間。
在戲曲演出中,觀者在一定意義上也參與了這場戲劇的演出。此時,“觀者”與“演著”雖然有了相對明確的劃分,但是在某一時刻,“觀者”確實扮演了“演者”的角色,對觀演關系的界定相較于后來的元雜劇,明清傳奇等似乎也是相對模糊的。演出的劇目同之前的祭祀儀式相呼應,其實其娛神性依然存在,只是同供盞儀式中的演出相比,娛神性已經大大減弱了。
隊戲在戲曲的發展史中有著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它使祭祀儀式中“觀”和“演”的關系進一步分化,使原本僅娛神的祭祀儀式演變為戲劇性表演,戲劇的“娛人性”超過了“娛神性”,而正隊戲的留存下來的劇目逐漸演化出元雜劇,可以說正對戲是宋元雜劇以及明清傳奇發生的前提,戲劇通過正隊戲逐漸走向成熟。
隨著時間的推進,戲曲的演變,供盞后的戲劇形態也從正對戲逐漸走向了宋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如果說在正對戲的演出中,有時“觀者”同時承擔著“演者”的角色,是戲劇演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在宋元雜劇和明清傳奇的舞臺演出中,“觀者”和“演者”已不能夠互換身份,觀演關系也得到進一步的分化,戲劇演出的舞臺固定下來。
從現存的古代戲臺來看,大量元明清的戲臺建筑同廟臺建筑的中軸線兩側出現了專門為觀者提供的看臺、看亭或看樓。無論是觀,還是演,位置已經固定,戲臺同正殿、獻臺、看樓有了固定的方位和規制,這是戲劇走向成熟的標志,戲劇在此時有了完整的演出空間形態。戲曲的娛神性大大減弱,娛人性逐步增強,“觀者”同“演者”的身份已經完全分化。
三、結語
戲曲發展的軌跡,始終遵循著娛神性的減弱與娛人性的增強,戲曲的發生其實便是表演形式逐漸從宗教祭祀活動的“束縛”中擺脫出來,由“神壇祭祀”演變至“世俗歌場”,“觀”“演”之間逐漸明確分化的過程。在分化的過程中,“演者”逐步依照人們的審美需求,心理需求,市場需求使戲曲的娛樂性,審美特征逐漸增強,更具有戲劇性,其故事更加生動,戲衣更加華麗,戲曲的舞臺演出更加程式化,戲曲的曲牌更加明確化,戲曲在這一過程中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并隨著時間與空間的流動逐漸演變為各類劇種。
注釋:
①榮世城.戲曲人類學初探[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②馮俊杰.戲劇與考古[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③榮世城.戲曲人類學初探[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④榮世城.戲曲人類學初探[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