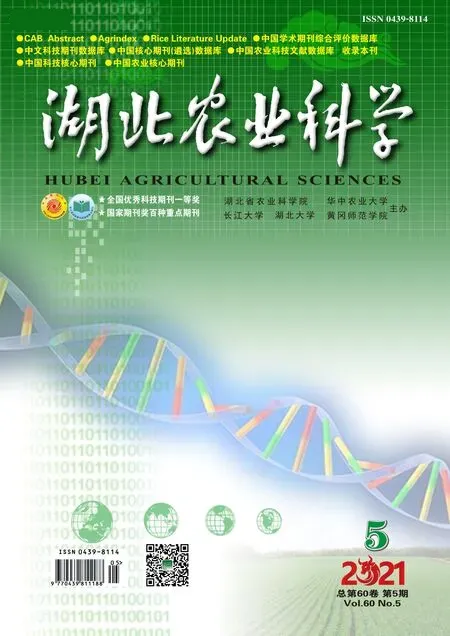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馮 佳,馮文勇,,石 磊
(1.山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2.忻州師范學院旅游管理系,山西 忻州 034000)
傳統村落又稱古村落,是指形成于農耕文明時期的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較豐富的文化、自然資源和較高的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經濟和社會價值[1,2]。傳統村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歷史文化的載體,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城市擴張、工業發展和人口集中,過去的10 年,國內總共消失了90 萬個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80~100 個村落[3],傳統村落正在逐漸消亡。為了保護傳統村落,2012 年起,住房城鄉建設部、文化部、財政部先后公布了五批國家級傳統村落,共計6 819 個。目前學者們對傳統村落研究成果豐富,主要集中在開發與保護[4-6]、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7-10]和文化景觀構建[11-13]等方面,特別在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著重探討了空間分布特征[14,15]和時空演化特征[16,17]等內容,研究方法以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為主,研究尺度包括宏觀和微觀。通過分析,發現宏觀研究尺度難以對微觀區域進行分析,微觀研究尺度不能從整體上反映空間分布特征,探討影響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的因素大多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鑒于此,本研究嘗試突破傳統研究尺度的束縛,從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尺度,運用ArcGIS 10.0、Google earth 5.2、SPSS 20.0 軟件對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山西省傳統村落的合理開發和保護提供借鑒。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傳統村落數量來源于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和財政部于2012—2019 年期間公布出來的五批傳統村落名錄,總計550 個;傳統村落空間分布圖主要是運用Google earth 5.2 軟件對550 處傳統村落進行坐標定位,運用ArcGIS 10.0 軟件將標定好的點疊加在山西省地形、水文、交通圖上制成;傳統村落的海拔、距河流的距離、距道路的距離數據來源于Google earth 5.2 軟件測量;DEM 高程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2018 年山西省各縣(市)交通、人口、社會經濟等相關數據來源于山西省2019 年統計年鑒。
1.2 研究方法
以ArcGIS 10.0、Google Earth 5.2 和SPSS 20.0 軟件為分析工具,運用疊加分析、最近鄰分析、核密度分析、空間自相關、相關分析法(表1)對山西省550個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2 空間分布特征
2.1 空間分布形態
運用Google earth 5.2 軟件,將山西省550 個傳統村落抽象為點狀要素并標記,根據最鄰近分析,運用ArsGIS 10.0 軟件中的空間分析工具計算山西省傳統村落的最鄰近指數,得到結果平均觀測距離5 730.466 8 m,預期平均距離9 775.113 2 m,R=0.586,由于0.586<1,表明山西省傳統村落趨于凝聚分布。

表1 研究方法及地理學釋義
2.2 空間分布密度
運 用ArsGIS 10.0 和Google earth 5.2 軟 件,將550 個傳統村落位置與山西省行政地圖疊加,使用Spatial Analyst 工具中的密度分析對其進行核密度計算,經過多次反復試驗,本研究選取帶寬h=50 km,繪制成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核密度圖(圖1)。總體上看,傳統村落主要分布在山西省中部和南部地區,北部地區分布較為稀疏且分散,南北差異明顯。傳統村落呈現出明顯的集聚分布,一個極核帶和3 個塊狀集聚區。根據山西省自然地理環境特征,將“一帶三區”的空間格局細化為太行-王屋山極核帶、汾河中游集聚區、桃河-松溪河集聚區和黃河-湫水河-三川河集聚區。

圖1 山西省傳統村落核密度分布
2.3 空間自相關性
山西省傳統村落的全局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olan’s I 指數0.216 844,預期指數-0.006 098,方差0.002 374,z 得分4.575 706,P 值0.000 005。估計值為正,接近于1,且z 值為4.575 706,通過顯著性檢驗,隨機產生此聚類模式的可能性小于1%,表明山西省傳統村落分布較多或較少的區域均呈現出一定的集聚特征。
全局Moran’s I 只能反映山西省傳統村落整體分布特征,無法直觀呈現出縣級區域內部的空間分布差異。本研究利用局部Moran’s I 指數進行山西省縣級傳統村落高值聚類探索及熱冷點分析。通過AcrGIS 10.0 中Anselin Local Moran’s I 可 得 聚 類 分布圖(圖2a)。從圖2a 可得出,山西省傳統村落縣級層面只呈現出明顯的高高聚集區域,主要集中在晉城市澤州縣、沁水縣、陽城縣、陵川縣、高平市,長治市上黨區及陽泉市平定縣。低低集聚是晉城市城區,其他區域聚類特征不明顯。
聚類分析結果不明顯,為了確定山西省熱點與冷點區集聚分布特征,利用ArcGIS 10.4中局部Getis-Ord Gi 分析得到冷熱點聚類分布圖(圖2b),圖2b 中山西省傳統村落冷熱點分布差異顯著,“南熱北冷”。從空間分布格局來看,山西省傳統村落的熱點區主要分布在晉城市全域、長治市南部及臨汾市、運城市西部以及陽泉市境內、晉中市西部和呂梁市東部交界處;次熱點區分布在臨汾市中部、晉中市東部及南部、呂梁市西部縣域內;冷點區及次冷點區分布在運城市、臨汾市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大部分區域。這與核密度分析的結果相似,山西省中部及東南部是傳統村落分布的集中區。

圖2 山西省傳統村落局部Moran’s I聚類分布(a)、冷熱點分布(b)
2.4 區域分布差異
山西傳統村落分布格局為中南部多,北部少。盡管中南部在整體上分布集中,但是內部也有明顯的空間差異。山西省各市因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歷史沿革、人文因素等存在差異,傳統村落分布數量也大相徑庭。就市域而言,晉城市傳統村落的數量最多,共有165 個,占全省傳統村落的30%;晉中市、長治市、呂梁市、臨汾市、陽泉市分布也較為明顯,分別占傳統村落數量的14.0%、12.7%、12.2%、8.5%、8.2%,這6 個城市的傳統村落占據山西省的85.6%;其余城市傳統村落分布較少,以太原為最,僅分布4個傳統村落。圖3 為傳統村落市域分布具體情況。
3 影響因素分析
3.1 地形因素

圖3 山西省傳統村落市域范圍數量分布
地形地貌作為一種基本的地理要素,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傳統村落的選址布局,是建村選址的基礎。運用ArcGIS 10.0 和Google earth 5.2 軟件,采用疊加分析的方法,將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圖與地形圖疊加(圖4),并運用Google earth 5.2 軟件測算出每一個傳統村落的海拔信息,探討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與地形及高程的關系。宏觀層面上,傳統村落空間分布以山脈為主要框架,自東向西依次在太行山脈、王屋山、太岳山及呂梁山脈山間海拔較低的低山、丘陵、河間谷地集中分布。微觀層面上,海拔小于500 m 的村落共有23 個;500~1 000 m,海拔每升高100 m,村落平均增加80個;1 000~1 500 m,海拔每升高100 m,村落平均增加29 個;1 500 m 以上,平均每100 m增加1.6個傳統村落。隨著村落海拔的升高,村落增加的數量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在1 500 m 以上的傳統村落僅有8 個,占總村落的1.5%。傳統村落更多地分布在海拔相對較低點,呈現顯著的低地性指向。

圖4 山西省傳統村落地形高程分布
山西省位于中國第二大階梯上,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分,地貌類型復雜,80%以上為山地、丘陵,眾多山間盆地相間分布。這樣封閉的地理環境本身就為傳統村落傳承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環境獨立,受外界的影響較小,能夠在朝代更迭、社會動亂的環境中安居,即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地形對村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傳統村落傾向分布于丘陵、山間河谷地帶,海拔在1 500 m 以下的傳統村落占比98.5%,這一方面是因為該區域地勢相對低平,有利于農耕,另一方面也因為海拔較低的區域水熱組合較好,有利于農業的發展,進而通過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影響到村落的空間分布。
3.2 水文因素
人逐水草而居,城依河道而建,中國古代先賢在聚落選址方面早就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風水觀。探討水文因素也采取疊加分析法,并運用Google earth 5.2軟件,測算出每一個傳統村落距河流的距離(圖5)。宏觀層面上,傳統村落大體沿河流兩側分布,黃河水系的傳統村落數量明顯多于海河水系,主要集中在黃河及其支流汾河和沁河流域,占全省村落數量的65%。微觀層面上,距河流1 km 范圍內的傳統村落有152 個,占傳統村落的28%,距河流1~10 km 范圍內,傳統村落距河流的距離每增加1 km,傳統村落平均增加33 個,距河流大于10 km,傳統村落距河流的距離每增加1 km,傳統村落平均增加10 個。隨著距離的增加,傳統村落增加的數量減少,也就是說距離河流越遠,傳統村落分布得越少。河流對山西省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有著巨大的限制作用,傳統村落趨向河流附近分布,呈現出近水指向。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大城重鎮無一不是位于大江大河兩畔,村落選址依然遵循。河流不僅是能夠為村落提供必要的生產生活用水,也是維持人類生存的必要資源,尤其在山西省這種黃土高原溝壑區,河流作為交通的意義和作用格外突顯。

圖5 山西省傳統村落水文分布
3.3 交通因素
道路是村落、城鎮之間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溝通的物質載體,尤其是對外交通是村落城鎮形成、發展的重要條件,對村落的選址及其格局影響深遠。本研究選擇干線即國道、省道和高速公路為測量標準,得到傳統村落道路分布圖(圖6)。宏觀層面上,傳統村落大多沿道路分布,微觀層面上距離國道或省道等5 km 的區域范圍傳統村落有438 個,占傳統村落數量的79.6%;距離大于10 km,傳統村落的數量僅有16 個,占傳統村落數量的2.9%。隨著距離的增加,傳統村落分布的數量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傳統村落沿路分布特征明顯。在交通表征中傳統村落大部分分布在道路附近10 km 范圍內,交通距離的可達性是傳統村落形成演化以及保護的基礎,交通相對便捷,溝通方便,為保護傳統村落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圖6 山西省傳統村落交通分布
3.4 人口因素
本研究通過在山西省統計年鑒獲取2018 年各縣(市)人口數據,運用SPSS 20.0 軟件中的相關分析法,探討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與人口的關系。結果發現,傳統村落集中分布的地區,人口數量并不突出;傳統村落數量和人口密度之間二者相關系數R=0.011,其相關性并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人口作為村落形成的必要條件,在村落最初產生的過程中處于重要地位,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口向城市聚集,村落空心化嚴重。通過以上分析,表明人口不是影響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并非是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傳統村落越集中。
3.5 社會經濟因素
本研究通過在山西省統計年鑒獲取2018 年各縣城鎮化率、地區生產總值,運用SPSS 20.0 軟件中的相關分析法,探討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特征與城鎮化和社會經濟的關系,結果發現(表2),傳統村落數量和各縣城鎮化率二者的相關系數R=-0.073,相關性不顯著;傳統村落分布在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傳統村落分布較多的縣,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在山西省各縣總排名較靠前,傳統村落數量與各縣地區生產總值二者相關系數R=0.269,在0.01 水平上顯著相關。這主要是由于較好的經濟基礎又使這些地區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為傳統村落的保護、修繕和發展提供物質條件。

表2 傳統村落分布數量與人口、城鎮化率、地區生產總值相關系數
3.6 政策因素
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傾斜是傳統村落保護工作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本研究在山西省11 個市人民政府網站以及住房與建設局官網中,以“傳統村落”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經過篩選和整理得到各個市有關傳統村落內容出現的頻次。表3 顯示,傳統村落出現頻次與分布數量大體上呈正比例關系,傳統村落出現頻次越多,表明政府對傳統村落的重視,當地分布的傳統村落也就越多。表3 所示除太原市外,其余各市基本符合上述推論,其原因是太原作為山西省的省會,國家下達的各種文件先經過省里而后再向各市傳達,所以在搜索頻次中太原市最多。陽泉、晉城、晉中、呂梁“傳統村落”出現頻次較高,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地方政府要比其他地方政府更為關注傳統村落,并且在采取各種措施進行保護,因此大部分村落都符合國家級傳統村落選取標準。在這一點上,政府的政策對傳統村落分布的影響可謂之大。

表3 山西省各地級市人民政府網站出現傳統村落頻次
4 小結
本研究運用ArcGIS 10.0、Google earth 5.2、SPSS 20.0 軟件,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相結合的視角,探討山西省傳統村落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①最鄰近指數R=0.586<1,表明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為凝聚型分布;②運用ArcGIS 10.0 軟件對傳統村落進行核密度分析,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呈“一帶三區”的空間格局,分別是太行-王屋山極核帶,汾河中游集聚區,桃河-松溪河集聚區和黃河-湫水河-三川河集聚區;③山西省傳統村落的全局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山西省傳統村落分布較多或較少的區域均呈現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且熱點分布差異顯著,“南熱北冷”。④山西省傳統村落空間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交通、社會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人口因素對其影響效果不顯著,社會經濟因素中,地區經濟條件與傳統村落數量相關性顯著,經濟發展與保護傳統村落并不沖突,甚至是保護傳統村落必要的經濟基礎。
傳統村落數據來源于國家公布五批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受到傳統村落評選條件限制,山西省還有較多傳統村落未能入選,這也是本研究中數據的局限性。同時影響傳統村落分布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未考慮到坡度坡向、歷史文化等因素對傳統村落布局的影響。山西省歷史悠久,文化特色鮮明,如何在保護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山西省各地區傳統村落的文化內涵,將傳統村落開發融入到山西省全域旅游的建設中,加強文旅融合,將是下一階段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