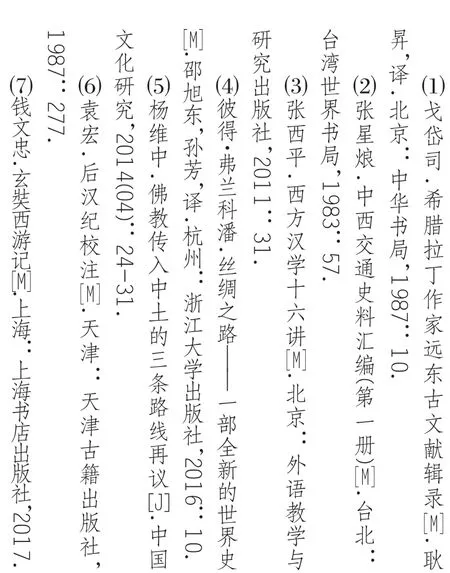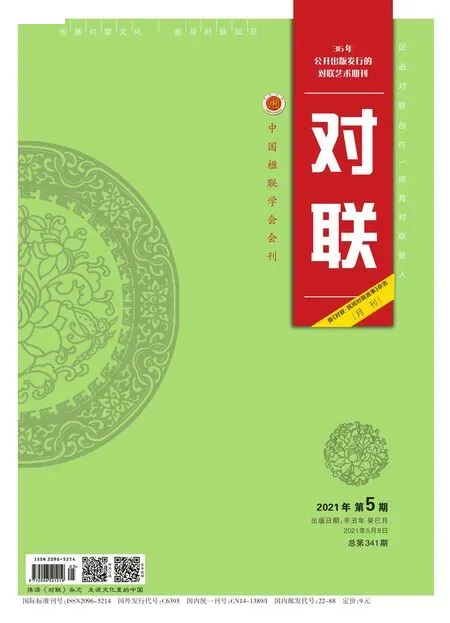《西游記》的絲路情緣探究
□趙春菊
文學是文化的最好記載,文學的傳播促成了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精神交流,為人類的合作與發展鋪就道路。《西游記》作為充滿異域風情的神話游歷故事,從其故事藍本中便可知其與絲綢之路的不解之緣。以《西游記》為文本窺探絲路上曾經發生過的文化交流,再合適不過。
一、『絲綢之路』于中國之意義
古希臘時期,西方人把中國稱為『塞里斯』(Seres),并記載了中國人使用蠶絲的情況,『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后再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和織布兩道工序』。一百多年后,希臘史學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臘游記》(The Description ofGreece)中提到絲不產生于樹木,而是產生于一種蟲子,但卻誤把蠶認為是蜘蛛之類的蟲子。此書譯者張星烺認為,『塞兒』的讀音與『蠶』相近,加上希臘語及之后拉丁語的尾音『斯』,就產生了『塞爾斯』這個對中國人的稱謂。由此可見,西方對中國的最初認識與絲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絲綢精美,其對于西方世界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當亞歷山大統一希臘、橫掃中東、攻占波斯、開進印度河流域之后,絲綢通過中亞及波斯進入羅馬。作為東方標志的『絲綢』成為媒介,打通了東西方的阻隔,此后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的崛起都對這條東西交流的通道起到了擴展鞏固的作用,將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張騫出使西域的重要影響恰恰在于溝通了漢夷文化,使中原文明迅速向四周傳播,也是中國主動認識世界、融入世界的歷史開端。
二、《西游記》與絲路的前世血緣
⒈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以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為標志
西域,在中國歷史版圖中被用來指稱今玉門關以西地區。『玉門關』被認為古代中國的西陲邊界。在漢代,它與『陽關』南北呼應,是漢王朝防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關隘,一句『西出陽關無故人』便可感知古人對西域異族風情的遙遠遐想。
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春秋戰國后期形成很多奴隸制小國,楚漢戰爭時期在冒頓單于的武力擴張下形成了統一的匈奴帝國。西漢立朝之初便受到匈奴的威脅。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漢武帝聽到了有關大月氏的傳言,急切想要得到居住在西域的民族的支持,聯合夾擊匈奴,以破匈奴之勢,于是才有了公元前一三九年和公元前一一九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可以說戰略上對西域的向往,促成了絲綢之路的開辟,也打通了古代中原地區與中亞的聯系。
⒉《西游記》的產生以唐代玄奘西游取經為故事藍本
絲綢之路這條連接中亞與東亞的交通要道不僅是商人們貿易往來的必經之路,也是思想交流的極佳通道。東西文化西傳東進、相互交織,開啟了東西文明交流的高級階段。對于中國來說,最為顯見的當屬東漢時期佛教的東傳。
佛教起源于印度。對于其傳入我國的路徑,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古籍記載較多的當屬『北傳』一路,即經由西域絲綢之路進入中國。隨著佛教的東傳,中國歷史上迎來了第一次翻譯高潮,即東漢末年的佛經翻譯。
到了唐代,由于當權者自認為是道家老子李耳后人,因此『揚道抑佛』,但佛教在中國已傳播甚廣,長安城里常見天竺高僧設壇講經,玄奘即是由此而對作為佛教圣地的印度心生向往,執意西去取經的。于是唐貞觀元年(六二七年),為探究佛教各派學說分歧,玄奘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六四三年啟程回國,六四五年回到長安,前后歷經二十余年。可以說,對西域的向往促成了玄奘的西游天竺,也為后世留下了無限言說的西游故事。
三、《西游記》對絲路的言說
玄奘西游回到長安,奉詔口述所見所聞,由門徒辨機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述他西游經歷國家的山川、物產、習俗等。《西游記》以此歷史事件改編而成,其成書經歷了一個長期演化的過程。后世弟子對其功德的贊美與神化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穿插了一些離奇故事,后又經唐末筆記、北宋話本、元雜劇等跨文本改編,形成了師徒四人取經的故事雛形。現存最早的刊本是萬歷二十年(一五九二)的二十卷百回本——世德堂本《西游記》,后世所看到的《西游記》成書大多在此基礎上修改而來。
玄奘西游與絲綢之路有著不解之緣,由此而來的《西游記》也從不同的角度言說著這條東西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的繁榮之路。
首先,《西游記》中刻畫的玄奘西游路線與古絲綢之路路線基本相符。
絲綢之路分為陸上和海上兩條,前者指中國與中亞、西亞各民族,以及希臘、羅馬等國的交通路線;后者指與東亞、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地區各國之間的交通路線。從貿易角度看,前者主要以販運絲綢為主;后者主要以販運瓷器、香料為主。兩條絲綢之路通過貿易促進了東西方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藝術等的交往。
玄奘西行從長安出發到達甘肅境內,然后通過蘭州、涼州等地達到玉門關,之后出唐朝邊境向西北而行進入沙漠,走到今天天山南麓,之后向西北跋涉,進入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之后翻越帕米爾高原,達到佛教圣地印度。從路線可見,玄奘先取道陸路絲綢之路,之后踏上南亞海上絲綢之路。在《西游記》敘事中,唐僧師徒出唐朝疆域后,一路向西,書中描寫經歷的西涼國,據考即在今甘肅省境內;之后的火焰山,則位于新疆吐魯番境內;之后的比丘國,地處吐魯番西面的樂陵川;之后的滅法國,從師徒幾人喬裝打扮的衣裝來看,已然是古波斯人之穿著;最后到達天竺國,則是印度。可知,《西游記》雖是作者根據《大唐西域記》杜撰而來,但所描繪路線走向大致與歷史相同,是古絲綢之路在文學中的直接體現。
其次,《西游記》中對絲綢的描寫甚多。
古絲綢之路以『絲綢』命名,其貿易往來雖非僅限于絲綢,但卻以絲綢最為著名。《西游記》中多有對絲綢的描寫,比如第四十六回中,師徒四人在車遲國與道士國師斗法,隔板猜物,車遲國王一句『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緞絹綾羅,那有此甚么流丟』一語道出當時的四種絲綢品種;再如第九十回,為答謝孫悟空、豬悟能和沙悟凈救難之恩,『(玉華州)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匹,與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領受,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可見當時絲綢之精美、貴重。
四、結語
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南亞佛教的傳入,南亞佛教在唐朝的流行與玄奘西游具有密切的聯系,玄奘西游的路線沿著絲綢之路行進。可以說,玄奘西游因絲路而起,沿絲路而行,促進了絲路沿線民族和地區的文化交流。《西游記》以玄奘西游為故事藍本,是對那段歷史的演繹描述,故事中多有對絲綢之路的展現,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結晶與見證。《西游記》作為一部體現絲路文化的文學作品,它的誕生促進了絲路文化的交流,《西游記》在東南亞很多國家與地區被多渠道翻譯、傳播、改編等,成為新時代絲路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