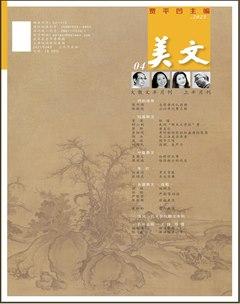土中炒豆君曾見?
張同武

“二月二,龍?zhí)ь^,家家戶戶炒豆豆。玉米豆,開金花,迎來祥龍下雨啦。面豆豆,土中炒,咬掉蟲蟲春耕早。”一首民謠道出了關(guān)中農(nóng)村過“二月二”的民俗,當(dāng)然,除過玉米豆和面豆豆,還有其他的豆類,但玉米豆和面豆豆是其中兩個(gè)比較有意趣的。
關(guān)于炒玉米豆,有一個(gè)美好的傳說,有一年開春時(shí)分,天公不作美,多日無雨,土地干涸,農(nóng)人苦焦。有一個(gè)好心的玉龍,偷偷給人間下了一場(chǎng)春雨,解了百姓燃眉之急。王母娘娘知道后大怒,把玉龍壓在了山下并放出狠話,除非金豆開花,否則永世不放。感念玉龍對(duì)人間的恩澤,聰明的農(nóng)人想出了炒玉米豆的辦法,讓金燦燦的玉米豆開出了金花,玉龍得救。
而炒面豆豆則是陜西渭南一帶的獨(dú)特的風(fēng)俗,也即把面團(tuán)做成豆子的形狀炒熟。炒面豆豆的面是要經(jīng)過發(fā)酵的,和蒸饅頭用的面一樣。但要在和面時(shí)加入鹽、花椒葉、小茴香等作料。先把大塊的面團(tuán)搓成指頭粗細(xì)的長條,再用刀剁成小塊,用手稍微揉搓一下,以使面團(tuán)圓潤。這些過程平淡無奇,有趣獨(dú)特的是炒制的過程,相信這個(gè)炒制的方法大部分的人沒有聽說過:在鐵鍋里放入土,然后加熱,再將制好的面團(tuán)放入翻炒,以至炒熟!
前面賣了個(gè)關(guān)子:土中炙炒。其中的原理想來很簡(jiǎn)單,鐵鍋導(dǎo)熱快,溫度高,即使文火,也難免會(huì)將面團(tuán)炒糊,或者是外焦里生。若放入油,那就有炸制或煎制的嫌疑。而在鐵鍋里放入土,則在鐵鍋和面團(tuán)中間加了一層介質(zhì),土的導(dǎo)熱性差,升溫慢,可使面團(tuán)逐步受熱,由表及里,外焦里嫩,掌握好火候,便可炒制出香爨脆酥的面豆豆。
這土,稱之為白土。和如今用作化工原料的工業(yè)產(chǎn)品白土是兩回事。說是白土,其實(shí)還是黃土,只是土的顏色已經(jīng)近乎白色。那么,什么樣的土能現(xiàn)出白色來?那只有找飽經(jīng)風(fēng)礪、未被污染、不生植物的土質(zhì)。哪里會(huì)有?這就是農(nóng)人的智慧,他們會(huì)在溝沿、崖畔、土窯找到這樣的土,挖回家來,找一個(gè)干凈的所在,儲(chǔ)存起來。因?yàn)檫@樣的土水分已經(jīng)揮發(fā)殆盡,雜質(zhì)也幾盡蕩然,細(xì)密、干爽、柔軟、潔凈,用作炒制食物的介質(zhì),不知道要比細(xì)沙好多少倍,如果再算上土的清香,簡(jiǎn)直就是極品了。白土也曾經(jīng)被農(nóng)人們用作粉刷房子的涂料,很環(huán)保、很綠色。
不知道是誰先有了這樣的發(fā)現(xiàn)或者說是創(chuàng)舉,抑或是先民們烹制食物辦法的繼承,總之這樣的辦法在渭南一帶過去是被廣為使用的,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比這更好的辦法,所以說這是一個(gè)偉大的創(chuàng)舉也毫不為過。
記得在過去,家中的主婦們?cè)诔疵娑苟箷r(shí),一定要在頭上包塊頭巾,畢竟會(huì)“土花”四濺,不可避免地會(huì)將主婦們變成個(gè)土人。雖然炒熟的面豆豆已經(jīng)不太沾土了,但無論如何會(huì)有些殘留。主婦們會(huì)用笊籬從土中把面豆豆撈出來,放在篩子里再篩一篩,還要用干凈的抹布擦一遍,才能成為入口的上好的小吃。曾經(jīng)有一個(gè)客居外鄉(xiāng)的長輩把面豆豆從家鄉(xiāng)帶到遙遠(yuǎn)的新疆,吃著香爨脆酥的面豆豆,鄰居詢問制作的辦法,這位幽默的長輩玩笑說,地里生長的,你看上面還有點(diǎn)土!
這種用土炒熟的面豆豆不獨(dú)香爨可口,養(yǎng)胃和中,而且經(jīng)久耐放,放在家里可以用作點(diǎn)心或零嘴,帶上旅途則是上好的干糧。記得改革開放之初,陜西的一位農(nóng)民企業(yè)家應(yīng)邀出訪,回來后在報(bào)告會(huì)上為飲食的不習(xí)慣大倒苦水,并再三提到自己帶出去的面豆豆成為一行人爭(zhēng)相享用的佳肴。小小的面豆豆早早地也有了飄洋過海的經(jīng)歷。
如今,快速發(fā)展的農(nóng)村已經(jīng)很難看到古代土城墻的蹤影了,甚至連土墻都很少見了,哪里去尋覓那一捧白土。
但面豆豆這種食品卻還在傳承,不過已經(jīng)是烤制或是炸制的了。
那么綠色的食品可能就此消失了,那么一種原始而又科學(xué)的炒制辦法失傳了,雖然我們失去了一點(diǎn)口福,但發(fā)展是主流,社會(huì)總歸在進(jìn)步著。
(責(zé)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