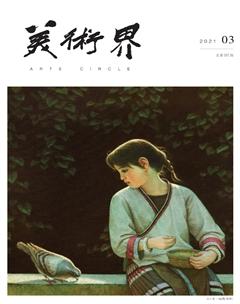中國畫和世界的關系

有一年,我和幾個朋友在大英博物館參觀,接近中午時大家回到大廳找地方休息,手里都拿著一小紙杯的熱咖啡,找了個靠近古埃及展廳南出口的地方,坐下聊天。
大廳里的人很多,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熙熙攘攘,買畫冊的、買小吃的、買飲品的,人來人往,非常熱鬧。能感覺得到這里聚滿了世界各地的人。的確,我們來英國也是奔著看美術館的,前天去了新泰特,昨天去了白立方,今兒又來看大英博物館。
這幾天馬不停蹄地跑,有點人困馬乏的感覺,一種疲態表露在每個人身上,坐那兒都像癱坐一樣沒有精神。看著他們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冒出一句:“假如我們用‘筆墨這個內容在這兒開個研討會你們覺得怎么樣?就講筆墨問題。”話一出口就覺得有點突兀,心里也愣了一下。在一個外國的博物館,周圍都是外國人,男女老少,黑人白人,聲音震得天響。把我們的寶貝“筆墨”拿出來放在這里面,也不對呀!更何況走進門去就是古埃及人身獅面相和東邊的古希臘神殿的碩大石雕,震撼無比。更為關鍵的是“筆墨”雖說是一個詞,但在這個場域就如同真“筆墨”出現一樣毫無遮掩……突然覺得很另類,對接不上。
還好,大家聽后并沒有什么反映,只是直楞楞地盯著我看了一下,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就這樣過去了。但是,雖然是一句笑談,可當說出這句話之后我的感受卻是“奇異無比”,就好像自己和“世界”做了一次學術交流一樣,驚得我五味雜陳……
這個記憶非常深刻。
“讓中國畫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和世界接軌與世界對話”。這些針對中國畫的喊話喊了許多年。在潛意識里已經成了某種心結。近年來又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說法,這么一折騰,越發覺得我們和世界的距離如同兩個區域的人,另一撥人總是時不時策劃著何時超越他或者干掉他。
實際上,我們自己劃了一條與世界之間的區分線。用這條線說明我們是中國、他們是世界(這里指的是中國畫)。試想一下,世界各國的畫家在創作時不考慮藝術標準而是總想著用什么樣的“畫法”達到那個所謂的“世界語言”,還要震驚世界,你不覺得可笑嗎……
什么是世界?是由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的世界,同樣,關于文化的藝術的也是由這些國家的貢獻所構成的,包括我們自己。所以說,中國也是世界,你我也是世界。我們的作品都是世界人類的財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可以獨自稱為世界。
其實,繪畫里根本沒有什么世界風格和世界語言之類的標準供人膜拜。如果說有那也是對某個藝術家或者某個時期的作品。說白了,世界性的語言或者讓世界讀得懂的語言不是什么世界級的圖畫,尤其對于當代文化藝術來說,而是相同的價值觀,共同關心的問題和在現代文明中畫家應該充當的角色。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繪畫也只能是“我們”和“世界”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