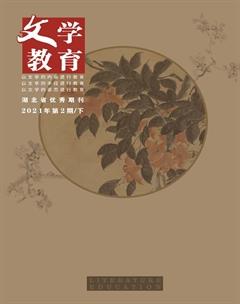《騎桶者》的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解讀
鄧羽夢
內容摘要:《騎桶者》是高中語文選修教材中的一篇經典課文。敘述者運用限知視角的藝術手法提供眾多看似“不可靠”的信息,同時通過回憶敘事對敘述時序進行有效的控制,給本文的虛構帶來合理的解釋或掩蓋。其中反映社會現狀的環境描寫、荒誕變形的故事情節以及無法正常溝通的人物對話,都真實而細致地反映了敘事者作為一個底層勞動者卑微、無助的形象。敘述者在自己復雜的內心獨白、不完整敘述以及似是而非、或虛或實的邏輯情節中穿插的價值評判,向讀者傳遞了與眾不同的文本主題意義。
關鍵詞:《騎桶者》 敘事藝術 人物形象 價值評判
《騎桶者》是人教版高中語文選修教材《外國小說鑒賞》中第八單元的第一篇課文,本單元的話題是“虛構”。《騎桶者》是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運用虛構、象征直覺的手法敘寫變形荒誕的形象,講述了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在天寒地凍、走投無路之時騎著煤桶去討煤,卻被煤店老板娘用圍裙輕輕地扇到了冰山區域,從此隔絕于人世的故事。本文將從“騎桶者”的敘事藝術、人物對話和作者寫作意圖的價值評判幾個方面對文本進行深入解讀,探討其教學價值。
一.對“騎桶者”敘述藝術解讀
(一)敘述視角:限知視角
《騎桶者》的敘事視角很明顯是屬于“限知視角”,運用第一人稱敘事。文中出現的人物有講述故事的主人公“騎桶者”,煤店老板以及把“騎桶者”用圍裙扇走的煤店老板娘。從小說的敘述技巧來看,作者巧妙地將“限知視角”分為了兩個部分來講述:首先文本開頭是“騎桶者”的內心獨白,故事發生于火爐里透出寒氣的冬季,嚴酷的周圍環境,“我”的遭遇:“空空的煤桶”,“冷酷的火爐”,“冷酷的天空”,“我像個乞丐,奄奄一息”。在這種物質極度匱乏的境遇下,主人公不僅通過“成功借到煤”的幻想來強化其遭遇的痛苦和對所需物質的渴望,還通過將幻想做鋪墊,使其與下文中“被老板娘用圍裙扇走”的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內心獨白式的自我描述更容易激起讀者的同情心,進而達到使讀者與“騎桶者”深度共情的目的,此時讀者完全有理由相信“騎桶者”所描述的一切都是真的。
第二部分從小說第三段開始,作者轉換了內心獨白式的敘述[3],利用與煤店老板和老板娘對話的方式來敘事,通過老板和老板娘的語言、行為、神態描寫來達到目的。“我”騎著煤桶漂浮在地窖門口的空中,對著地窖里面的老板祈求道:“求你給我一點煤吧”,煤店老板轉過頭問老板娘:“我沒有聽錯吧?是一位顧客。”,然而老板娘卻一面編織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著火爐取暖平靜的說:“我什么也沒有聽見”。這里的對老板娘“平靜”和“舒服”的描述,是“我”根據自己的觀察所得到的對老板娘心情、狀態的主觀判斷。接著,老板固執的相信確實是有人在門外,老板娘便只好出去求證,此時“騎桶者”說的是:她當然馬上看到了我。但這也是他單方面的認為,并沒有確切理由說明老板娘一定看到了漂浮在空中的“騎桶者”。最后,在“騎桶者”衷心的懇求老板娘的時候說:“錢我當然是要全數照付的,不過我不能馬上付,不能馬上”,但老板娘卻還是說什么都沒有聽見,并把圍裙接下來輕輕地把“我”扇走了。從倒數第三段的“她當然馬上看到了我”到最后一段“她什么也沒有看見,什么也沒有聽見”,可以看出故事情節的不合理之處。這一系列的情節都來自于“騎桶者”單方面的所見所聞所感,或許其中有很大成分的猜測、臆想,所有人都不得而知。
因此,運用“限知視角”的方式呈現從“騎桶者”本人立場出發的“借煤”故事,將讀者和敘事者的距離拉近,會使小說的敘述顯得真實親切。但這種敘事視角只能局限于敘述“騎桶者”的所見所聞所感,給讀者眾多看似“不可靠”的信息,進而使讀者對故事的情節邏輯“似信非信”,符合卡夫卡運用虛構、象征直覺手法的敘寫風格。
(二)敘事時間
敘事時間涉及“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兩個層面。作為故事敘述者的“我”,存在經歷這件事情中“過去的我”和回憶敘述這件事情的“現在的我”的區別。講故事的節奏是由“現在的我”來控制的,故事時間和敘述方法早就在作者的掌控之中,正如菲爾丁在《湯姆·瓊斯》中指出:一旦任何似乎尋常的場面露了頭,我們就不惜筆墨得將他盡量像我們的讀者展示。
準確地說,《騎桶者》的話語時間是在“我”賒煤不成之后,這一特定的時間決定了敘述者從故事敘述的開頭就已經是一個借煤的失敗者,但敘述者卻仍然煞有其事地娓娓道來,特別是對于選擇怎樣的方式去借煤以及所預想的“女主人把最后殘剩的咖啡倒給我;同樣,煤店老板雖說非常生氣,也將不得不把一鏟煤投進我的煤桶。”的美好結果,都顯得那么自然,一切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在與煤店老板娘對話的過程中,“騎桶者”不停用喊話的方式去乞求。讀者用“我”的眼光來注視借煤的經過,用“我”的獨白來共情感受無助的處境,用“我”的敘述來評判老板和老板娘的為人處世。
為了“騙”得讀者的同情,“騎桶者”不講那些對他不利的背景信息,只講能夠引起讀者同情的信息。他成功地騙過了讀者的雙眼,使讀者一直蒙在鼓里。這正是小說家對話語時間進行調控的一個常規現象:敘述者回溯過去,概述某一段時間中的主要事件,故事實際時間按照敘述者的意愿而撥動,從而使故事主要內容得以集中。這種敘述方式,可以使讀者通過人物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來觀察體驗,能夠更自然地直接感受人物細致、復雜的內心活動,從而帶給讀者真實感、親切感、場景感、參與感,具有先天優勢的對敘述時序進行有效的控制, 給本文的虛構帶來合理的解釋或掩蓋。
二.對“騎桶者”人物形象解讀
(一)從環境來看“騎桶者”現狀
作為小說三要素之一的環境描寫,不僅可以反映出事件發生的背景,還能透過環境細探人物的心理變化和性格特征。故事開篇介紹“煤全部燒光了;煤桶空了;煤鏟也沒有用了”,一切空空如也的感覺讓人突然走進了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經濟蕭條、人民窮困的社會,這是奧匈帝國那個缺煤的冬天的真實寫照。雖然煤燒光了,但求生的意念仍在;接下來的環境描寫,“火爐里透出寒氣,灌得滿屋冰涼。窗外的樹木呆立在嚴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銀灰色的盾牌,擋住向蒼天求助的人。”,這是借煤事件發生的背景和間接原因。“寒氣、滿屋冰涼、窗外的嚴霜、冷酷的火爐、冷酷的天空”等等字眼,不僅可以突出此時天氣極度寒冷,“我”除了去借煤以外別無他法,同時更是作者將自己苦難遭遇和無助心情外化的重要表現。天空是冷酷的,拒絕提供幫助,暗示了主人公最后的悲慘結局。看似是環境描寫,卻影射了當時的社會環境,然而即使在這樣貧乏的社會,也有極大的貧富懸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二)從情節來解讀“騎桶者”形象
1.借煤方式之怪
“騎桶者”為什么是騎著煤桶“飛”而不是提著煤桶“走”呢?首先是需要煤的緊迫性:煤全部燒光了,煤桶空了,煤鏟也沒有用了,就連本應供暖的的火爐也透著寒氣,“我”可不能活活被凍死,“我”必須快馬加鞭向煤店老板尋求幫助。由此可見,“騎桶者”雖然是一個物質極度匱乏者形象,但他并沒有聽天由命,怨天尤人,而是積極主動尋求幫助,渴望去走出困境。
第二,作者在第二段說道“我必須向他清楚地證明,我連一星半點煤屑都沒有了”,“我”決定此行前去的方式是騎著煤桶前去,煤桶已經空得飄起來了,這不就能證明,此時我對煤的匱乏已經到了極致了嗎?就算“我”騎在上面他也從未下降到齊房屋大門那么低,有什么能比一個煤桶漂浮在空中,更能證明它里面空空如也的呢?這一點可以看出,“騎桶者”是一個誠信且堅定的人,他愿意向老板堅定地證明自己沒有一星半點的煤,以此證明自己借煤的決心。
第三,煤老板對于我的通常的請求已經麻木不仁,因此“我”必須選擇非常獨特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去借煤。提著煤桶借煤是最普通的方式了,但是“我”現在已經就快瀕臨死亡了,因此,騎著煤桶去借煤更能引起老板的注意,或許他就會更快借煤給我。說明“騎桶者”很機智,很聰明,也很簡單,他其實潛意識更加愿意相信老板是會借煤給他的。通過上述情節可以看出“騎桶者”雖然物質極度匱乏,身份卑微底層,但他還是選擇誠信,真誠的對待每一個人。無論身處怎樣的境地,始終心系善意,心懷希望,心存美好。
2.借煤數量之少
“騎桶者”為何要去借煤呢?文中關于“騎桶者”內心獨白的描寫中,對借煤的原因做了充分的敘述,“煤全部燒光了;煤桶空了;煤鏟也沒有用了;我連一星半點煤屑都沒有了,我可不能活活凍死”,由此可知,這時的“騎桶者”存活的唯一可能就是借到煤,他是一個物質極度匱乏但內心的信念感很重的人,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活下去。
“騎桶者”為何借煤的數量如此之少呢?文中寫道“我”與老板和老板娘的對話,“煤店老板,求你給我一點煤吧”“我只要一鏟子煤;一鏟最次的煤也行。錢我當然是要全數照付的,”可見“我”作為一個物質極度匱乏者,對煤的質量已經不做任何要求了,一鏟子最次的煤也能讓“我”得到滿足,從“如數照付”這個詞可以看出“騎桶者”是這個店的常客,并且從不賒賬,在這個極度缺煤的時刻,他還是堅定的承諾會給錢。
通過上述情節可以看出,“騎桶者”是一個在生死邊緣徘徊,但始終知足的人,體現了在社會底層生活的物質極度匱乏者對活著的渴望和乞求的卑微,但始終保持內心的堅定信念的可貴品質。
3.“騎桶者”對老板娘的態度變化
“騎桶者”初次對老板娘的態度體現在老板不確定是不是門外有人在喊,于是想讓老板娘出去看看,此時“騎桶者”說:“是我啊;一個老主顧;向來守信用;只是眼下沒錢了”,誠懇表明自己的來歷,強調自己是一個向來守信用的老主顧,此時的態度的非常誠懇的。接著老板娘說街上沒有人,空蕩蕩的,這個時候“我”突然緊張了起來,借煤的心也變得急迫了起來,感覺希望慢慢在消失了。于是“我”開始喊道:“請你們抬頭看看,你們就會發現我的;我請求你們給我一鏟子煤;”,此時“我”的態度是謙卑、恭順、忐忑,對老板娘很謙卑,希望老板娘抬頭看看他,同時恭順得請求老板娘給一鏟子煤,并忐忑地希望得到回應。然而卻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萬般無奈之下“我”對老板娘喊道,“衷心地向你問好;我只要一鏟子煤;一鏟最次的煤也行。錢我當然是要全數照付的。”此時我的態度是低下、諂媚、可憐、無力,低下地懇求老板娘要一鏟最次的煤,諂媚地向老板娘問好,顯得多么可憐無力。得到的結果卻是老板娘把圍裙解了下來,并用圍裙把“我”我扇走,此時“我”的借煤希望已經完全破滅,我開始回頭對老板娘喊,“你這個壞女人!我求你給我一鏟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對老板娘的態度變成了氣惱、仇視、詛咒、決絕。
“騎桶者”對老板娘的態度變化過程清楚得顯現了性格上的分離,體現了在面對社會現狀時,即使竭盡全力、使出渾身解數也無力改變現狀的社會底層勞動者形象以及當時的悲慘現實。
三.價值評判及總結
通過《騎桶者》虛構、象征直覺的手法、巧妙地敘述藝術和荒誕的情節所體現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在敘述事件的同時,還穿插了一些價值評判。在作者描述的這個充滿矛盾、扭曲變形的虛擬世界里,一些底層勞動者在物質匱乏的惶恐,無助和不安的境遇中,勇敢的嘗試,始終保持內心的堅定信念和對活著的渴望。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無力改變的底層小人物的生存狀態,敘述者通過自己的不完整敘述以及似是而非、或虛或實的邏輯情節,表達了自己的真實內心,向讀者傳遞了文本的主題意義,擴充了閱讀的審美效果。
參考文獻
[1]外國小說欣賞[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2]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張正耀.變形了的信息——《騎桶者》的不可靠敘述藝術[J].中學語文教學,2016(04):43-47.
[4]華萊士.馬丁,著.當代敘事學[M],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5]亨利·菲爾丁,著.湯姆·瓊斯[M],張谷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作者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人文與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