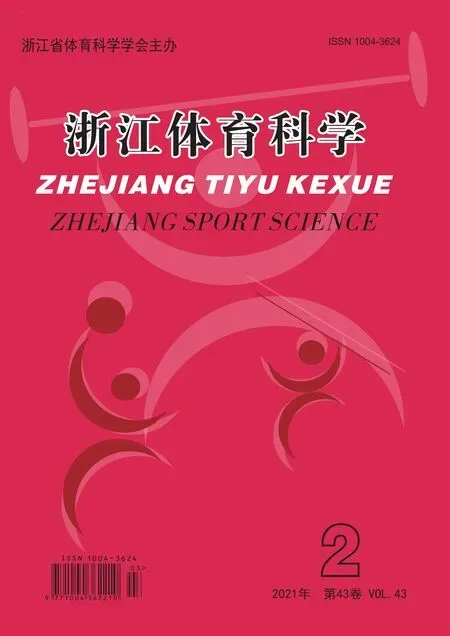媒介體育
——一種美學共同體
周雪蕾
(成都體育學院 新聞與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共同體”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最早引入共同體一詞。當前,共同體理論已成為西方后現代問題研究的重要視角。從共同體理論的歷史演變來看,西方共同體理論大致經歷了道德共同體、契約共同體和美學共同體三個階段。
所謂“美學共同體”,又稱“審美共同體”或“趣味共同體”(community of aesthetics, community of taste),是指在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所引起的大眾審美方式的延展與變異: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審美現象不但豐富多彩,而且本身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并以社會交往與道德實踐的形式實現出來。在此過程中,作為傳統社會之“共有利益”的倫理價值及其“道德共同體”訴求,逐漸被后現代社會的以審美價值為旨歸的共同體訴求所取代,而這種全新的“美學共同體”一旦走入現實,便與大眾的生存境況相合拍,并進一步成為大眾癡迷追求的個體體驗的理想境界[1]。
本文將從美學共同體的視域來考察現代社會的一種特殊媒介文化形態——媒介體育,探討美學共同體在其中的定位和意義。
1 美學共同體的意涵
工業社會把人從自然、原始的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現代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但過度強調個性化的個人主義時代造成了諸多社會問題,人們的目標感、認同感、歸屬感逐漸淡漠甚至消失,對話和交往趨向斷裂,傳統社會根基發生動搖。人們開始懷念過去的共同體,并期待重建共同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著名社會學家、當代西方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問題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之一齊格蒙特·鮑曼評估了共同體的歷史和現實,認為共同體是一個溫暖而舒適的場所,一個溫馨的“家”。共同體允諾了安全感,但同時也剝奪了我們的自由。在《共同體》一書里,齊格蒙特·鮑曼將美學共同體作為一種虛假的、替代的共同體加以描述,他認為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詳細闡述了美學與共同體的聯系。身份認同看起來與美共享著共同體的存在地位:像美一樣,除了廣泛的協定和一致(明確的或默示的,通過判斷的共識性的同意,或通過一致的行動表達出來)以外,它沒有其他基礎可以依據。就像美可以歸結為藝術體驗一樣,我們正在討論的共同體也是在這個體驗的“溫馨圈子”內產生并被消費的[2]。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共通感是鑒賞判斷的前提,有關審美共通感的學說告訴我們,在人類的審美生活中,有一個人類共同生活的層面,也就是有一個共同體(意即美學共同體或審美共同體)的基礎。“所以當我在這里把我的鑒賞判斷說成是共通感的判斷的一個例子,因而賦予它以示范性的有效性時,共通感就是一個理想的基準,在它的前提下,人們可以正當地使一個與之協調一致的判斷及在其中所表達出來的對一個客體的愉悅稱之為每一個人的規則”[3]。康德并沒有明確提出“美學共同體”這一概念,但《判斷力批判》開啟了一種審美政治的可能性,即美與人類的共同體生活有內在的關聯。這意味著藝術生活與人類的共同體生活,甚至與人類的政治生活有著內在的親緣性。后代的哲學家們確實藉此開始探討審美與共同體的問題,當然包括齊格蒙特·鮑曼。
社會學家施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中寫道:“我們的整體生活方式——從我們的共同體形態到教育組織和教育內容,從家庭結構到藝術和娛樂的地位——都深受民主和工業的發展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也深受傳播擴展的影響。”那些帶給人們確定性的共同體都遠去了,永恒的價值觀持續貶值,時尚價值觀漸成共識,作為傳統的、永恒共同體的代替品,美學共同體基于消費而非契約,時時處于一種脆弱的、易受傷害的狀態,永遠需要警戒、強化和防御,它無法擺脫反思、審美疲勞、質疑和爭論,它更像一份單方面的協議,每次更新續簽不能保證下一次的更新續簽,而且隨時可能被撕毀。它的成員甚至可以沒有任何理由就脫離而去。但是,美學共同體還是帶來了些許脆弱的片面的確定性……像一把救命稻草,美學共同體被大眾抓在手里,成為永恒共同體的代替品[4]。
美學共同體聚集的是尋求個人意義和身份認同的消費人群,是以偶像、品牌或事件為中心。對現代體育而言,媒介體育最鮮明地凸顯了美學共同體的特征。
2 媒介體育美學共同體的構成
溫納(Wenner)是較早提出“媒介體育”概念的一位學者,他認為該詞蘊含了多層次的意義。溫納將其區分為三種不同的研究層次及對象,分別是:機構、文本、閱聽人的體驗。在溫納(1998)看來:媒介體育的“機構”包括所有在全球傳播、娛樂以及休閑復合領域中所有重要的機構與角色,媒介體育復合領域帶來了具有支配地位的“后現代體驗”;媒介體育的“文本”則包括了種族、性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英雄主義等意識形態,彼此在體育的超現實世界中相互交錯漂浮;媒介體育的“閱聽人”則能體驗到屬于體育舞臺上的儀式化暴力對社會關系與家庭生活的深刻影響,尤其當體育進入網絡空間時,媒體閱聽人則必須更進一步與體育迷及其高強度的涉入(in-volvement)進行搏斗[5]。國內學者認為,媒介體育是體育信息的媒介文化形態。具體說, 媒介體育是大眾認知體育現象和體育事件的中介,是大眾媒介以體育為傳播內容,以圖像、音響、文字、色彩等系統符號為形式,囊括了與體育相關的所有新聞類、專題類、訪談類、娛樂類節目或報道的媒介文化形態[6]。這樣的定義不僅讓我們看到現代體育的一種特殊形態——不同于呈現在賽場上、跑道上的體育運動,各種體育形態以文字、圖像、聲音的方式讓受眾知曉、感知、迷狂,更甚于現場觀看,而且,塑造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不同于用身體參與體育運動,沒有面對面的了解和交流,甚至一生未曾謀面,卻共享同樣的故事和精神。他們或為了一支球隊,或為了一位球星(體育明星),或為了一場比賽,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膚色不同年齡性別的人組成“共同體”,為了一個運動品牌的服裝、球拍和裝備,全球不同角落的人有共同的消費和時尚,或是被同一個廣告吸引、打動。不用血緣、地域的相連,不用真正的共同體,人們就能魔術般地有一種“共同體的體驗”,喚起一種歸屬感的快樂,卻沒有被限制的不適。不可否認,體育本身有其巨大的、特殊的誘惑力,但當媒介以收視率、閱聽率、點擊率為目標進行營銷,當體育賽事俱樂部圍繞利潤策劃布局,當品牌廣告商以廣告銷售額推廣所謂體育文化時,我們很難辨認分散的人群是被體育本身吸引還是被“數量權威”打動,也很難否認這是一種商業行為和消費行為。
在這個媒介體育的美學共同體中,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構成要素。
2.1 體育產品——美學共同體的核心
體育產品是體育消費者關注的對象,也是媒介體育追逐和關注的目標,是體育領域的美學共同體的緣起和存在依據。這里的體育產品特指那些具有聚焦價值、萬眾矚目的事物,包括體育明星、體育賽事、體育運動品牌或一個現象,而在今天的體育領域,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體育IP(即體育知識產權),包括賽事IP、俱樂部IP、體育明星IP等品牌。
奧運會和世界杯是最著名最悠久的體育IP之一,奠定了世界體育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也奠定了全球體育產業的基礎。歐系五大賽事和美系四大職業聯賽也是經典的賽事IP。NBA聯賽(美國職業籃球聯賽)至今已舉辦了超過70年,成為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職業體育組織,以42種語言向212個國家直播賽事,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體育商業品牌之一,年產值超過40億美元,邁克爾·喬丹、姚明、林書豪等NBA明星更是家喻戶曉。英國體育最經典的IP英超聯賽,也是收入最高的足球聯賽。英超2016-2017賽季的總收入為45億英鎊,在全球的足球聯賽中位居首位,而這比收入排名第二的德甲聯賽要高出20多億英鎊。幾乎每一個體育迷去英國都會選擇在豪門球隊看一場球,再帶回一條屬于主隊的圍巾。在中國,最成熟的兩個體育IP資源當屬中超聯賽和CBA,正是經典IP背后存在的巨大利潤空間,讓資本競相追逐這些在中國還未完全開發的體育資源。
體育產品是美學共同體中體現其價值和特色的本質和規定性所在。我們看到,媒介體育時代的體育產品已經不是脫離媒介和消費者影響的獨立存在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明星(偶像)、大型賽事和品牌都是大眾媒介傳播推廣的產物。以電視為代表的媒介的普及使一些體育項目廣為人知,并且將一些體育明星塑造成為英雄式的人物或青少年模仿的時尚榜樣。今天,媒介可以直接發明或促成賽事。媒介的商業邏輯甚至導致媒介對體育的控制和征服,強迫體育犧牲自身的特性與規律來屈從媒介的標準和價值。
體育消費從實物型到觀賞型,再到參與型。體育消費中最持久最具吸引力的不是實物消費,而是觀賞和參與,其基礎是對賽事或明星等體育IP的認同,這與娛樂圈的原理一致。在現代消費社會,體育產品的功能亦遠遠超越了健身的需要甚至體育本身的范疇——追求出類拔萃、擺闊消費、跟國際潮流和追求對社會毫無意義的個人刺激。新潮運動項目的發明越來越快——那些趕潮流的人總是在尋找下一個可能出現的潮流,而且也能讓人明白為什么體育越來越成為娛樂業的組成部分。秀和體育賽事互相幫襯促成超大型活動,使得新英格蘭愛國者隊和紐約巨人隊之間的比賽在世界范圍內有8億人觀看。福布斯榜把體育明星和電影以及波普明星一起放在名人欄,遵循的亦是這種邏輯[7]。
2.2 體育消費者——美學共同體的成員
這里所謂的體育消費者不僅包括因為熱愛體育運動而親身參與和親臨體育場所觀看的個體,更指向那些接觸和使用媒介體育的數量更大的人群。也不僅指體育運動“迷”,還包括“看熱鬧”、單單被宏大賽事或體育明星所吸引的人,即被今天的體育資本稱作的“泛體育人群”。在體育學科研究中,他們可能屬于某種意義上的體育人口,具有體育社會學上的意義。但他們對于物品的消費已不僅局限于最基本的使用價值,而是意圖通過消費其中被賦予的符號價值或文化意義,達成反映自我定位、生活方式、建構社會認同的目的。即他們通過體育消費的是觀賞,是文化,是價值。
如騰訊體育一開始瞄準的就是更廣泛的大眾市場,而非體育迷市場。騰訊體育希望通過體育和娛樂跨界的方式,吸引更多非體育核心人群用戶關注到體育中來,慢慢喜歡上體育,成為體育產業的核心人群,慢慢地把泛體育人群變成體育人群[8]。這樣的定位是符合美學共同體的特點的。
在消費社會,消費者通過大量的視覺文化消費(購物中心、巨幅商業廣告、電視、電影網絡等多媒體制造的偶像、明星形象),模仿他者的審美品位和消費習性,追逐時尚。在體育領域同樣如此。國內有學者根據Wenner和Gantz(1989)以洛杉磯等地的居民為對象,研究受訪者收看電視體育節目的動機的結果,歸納出消費動機的四個要素:①獲得喜愛球員或球隊的信息;②休閑、娛樂及情節的刺激;③通過觀賞體育獲得交談的題材,進而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④認同,體現主體與體育對象(球隊或球員)的一種依屬關系[9]。在倫理學和“共同體”視域下,體育消費者與消費社會里那些時尚與美的追逐者和消費者一樣,是尋求身份認同和意義的美學共同體的一員。
不管是后現代學者,還是后現代消費大眾,大都將個體自由的新希望寄托于審美,認為審美生活才是最為道德的生活。在美學共同體中,人們期冀在享受自由的同時又能規避自由所產生的風險后果。如果說基于審美化倫理的個體的自由感和不安全感是這一倫理的一體兩面,那么歸屬于一個“美學共同體”,則意味著審美的個體之間互相結合,成就一個自由與安全圓融為一的有機體。可以說,在這一美學共同體中,“人們以各種格局相處在一起,以體驗多重的吸引、感覺、感知以及一個超邏輯共同體的生機,體驗同在一起的具體感覺以及因依附于同一個可被別人認知的符號的共同情感而產生的共同感”[10]。想想在奧運會和世界杯期間迅速積聚的人群和關注度,又怎樣在賽事結束后迅速消散,就能理解這個特點。
美學共同體成員作為消費群體是超越地域、國家、種族甚至宗教的,他們不是因傳統的血緣、民族性、宗教信仰甚至地緣性而結盟,而僅僅是因著被媒介傳播及擴張的體育產品所吸引去追逐和消費而形成的“共同體”,其脆弱性和暫時性是天生的。
2.3 媒介——美學共同體的構造者和放大器
英國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提出的鄧巴數理論指出,在小于鄧巴數限制的群體規模內,人類的認知能力能夠借助記憶完成對他人的個性化認知,從而建立親密的關系;在大于鄧巴數限制的群體規模以后,人類的認知能力就無法依靠記憶實現對他人的個性化認知,需要借助新發明的認知工具才能建立合作關系。超越鄧巴數限制,實現陌生人之間的大范圍合作,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也是人類社會結構區別于其他動物群體結構的重要特征。為了實現陌生人之間的合作,人類創造了各種工具,從神話到法律,從傳說到契約,從宗教到帝國,從信仰到金錢,而媒介也是人類創造的這種突破人類認知限制的鄧巴數的工具之一。
通訊和媒介技術的每一次革新和進步都帶來體育和體育傳播的擴張,促進了受眾和消費者的巨量增長,在傳播上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甚至突破了專業和興趣的界限,看看世界杯和奧運會期間興致勃勃的“假球迷”和“體育盲”就能明白。這樣的群體是超越地域、種族甚至宗教的。因此,媒介構造了跨越時空共享共情懸念或榮耀時刻的巨大人群——看不見的美學共同體。
而在美學共同體中,媒介的重要功能是達成數量權威。鮑曼認為,在這個地方性褊狹觀點和“地方意見領袖”緩慢而又無情死亡的時代,只有兩種權威被保留下來,一是“知道得更好”的專家權威,二是數量權威,即數量越多,錯誤的可能性越小,這種確定性和穩固性是從大眾壯觀的分量中借取的。這樣一種夢想的共同體通過令人敬畏的數字的力量來證明目前選擇的正當性,并烙上“社會同意”的身份認同。媒介在美學共同體中起到了這種放大器的作用。媒介體育的超速發展也正是看準并順應了這樣的媒介放大器作用。如英超2016-2017賽季的總收入為45億英鎊,在全球的足球聯賽中位居首位,而這比收入排名第二的德甲聯賽要高出20多億英鎊。而這種差距也主要體現在電視轉播收入的差距上,2016-2017賽季,英超20隊上個賽季一共得到了28億英鎊的電視轉播費,而德甲18隊上個賽季的電視轉播費總收入僅為14億英鎊。
由此可見,體育產品、體育消費者與媒介各司其職又通力合作,形成了體育中的美學共同體。我們今天常見的“流量、粉絲、品牌效應、情感因素”這些詞匯都與“美學共同體”理論有密切的關系。以此來看待現實中的體育現象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以國際冠軍杯ICC(International Champions Cup)為例,2015年進入中國,連續舉辦了三年,2018年未將中國作為比賽地。2017年中國的四場比賽,電視觀眾有3 100萬之多,現場觀眾只有13萬,反觀美國,電視觀眾600萬,但現場觀眾達到了65萬之多。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西班牙國家德比涌入了6萬觀眾,平均票價高達750美元,在新加坡的比賽則有5萬觀眾,相比之下,中國賽的上座率就顯得可憐。為什么擁有最大球迷人群的中國在票房上的貢獻遠沒有想象中那么巨大呢?中國球迷對足球的巨大熱情和場均3.25萬人的上座形成巨大反差,這讓主辦方感到失望。“看上去,中國的球迷沒有海外球迷那么喜歡去現場。我能夠感受到ICC在中國的熱度,比如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在談論ICC,很多媒體都在報道ICC,但真正要去球場看比賽時,很多球迷選擇待在家里”[11]。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當然有國內場地設備、條件及配套設施等各方面的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球迷和體育消費者首先是從媒體認識并迷上國外明星球隊和球星的,和歐美本地球迷不同,與他們缺乏傳統共同體中本應具備的血緣、地緣或文化上的關聯,如前文所述,美學共同體天生的脆弱性和暫時性決定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愿意為“消費”付出的代價是有限的。
3 媒介體育美學共同體的特征
媒介體育作為美學共同體體現出當代體育消費大眾對歸屬于一個溫馨舒適的“美學共同體”的強烈渴望,展現出消費個體之審美自由意趣追尋集體共鳴并達致“同一個心,共一個靈”的現實需求。但在實際體驗中,因其固有性質卻顯示出與這個訴求不盡相符的特征。
3.1 易碎的穩定性
如前所述,美學共同體的確定性和穩定性是由其數量權威引致的,這似乎為共同體帶來了某種安全感。但與一個真實的體育俱樂部、體育協會或球迷組織不同,媒介體育中的共同體雖然個體數量巨大,卻是易碎的,解散它和組合它同樣容易。它的建立和解體必須取決于那些組成它的人作出的選擇——取決于他們賦予還是撤消對它的忠誠的決定。這種忠誠決定不是一經宣布就變得不可撤消了:這種選擇造成的聯結不應該是不便,更不用說是妨礙進一步的和不同的選擇了[2]。事實上,后現代社會對時尚包括對體育時尚和明星的不斷追求與更新,使得“美學共同體”處于一種不斷產生又不斷消失的狀態,實在是易碎的。
3.2 虛假的歸屬感
與現代個體對“道德共同體”的歸屬感不同,后現代個體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并不取決于某種一致的倫理規則,而是取決于他們所共同關注的審美焦點,一場精彩的賽事,一個備受歡迎的體育明星,抑或一個吸引大眾眼球的媒介事件。事實上,消費時代個體對“美學共同體”的歸屬感主要便源于商業偶像之導引,因為“偶像造就了一個小小的奇跡:他們使得不可思議的東西發生;不用真正的共同體,他們就能魔術般地讓人有一種‘共同體的體驗’,喚起一種歸屬感的快樂,卻沒有被限制的不適”[2]。
盡管后現代的“美學共同體”作為一種無限制的交往共同體,描繪出一種“審美的共同生活將使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主成為可能”的美好圖景,不過,在這一以商業偶像為導引的共同體中,個體的歸屬感依然是虛妄的,相比之下,孤獨感才是“美學共同體”中每個個體的真實遭際,因此,就每個個體而言,“每個人都將他者分配成他為游戲設置的舞臺上的一個支持者”, “他者僅僅以快樂對象的面目出現”[12]。很顯然,這種將他者功用化的“美學共同體”,最終是無法給予個體以歸屬感的,恰恰相反,與各類賽事的狂熱和大眾狂歡相對照的,是實際生活中每位個體的無盡的落寞與空虛,媒介體育的狂熱觀眾,最終在消費時代“美學共同體”中收獲的,不過是狂歡與熱情背后的無可避免的“原子式”的孤獨感,從根本上看,“他們日復一日被允諾的,是一個沒有歸屬的共同體,是孤獨者的和睦相處”[2]。
3.3 內在的矛盾性
從以上兩個特征就可以看出,媒介體育中的美學共同體具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性,這至少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物質與精神的矛盾,二是自由與安全的矛盾,三是永恒與易逝的矛盾。
4 思考與啟發
綜上所述,當代消費社會意圖藉由審美而塑造一個有機的共同體社會,媒介體育作為一種美學共同體是后現代社會消費取向在體育領域的特有呈現,具有虛擬性和想象感,與過去那種地域性的、凝固性的、整體性的道德共同體不同,美學共同體是不穩定的、開放的,它是社會碎片化和大眾文化消散的產物,是消費時代孤寂個體所創造出來的基于“想象的安全感”的真實共同體的替代品。
不同于媒介體育這種美學共同體,真正的、真實的體育共同體無法在短時間內形成,也不可能僅僅依靠數量權威達成,為什么上文所述ICC在中國現場遇冷?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真正的由俱樂部與球迷聯結而成的牢固的共同體尚未形成,美系四大職業聯賽在1950年前即已成型,歐系五大賽事更是集中在1930年前就已形成,世界上IP價值最高的體育賽事在1950年前已基本形成,都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反觀中國,稍具規模的中超、CBA、乒超在20世紀末才初步形成,市場、球迷包括各種硬件的完善尚需時日,即使有資本也無法一蹴而就。資本有資本的需求,但市場有市場的規律,體育共同體也有其生長的過程和規律,媒介體育不是體育的一切,美學共同體無法代替真實的共同體。它的龐大、熱鬧和喧囂也許可以成為資本有利可圖的資源,但卻值得冷靜的研究者從另一個視角思考體育及媒介種種,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反思當今體育界的各種經濟現象和倫理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