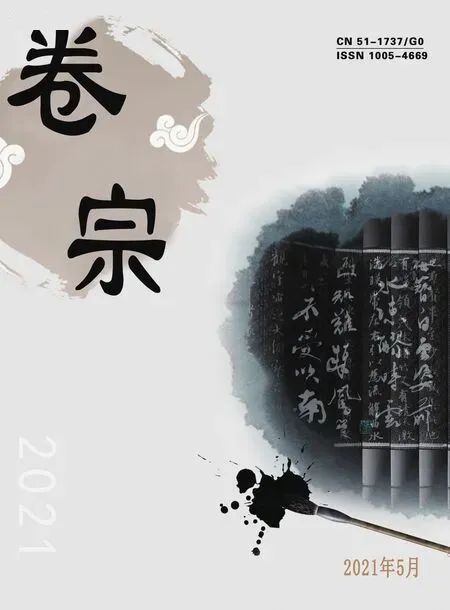淺析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以“吃食堂”“給力”“可愛”為例
原俊寧
(攀枝花學(xué)院外國語學(xué)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1 引言
吃+NP的結(jié)構(gòu)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吃食堂”類短語是特殊的,因為如果從傳統(tǒng)語法來分析,NP是“吃”的受事,那么NP必須有可以被吃的屬性,如“吃蘋果”、“吃早餐”等等。顯然,“食堂”是一個處所,不可以被吃。但是在生活中,“吃食堂”“飛北京”等短語是人們都可以理解熟知并且廣為接受的。這類短語表現(xiàn)出句法語義錯配現(xiàn)象,因而一直受廣大學(xué)者們高度重視,并有許多優(yōu)秀而深入的研究成果。隨著社會和語言的發(fā)展,“吃食堂”所映射的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也越來越受學(xué)者們關(guān)注。本文以之前的研究為基礎(chǔ),從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來進(jìn)一步分析“吃食堂”之類的短語,并淺析該原則對現(xiàn)代生活中的語言的影響。
2 相關(guān)研究回顧
前輩們的研究出發(fā)點和視角各有不同,研究理論也頗有洞見。通過對學(xué)者們之前的總結(jié)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學(xué)者們有的從某一個角度分析,有的從多個角度分析,而研究角度主要有:句法學(xué)、語義學(xué)、語用學(xué)、認(rèn)知語言學(xué)以及民族心理學(xué)方面等。
在漢語中,由于不存在顯性格,不需要以格特征和格過濾來核查語義匹配,語義的匹配較英語寬松,這就使得同食物語義關(guān)聯(lián)的“食堂”等詞項能夠進(jìn)入該類表達(dá),這類表達(dá)在句法上合法。“吃食堂”中違反了論旨指派要求,主動詞不能為論元指派論旨,所以論元允準(zhǔn)成為研究的重點(Lin 2001;Zhang 2002;郭繼懋1999;馮勝利2005;楊永忠2007,2009;程杰2009;孫天琦2009)文獻(xiàn)中把相關(guān)論元稱為外圍格(袁毓林1994)、非核心論元(程杰2009;孫天琦2009;孫天琦、李亞非2010)、或涉用格(胡建華2010)。生成語法研究認(rèn)為,構(gòu)成這一結(jié)構(gòu)特殊性的主因是動詞具備不同的詞匯語義表征或漢語中部分動詞可以不選擇標(biāo)準(zhǔn)題元來解讀而獲得句法實現(xiàn)。構(gòu)式語法則認(rèn)為“吃食堂”是單賓語句的基本構(gòu)式之一。認(rèn)知語法研究認(rèn)為,“吃食堂”結(jié)構(gòu)中的“食堂”是受事賓語的轉(zhuǎn)喻形式。計算語言學(xué)家則認(rèn)為“吃食堂”這一結(jié)構(gòu)屬于漢語語義表達(dá)框架中的廣義配價模式。
孫天琦(2009)認(rèn)為“吃食堂”中食堂是光桿名詞,即使加定語也只能加限制性或黏合式定語,不能加描寫性或組合式定語。例如,不能說“吃干凈的食堂”,也不能說“吃豪華的/三個/老張的飯店”這樣的表達(dá)。唐依力、齊滬揚(2010)認(rèn)為“吃食堂”類結(jié)構(gòu)中名詞是無定的,且指稱意義極弱,并認(rèn)為名詞成分若屬于基本層次范疇,則更利于信息的交流,這體現(xiàn)了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但若是處所名詞表達(dá)基本層次及范疇的下位概念,只要提供足夠的語境信息,這類名詞依然可以用在“名詞+處所”結(jié)構(gòu)中。
在《換一種思路看漢語中的“吃食堂”類語言現(xiàn)象》這篇文章中,汪玉寶和趙建軍兩位學(xué)者論述了因動賓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導(dǎo)致用當(dāng)前流行的動賓結(jié)構(gòu)理論解析“吃食堂”類語言現(xiàn)象帶來的困擾,并提出一種新思路,不能僅從共時的結(jié)構(gòu)層面尋找語言現(xiàn)象存在的本質(zhì)原因,而應(yīng)立足于該民族思維方式的特性。他們進(jìn)一步論證了“吃食堂”類動名結(jié)構(gòu)的語言現(xiàn)象是漢民族直覺性“兩點論”思維方式固化在漢語中的一種典型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
眾所周知,語言反映社會與文化。因此,隨著社會的信息化大發(fā)展,語言也隨之發(fā)生了很多改變。當(dāng)今的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人們的語言也變得很簡潔,這樣會節(jié)省交際時間,提高交際效率。“吃食堂”便比“吃食堂的飯”或者“在食堂吃飯”簡潔許多,同時,也不會使交際雙方產(chǎn)生交際障礙。這就是“吃食堂”所映射的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3 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經(jīng)濟(jì)原則既可以指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也可以指既定目標(biāo)下的成本最小化。語言學(xué)中的經(jīng)濟(jì)原則是從經(jīng)濟(jì)學(xué)中的經(jīng)濟(jì)原則借用而來的。學(xué)者齊夫(George Zipf 1949)首次明確提出這一原則。齊夫認(rèn)為,人們交際時總是傾向于選擇既能夠滿足說話者完整表達(dá)又能滿足聽者完全理解所需的最少的語符,這就是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其實,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典籍里早有論述。劉勰在《文心雕龍﹒镕裁》中指出:“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劉勰把文章中的贅文、累句、浮詞比作多余的“駢拇枝指”,提出要“芟繁剪穢”,刪減重復(fù),使文章“弛于負(fù)擔(dān)”。這段話的實質(zhì)就是要求語言投入最小化,即“如果一個詞足夠的話,決不用第二個”。
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又叫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或者省力原則,我們認(rèn)為是指語言系統(tǒng)本身以及語言運用過程中數(shù)量與效果二者的最佳結(jié)合。具體說來是在效果不變的情況下盡可能減少數(shù)量;在數(shù)量既定的情況下,盡量擴(kuò)大效果;或者是數(shù)量減少而效果擴(kuò)大的。凡是符合上述三種情況之一者,我們都認(rèn)為是符合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是語言經(jīng)濟(jì)性的體現(xiàn)。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始終貫穿于語言的各個層次和語言發(fā)展的各個階段,是語言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經(jīng)濟(jì)性也因此被認(rèn)為是語言普遍性的一個重要方面。這里所謂的“數(shù)量”是指詞語或者句子的長度,也就是詞的數(shù)量的多少,這個跟時間是緊密聯(lián)系的,因為數(shù)量越少,寫出來或者說出來所需要的時間就越少,消耗的體力就越少,所以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數(shù)量、時間、體力的消耗三者是相一致的概念。
惠特尼(1827---1894)是美國第一代語言學(xué)家的杰出代表,被公認(rèn)為“美國語言學(xué)的先驅(qū)和揭幕人”。惠特尼最早體現(xiàn)語言經(jīng)濟(jì)思想的論述見于其專著《語言和語言研究》。他說:“所有的語音發(fā)出來都依賴力,消耗肺、喉和嘴里肌肉的能量。這個力,像其他所有人類發(fā)出的力一樣,有一個本能的特點,就是尋求減負(fù)和避讓---我們稱之為惰性,或者稱之為經(jīng)濟(jì)。”“實用的方便成了至高無上的考慮,其他的考慮都向其讓步。”惠特尼認(rèn)為建議傾向的產(chǎn)生與語言的性質(zhì)有密切的關(guān)系。他說:“因為語言是一種工具,與其他工具相比,簡化(語言工具)初始形式這一法則同樣具有自然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說,人類在使用工具時自然會追求工具的易于操作性,語言既然是一種工具,人類在使用語言時,也自然會追求語言的簡易性。
惠特尼主張,簡易傾向并非簡單地引導(dǎo)人們走捷徑,這一傾向是語言發(fā)展的一個主流旋律,符合語言本質(zhì)的趨向,并且這一現(xiàn)象只會促進(jìn)語言的簡化和方便,而不會對語言產(chǎn)生任何傷害。他說:“省略掉語言的某些部分不會破壞對意義的理解,而會使語言更容易掌握,更符合習(xí)慣和偏好。語言科學(xué)還沒有發(fā)現(xiàn)比這更基本的規(guī)律,或者能與此并駕齊驅(qū)的規(guī)律。這是貫穿世界語言的一個主流,它推動語言材料向一個特定方向移動,盡管向其他潮流一樣,它也有逆流,小規(guī)模的相反方向的運動似乎可以占上風(fēng)。這一主流趨勢的另外一個表現(xiàn)就是:引導(dǎo)人們在書寫時使用簡略寫法,避開通常的路線而走捷徑,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
惠特尼還指出:“語言中的經(jīng)濟(jì)傾向恰恰在于它是‘破壞性’行為的同時也是具有建設(shè)性的行為。它最初產(chǎn)生的那些形式后來被刪減、扔棄;如果沒有簡易傾向,合成詞以及組合型的短語會一直是老樣子。”簡言之,其影響是使得松散的構(gòu)造“變成純粹的符號,使符號更加簡易”。這實際揭示了新詞和新表達(dá)式產(chǎn)生的方式之一:對已有的形式進(jìn)行刪減或壓縮,也就是說,惠特尼已注意到簡易傾向?qū)π抡Z詞和新表達(dá)式產(chǎn)生的推動作用。
惠特尼在討論簡易傾向的意義時已經(jīng)有很周全的考慮,他細(xì)心地區(qū)分了“經(jīng)濟(jì)”和“糟蹋”。他說:“這些舉措不會對語言有任何傷害,除非比潛在的經(jīng)濟(jì)性失去了更多的東西,那樣確實就是‘懶惰’而非‘經(jīng)濟(jì)’了。在語言的運用過程中會出現(xiàn)兩種情況:真正的經(jīng)濟(jì)和懶惰的糟蹋。”這里實際提出了兩個觀點:第一個,運用經(jīng)濟(jì)原則時的“經(jīng)濟(jì)”是有度的,超過了一定的度就不再是“經(jīng)濟(jì)”而是由于懶惰而在“糟蹋”語言;第二,在語言演化過程中具有建設(shè)性意義的,是“真正的經(jīng)濟(jì)”而非“懶惰的糟蹋”。
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意味著語言使用過程中的“收獲、節(jié)約、節(jié)省、省時”,這一原則規(guī)約著交際雙方,使交際活動得以順利進(jìn)行。交際過程中,在達(dá)到交際目的的情況下,發(fā)話人盡量減少詞語的使用,而聽話人則希望發(fā)話人盡量說得詳盡、清晰一些,這似乎形成了一對不可調(diào)解的矛盾。從經(jīng)濟(jì)的角度探討語言使用原則,就涉及交際雙方照顧對方的認(rèn)知能力和利益訴求,使雙方不因信息過于簡單或者冗余而使交際無法進(jìn)行下去。因此,語言經(jīng)濟(jì)性要求交際雙方把握語言經(jīng)濟(jì)的程度。
通過對實例“吃食堂”、“給力”“可愛”的分析,就可以較為全面的理解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4 “吃食堂”“給力”“可愛”中的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漢語是一種意合的語言,人們對語義的理解往往會憑借語境及語感來完成。中國的傳統(tǒng)思維注重直覺經(jīng)驗,人的主觀認(rèn)知往往會加入到句法結(jié)構(gòu)中,因而人們常常把語義相關(guān)的詞語相互替換進(jìn)行組合。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普遍存在于現(xiàn)實會話中,比如“吃食堂”、“給力”、“可愛”等等這些詞匯都是在交際過程中被人們廣泛使用的。但是,這三個詞匯也從不同的角度表現(xiàn)了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多個層面。
4.1 “吃食堂”
對于“吃食堂”、“一張北京”、“飛上海”之類短語,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是“吃食堂的飯”“一張到北京的車票” “乘飛機(jī)去上海”。這種認(rèn)為是追求語言“經(jīng)濟(jì)”性的分析一直以來都是被認(rèn)可的。這也正好滿足了Haiman的觀點,即包括Vi+NP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有標(biāo)記句式的產(chǎn)生是為了獲得表達(dá)上的經(jīng)濟(jì)性,表現(xiàn)為語言表達(dá)方式的縮短或簡化,以實現(xiàn)“邏輯省略”、“語法省略”和“語音省略”。刑福義也提出一條重要的語用原則,認(rèn)為借助言語背景,言語盡可能經(jīng)濟(jì)簡練。這也與人們的常說性有關(guān),畢竟“吃菊園一號的食堂”就沒有“吃食堂”這么容易被人理解以及被人使用。“食堂的飯”和“食堂”有明顯的意義上的聯(lián)系,在一定言語背景的前提下,人們受實踐經(jīng)驗和直覺經(jīng)驗的支配,將二者進(jìn)行替換,用吃的場所代替食物,形成了“吃食堂”這種特殊的表達(dá)形式。
語言具有社會性,“吃食堂”類短語語言表達(dá)方式極為有效,以最少量的話語表達(dá)出無窮的語言留白,同時兼?zhèn)淝擅畹穆?lián)想,是經(jīng)濟(jì)與色彩的融合,這便是這種表達(dá)得以廣泛應(yīng)用的原因。在語言交際中,人們總是傾向于用簡潔的話語表達(dá)盡可能多的信息,即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吃食堂”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語言的優(yōu)化型和經(jīng)濟(jì)性。語言優(yōu)化最重要的表現(xiàn)便是以簡馭繁。“吃食堂”結(jié)構(gòu)在表達(dá)上簡潔明了,在一定的言語背景中,在不產(chǎn)生歧義的前提下,依靠人已有的認(rèn)知能力,用食物存在的處所代表食物本身,省去了冗長的成分,簡化了句法結(jié)構(gòu),使語言表達(dá)經(jīng)濟(jì)簡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造出類似的結(jié)構(gòu),如吃大碗(吃大碗的飯),掏鳥窩(掏鳥窩的蛋)等。
4.2 “給力”
Werner Leopold 指出,“語言發(fā)展并非遵循一種趨勢,而是兩種相反的趨勢:清晰趨勢和經(jīng)濟(jì)趨勢。清晰和經(jīng)濟(jì)兩極現(xiàn)象總有一種占優(yōu)勢,但都存在且交替出現(xiàn)。”Tauli 則認(rèn)為語言演化是由五種驅(qū)動力所決定的,即清晰趨勢、容易或省力趨勢、情感沖動、美學(xué)趨勢和社會沖動。“給力”而不說“給予力量/支持”,言簡意賅而傳神。因而“給力”一詞廣受歡迎,并登上了《人民日報》、《紐約時報》,而“gelivable”也流傳開來。“給力”與“給予力量/支持”相比,二者有密切的聯(lián)系,可以以感性的經(jīng)驗?zāi)J綖榛A(chǔ)使表達(dá)更為自然、簡潔,在日常語言交際中被廣泛應(yīng)用。
4.3 “可愛”
在網(wǎng)民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建構(gòu)網(wǎng)絡(luò)流行話語的過程中,難免存在著構(gòu)詞不規(guī)范和使用不符合現(xiàn)代漢語的詞語規(guī)范要求和語法規(guī)定的失范現(xiàn)象。因為這種不規(guī)范很容易造成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形成受到變異語碼的干擾,形成信息過載和閱讀障礙,破壞了現(xiàn)代漢語的純潔性。網(wǎng)絡(luò)流行語一直以來被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語言學(xué)家所詬病。“可愛”被作為“可憐沒人愛”的縮略語,“蛋白質(zhì)”被作為“笨蛋+白癡+神經(jīng)質(zhì)”的縮略語,在這里,并不是“真正的經(jīng)濟(jì)”,或者可以說,這偏離了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實質(zhì)。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使用是有條件的,語境、語言結(jié)構(gòu)及社會心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語言能夠充分明晰地表達(dá)意義和情感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
5 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與詞語發(fā)展
語言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是語言的一條根本原則,是語言變化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語言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表達(dá)、交際。在言語交際中,交際者在特定的語境中用相對較少的語言手段明白無誤地表達(dá)出交際意圖,但并不是說數(shù)量越少就越好,因為只有那些更有效地表達(dá)了言語意圖的距自己才是真正經(jīng)濟(jì)的,也就是說,要從言語的表達(dá)效果、交際目的以及其所達(dá)到的功能等多個角度進(jìn)行綜合考慮,這就有一個數(shù)量和效果最佳結(jié)合的問題,這種結(jié)合是在表達(dá)和交際中衡量的,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并不是靜態(tài)的。
語言是人類最主要的交際工具,它服務(wù)于社會,并隨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當(dāng)代科技以迅猛的速度向前發(fā)展,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也日益加快,為了適應(yīng)這種情況,語言表達(dá)方式的簡化即“縮約”,就成為當(dāng)代語言發(fā)展的一個顯著趨勢。語言中的“縮約”現(xiàn)象首先受到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的制約。隨著網(wǎng)絡(luò)的發(fā)展和網(wǎng)民們所形成的新的語言社區(qū)的壯大,網(wǎng)絡(luò)交際語言正以它獨有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中,并逐漸形成自己的體系。同時,網(wǎng)絡(luò)語言也對現(xiàn)有的語言產(chǎn)生沖擊和挑戰(zhàn)。
經(jīng)濟(jì)原則在語言使用中起普遍性的規(guī)約作用,它使交際雙方在言語復(fù)雜性傾向和簡約性傾向的競爭過程中達(dá)到均衡狀態(tài),是交際雙方能夠順利進(jìn)行。并且,經(jīng)濟(jì)原則也是維持語言正常運轉(zhuǎn)的重要原則,是規(guī)范語言使用的語用機(jī)制。
在當(dāng)今社會,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越來越重要。人們在說話時,總是會尋找一個最簡潔而又不會有交際障礙的表達(dá)。因此,諸如“吃食堂”、“給力”、“可愛”這些詞語頻頻出現(xiàn)在人們口中,只是,在網(wǎng)絡(luò)流行語橫出的社會,人們需要去辨別其中的可行與否,做到“真正的經(jīng)濟(jì)”。
6 結(jié)語
“吃食堂”是一種簡潔說法,受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影響。而現(xiàn)代生活中的語言受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因此“給力”、“可愛”等這些簡單的詞匯不斷涌現(xiàn)。而從傳統(tǒng)語法分析,并不能解釋清晰。因此,語言學(xué)家們從其他多個角度分析研究,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便是其中之一。語言是社會的語言,處在不斷變化發(fā)展中,經(jīng)濟(jì)原則便是其依據(jù)之一。著名語言學(xué)家陳源說:“語言的變異是任何一種活的語言所經(jīng)常發(fā)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沒有變異的語言是僵化的語言,是死的語言。”本文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淺析一直以來深受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吃食堂”之類短語,并從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比較了“吃食堂”、“給力”、“可愛”三個詞語,以供參考。將語言經(jīng)濟(jì)原則與不斷變化的實際語言相結(jié)合的深刻問題,還值得進(jìn)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