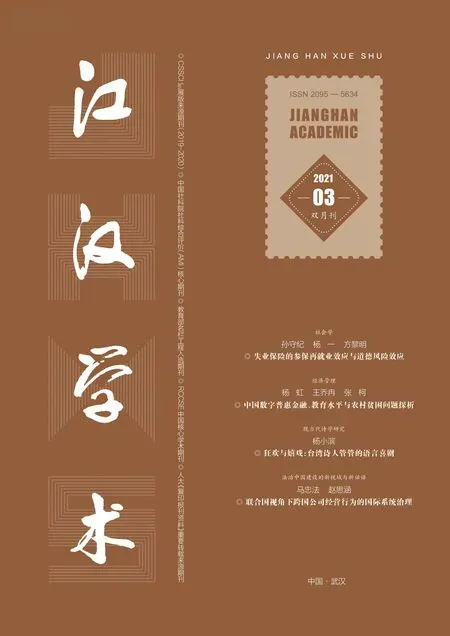從感性的碰撞到學理的輸入
——論早期外國詩歌譯介與詩學研究的展開
朱明明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100048)
從梁啟超首次譯出《端志安》與《渣阿亞》,到胡適稱一首譯詩《關不住了》——為“我的新詩成立的新紀元”[1],歷經約十七年的時間。然而,在胡適使用了十一個外國譯音字的《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之后,僅僅兩三年的時間,外國文字已經直接可見于“新詩”的標題和詩句中了,如郭沫若以羅馬愛神的英文名為題的詩《Venus》以及直接使用英文的《演奏會上》等詩。這種“西字插入”的現象,生動地反映出中國詩歌在新詩運動初期所呈現出的擁抱世界的激情。自此至1923 年前后,翻譯和介紹外國詩歌、輸入西方詩學原理的著作如井噴般不斷涌現,這些早期詩歌譯介的意義和貢獻主要是“放大了詩的眼光”,而詩學方法與原理的輸入,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訓練了詩人與讀者們對待詩歌的眼光。
一、擁抱世界的氣象
以“新”姿態問世的《青年雜志》,創刊之初就宣告了“世界的而非鎖國的”[2]這一理想。從他們的思想與立場上看,“新”即“近世”、“現代”或“當代”,“世界的”即“西洋的”或“歐洲的”,而實際上,這兩者又是分不開的一件事。比如,創刊號《新舊問題》一文直接宣稱:“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陳獨秀也有同樣的觀點:“近世文明,東西洋絕別為二。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歐羅巴文明,移植亞美利加,風靡亞細亞者,皆此物也。”[3]隨后,陳獨秀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贊歌》(選自《吉檀迦利》中的四首),以及一首贊美歌《亞美利加》的歌詞,與稍后《新青年》發表的其他譯詩一樣,兩篇都以中英對照的形式刊出。如果從陳獨秀及《青年雜志》對西洋文明的追求這點來看,那么翻譯“東洋詩人”泰戈爾的作品似乎與之相違背,況且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還曾介紹泰戈爾為“隱遁詩人”,不愿青年效仿。不過,譯后所附的詩人簡介多少透露了原因所在,即“馳名于西方世界”,陳獨秀這樣介紹泰戈爾:“印度當代詩人,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曾受Nobel Peace Prize,馳名歐洲,印度青年尊為先覺,其詩文富于宗教哲學之理想。”[4]
《新青年》初期的譯介基本是站在國家與民族獨立的立場上放眼世界的,直至《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后,才漸漸如周作人所說,主要出于“思想美妙,趣味普遍,而且也還比較的可以翻譯”[5]的原因,而且數量方面也有所增加,陸續刊載了劉半農、周作人、胡適等人的不少譯詩。然而,《新青年》對譯介和輸入外國詩歌資源的貢獻主要在于打開新的局面,而非建設的功勞。西方詩歌只是《新青年》認識西方的一個部分,引進外來資源革新中國詩歌,也只是《新青年》以西洋文明變革傳統中國的一個部分。也因此,對外國詩人的譯介明顯帶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基調。
如果說《新青年》時期引介外國詩歌主要是作為“認識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此后對于外國詩歌資源的引進則有了明顯的借鑒意識,以期彌補、改造傳統詩歌資源的局限。在《新青年》打開了譯介局面之后,接續的重要力量還有《時事新報·學燈》(1918)、《少年中國》(1919)、《小說月報》(1921)、《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921)、《晨報·副刊》(1921)、《詩》(1922)等,都不程度地加入了翻譯和介紹外國詩歌與思潮的生力軍,配合、推動了當時的“新詩”運動和詩學研究的發展。
《少年中國》創刊號就引介了對中國“新詩”運動造成影響深遠的美國詩人惠特曼,也預見性地宣示了這位美國詩人以及《少年中國》雜志將成為這一時期改造中國詩歌的主要力量。《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的作者田漢不僅介紹了惠特曼,還貢獻了可能是最早的惠特曼譯詩,即《太久太久了,美利堅》和《你,母親,和你那些完全平等的兒女》一詩中的第四節。1920 年初《少年中國》還連續推出了兩期“詩學研究號”,更是集中地介紹和翻譯了不少西方詩人及作品。比如《英國詩人勃來克的思想》首次引介了布萊克(William Blake),《近代法比六大詩人》集中介紹了比利時詩人魏爾哈倫(Emile Verhaeren)以及薩曼(Albert Samain)、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雷尼埃(Henri de Regnier)、雅姆斯(Fran?cis Jammes)和福爾(Paul Fort)等五位法國現代詩人。田漢選譯了鹽釜天飆(Shokama)所著《歌德詩的研究》中《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一章,由此不少歌德的詩作被翻譯出來①。此外,泰戈爾也是詩學研究號引介的重點。以黃仲蘇為例,兩期共翻譯泰戈爾詩23 首,并作《太戈爾傳》②,這應該是泰戈爾的詩作第一次被大量翻譯進來。另有介紹普希金的小傳《俄國詩豪樸思徑傳》和介紹比利時詩人兼劇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詩人梅德林》。自第二卷起,《少年中國》對法國詩歌的引進多了起來。周無在《在法蘭西近世文學的趨勢》一文中還將古爾蒙、雅姆斯與巴特利(Henry Bataille)一并稱為新浪漫主義(Néo-romantisme)的代表詩人加以介紹,還相繼翻譯出了象征派代表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兩首詩作《秋歌》和《他歌在我心里》以及法國現代詩人德斯帕克斯(émile Despax)的《幸福》,并作譯序簡要評價了這位死于一戰中的抒情詩人。李璜的《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概述了法國古典格律詩和巴那斯詩派,隨后著重介紹了法國象征詩派及波德萊爾和魏爾倫兩位代表詩人,最后引出了法國自由詩(Vers libre)的概念,同時介紹波德萊爾的還有田漢的《惡魔詩人波陀雷爾的百年祭》。黃仲蘇的《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雖題名為“1820 年以來”,實際上是梳理了法國抒情詩的歷史,著重介紹了1820 年以來的三個抒情詩流派,于其中翻譯出了不少浪漫派詩人拉馬丁(Lamartine)的詩作,又作《詩人微尼評傳》專門介紹了阿爾弗雷·德·維尼(Alfred de Vigny)這位法國浪漫派的先鋒,李思純還在《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一文中嘗試翻譯了不少英、法、德三國的抒情歌謠。此外,比較特別的是,《少年中國》還通過發表會員間交流詩歌經驗與詩學問題的通信,間接介紹了不少外國詩人及詩學思想。以上可見,無論從介紹外國詩人還是從詩歌翻譯上看,《少年中國》可謂“新詩”運動發端初期引進外國詩歌資源的重要陣地。
與《少年中國》存在一部分共享作者的《時事新報·學燈》,也積極從事外國詩歌與文學的譯介。致力于輸入新思想、新文藝的《學燈》,自1919 年宗白華任編輯以來,更是介紹、翻譯了不少外國詩人及其作品。如郭沫若譯自歌德《浮士德》的《鈔譯》《風光明媚的地方——浮士德悲壯劇中第二部之第一幕》及譯自惠特曼的《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里》,謝六逸也發表了兩首惠特曼譯詩《挽二老卒》和《在維克尼納森林中迷途》。引介外國詩與詩人的論文還有,詳細評介波德萊爾及法國詩歌的《鮑多萊爾》和《法國兩個詩人的紀念祭——凡而倫與鮑桃來爾》等。《學燈》還曾設“但丁六百年紀念”和“歌德紀念號”,集中地介紹了這兩位西方大詩人。此外,《十四年來的諾貝爾獎金的文學家》一文中也介紹了幾位諾獎詩人,如英國詩人吉卜林(Kipling)、德國抒情詩人海士(Heyse)、比利時詩人和劇作家梅特林克、印度詩人泰戈爾、瑞典詩人海定斯頓(Heidenstam)等。除了外國詩歌與詩人的譯介,本著輸入新學理的發刊理想,《學燈》還留意于介紹外國的批評理論及批評家,翻譯了文齊斯德(C.T.Winchester)《文學批評之原理》的一章,介紹了日本的廚川白村、丹麥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英國批評家西蒙斯(Arthur Symons)等。
另一個《時事新報》的副刊《文學》(《文學旬刊》《文學周刊》),可謂一支輸入外國詩歌資源的主力。本著“一面努力介紹世界文學到中國,一面努力創造中國的文學”[6]的創刊宗旨和“把翻譯看作和創作有同等的重要”[7]的旨趣態度,《文學》在翻譯外國詩歌、引介外國詩人及詩學觀念等方面,均有很大貢獻。自1921 年5 月創刊至1923 年前后,翻譯了很多重要的外國詩人。德國詩人如海涅的《情曲》、歌德的《對月》、《游客夜歌》和《所得》;英國及愛爾蘭詩人如雪萊的《給英國人》、王爾德的《幻想的裝飾》和《沉默的戀愛》、羅塞蒂的《瞧不見的風》、埃德加·坡的《烏鴉》、高爾斯華綏的《生命》、夏芝的《戀愛的悲歌》《苦痛》和《老媽媽的歌》等。泰戈爾的詩及日本詩歌翻譯得也比較多,前者如鄭振鐸對泰戈爾的翻譯,后者如譚槐對澤柳健和生田春月等人的翻譯。《文學》還發表了不少引介外國詩人的論文,如介紹夏芝的《愛爾蘭詩人夏芝》《得1923 年諾貝爾獎金者夏芝》等,以及一口氣列出了57 位詩人的《最近英國詩壇人物》。另有詩人評傳的翻譯,如K H 譯自克洛泡特金著《俄國文學論》的《普希金評傳》和《婁蒙妥夫評Lermontoff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學旬刊》自37期改為由文學研究會編輯后,格外重視“批評”的建設和翻譯,以提升讀者純正地理解作品的機會,因而開始發表譯介外國詩學原理和批評類的著作,如譯自勃利司·潘萊(Bliss Perry)《詩之研究》中的兩章《詩人與非詩人之區別》和《韻節及自由詩》;或是在討論詩學問題時刻意參照外國資源、有意識地輸入外國詩學觀念,如討論詩之概念的《何謂詩》一文援引了文齊斯德(Win?chester)、史特曼(Stedman)、華茲華士(Word?sworth)、席萊(Shelley)、愛摩生(Emerson)、安諾爾特(Arnold)等人的觀點,《詩歌的分類》一文則基本是在介紹歐洲詩歌的三大類,即抒情詩(Lyrical poetry)、史詩(Epic poetry)和劇詩(Dra?matic poetry)及其發展變遷情況。總之,《文學》在翻譯和引介外國詩歌資源方面所產生的廣泛影響是不可替代的。
1921 年1 月全面改革后的《小說月報》,本著“西洋文學變遷之過程有急需介紹與國人之必要”[8],開始空前熱情地輸入西洋名著與思潮,外國詩與詩人當然也是題中之義。其譯介涵蓋了俄、英、法、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日本、印度以及東歐各國,比較特別的如對俄國詩人屠格涅夫的翻譯,對瑞典諾獎詩人赫滕斯頓(Heidenstam)的翻譯和介紹,還有沈雁冰雜譯波蘭、捷克、烏克蘭、塞爾維亞等小民族詩歌等等,實在不勝枚舉。《小說月報》還陸續推出了“德國文學研究”“俄國文學研究”“太戈爾專號”“拜倫專號”“法國文學研究”等。同時,《小說月報》也很重視文學批評的譯介,信奉批評對于文學有極大影響,并且認為中國向來無所謂批評及標準,由此致力于引進西方理論以引導國人創造新文學。時任主編的鄭振鐸還列出了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在詩歌理論與批評方面,稍后林孖譯自埃德加·坡的《詩的原理》以及希和譯著的《論詩的根本概念與功能》,可以視為踐行這一主張的代表。
與《小說月報》這樣熱情地擁抱世界、輸入外國詩歌與文學資源不同,《詩》月刊努力于建設、呵護“新詩”本身,而不旨在“大規模地介紹與研究”以求“為人生”的文學。其實,像《文學》和《小說月報》這樣大型的刊物,盡管有著超大容量,在大規模的輸入的同時,仍不免時而給人以生吞活剝之感。《詩》月刊則宣布了一種“游戲”的態度。編輯余談中有這樣的話:
我們覺得把一種雜志辦得好些很為有趣,所以我們自己為本刊作文乃是滿足興趣,滿足游戲的沖動,進一步說,就是我們(或者只是我)編輯本刊也是因為滿足游戲的沖動——雖然好唱高調的人曾反對以游戲的態度對待文學,但我則以為不當一概而論。我們說出自己做文章的意思,一則期望讀者對于我們的文章不能期望過深,二則希望讀者將來注意詩篇甚于文章。[9]
《詩》沒有發刊宣言,但這里希望讀者“注意于詩”,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宣言。《詩》的宗旨在為當時國內較好的“新詩”提供發表的場所,盡管也發表一些討論詩歌問題以及介紹外國詩人與詩的文字,卻只是“附帶及之”。雖說如此,《詩》還是貢獻了許多外國詩歌的翻譯,所選譯詩歌基本為近代,且選取范圍十分廣泛,既包括并不罕見的詩人如泰戈爾、雪萊等,也有比較少見的華茲華斯、勃來克等詩人。代表性的如陳南士對雪萊和德國現代詩歌的翻譯,周作人對日本俗歌和法國俳句的翻譯,王統照對愛爾蘭詩人阿林厄姆(William Allingham)的翻譯,俞平伯對波德萊爾散文詩的翻譯,還有沈雁冰對烏克蘭詩人凡特科維奇(Yuriy Fedkovych)和南斯拉夫民間抒情詩的翻譯等。重點在于,這些翻譯往往伴有譯者的附跋或小序,如王統照譯愛爾蘭詩歌的附識、陳南士譯德國現代詩十首附跋,盡管簡短卻不同程度地介紹了所譯詩人或詩派。不僅如此,《詩》還發表了不少有影響力、有價值的介紹外國詩歌的論文,如劉延陵的《美國的新詩運動》《現代的平民詩人買絲翡耳》和《法國詩之象征主義與自由詩》,王統照的《夏芝的詩》等。
稍晚一些,1922 年3 月問世的《創造季刊》與1923 年5 月創刊的《創造周報》也加入到了譯介外國詩歌的行列。季刊時期,郭沫若翻譯了他稱之為“散文詩”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并作序深入闡述了少年歌德的詩學,這篇《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收錄于《創造季刊》第一期。之后,郭沫若還發表了他翻譯波斯詩人海亞姆(Omar Khayyam)的魯拜詩(Rubaiyat)《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③(譯詩一百首)》,對此,聞一多隨后發表了評論文章《莪默伽亞謨之絕句》,成仿吾也譯出一篇研究英譯本魯拜詩的《莪默伽亞謨新研究》。除了歌德與海亞姆,郭沫若還翻譯了不少雪萊的詩,《西風歌》《歡樂的精靈》《拿波里晚盤書懷》《招“不幸”辭》《轉徒(二首)》《死》《云鳥曲》《哀歌》,這些譯詩一并發表于《創造季刊》一卷四期的“雪萊紀念號”。介紹和研究雪萊的文章還有《英國浪漫派三詩人——拜倫、雪萊、箕次》、《Shelley》和《雪萊年譜》。郭沫若還翻譯了英國詩人格雷的名作《墓畔哀歌》,譯詩之外,他還翻譯了英國學者紐波特《英詩新研究》中“未來派與詩形”一章,作《未來派的詩約及其批評》一文。
此外,《晨報·副刊》也介紹過一些外國詩人和詩,主要是周作人對日本、英國和法國詩人的翻譯和介紹,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他對日本歌謠俗曲的翻譯,可以看作是輸入日本小詩的一個重要的橋梁。這時期比較特別的是《學衡》雜志。盡管《學衡》主要編輯都有英美留學背景,卻可能由于他們的與時代精神相左的立場,1922年至1924 年間創刊初期的《學衡》,并沒有成為這時期引進西方詩歌與詩學的重要途徑,更是鮮有對外國近現代詩歌的譯介。不過,1922 年第9至14 期的《學衡》上連載了吳宓的《英詩淺釋》,同時刊登了不少十九世紀英國著名詩人的畫像。數量雖少,但吳宓從中西詩學比較的視角立論,是這一時期罕見的翻譯嘗試和難得的闡釋研究。
二、現代性的尋求
綜上來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印象,與更早的梁啟超和魯迅等人相比,這時期對外國詩歌資源的需求更迫切,尋求的方向極大地擴展開來,因而引進的內容更龐雜,甚至給人以喧嘩、混亂之感。在此前的拜倫式的英雄詩人之外,出現了許多新的詩歌議題,平民的、民主的、勞動的、人格與修養的、戀愛與兩性的、進化與科學的,等等。其中“平民的”可能是這一時期譯介外國詩人的一個最常見的標簽,“平民詩人惠特曼”“國民詩人普希金”“人民詩人甫祿斯特(Frost)”“平民詩人買絲翡耳(Masefield)”等。然而,種種議題其實仍然承繼了晚清以來詩歌革命對思想與精神問題的關注。正如李思純這一時期曾指出:“近年來國人的討論,除胡適之先生略及于形式方面外,其他的討論,都偏重于詩的作用價值,及詩人的修養。盡有人主張著眼藝術方面,卻于詩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論。”[10]
比如田漢對惠特曼的介紹和翻譯。介紹惠特曼時田漢首先討論的問題是“美國精神與民主主義”,在他看來,惠特曼的詩與“作詩法”和《佩文韻府》無關,而只為“發皇美國精神”“鼓吹民主主義”。田漢還直言之所以紀念惠特曼,首要是由于其贊頌的“美國精神”和“民主主義”:
我們因為我們的‘中國精神’(Chung-Hwa?ism)——就是平和、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還沒有十分發生,就要紀念惠特曼,把他所高歌的美國精神(Americanism)做我們的借鏡。
我們中國少年所確信能夠救“少年中國”的就只有“民主主義”一服藥,所以我們要紀念百年前高唱“民主主義”的惠特曼的出生,而且恰在“大戰告終,民主勝利”的時候,紀念他的意義尤深。[11]
在介紹惠特曼時,田漢所翻譯的兩首惠特曼的詩,也都緊扣了“美國精神”與“民主主義”。比如《太久太久了,美利堅》一首,惠特曼以昂揚的氣魄呼喚祖國在痛苦中學習、與厄運搏斗,典型地體現出他詩歌中從不退卻、永遠無畏的精神。哈羅德·布魯姆稱惠特曼是“寫出了時代氛圍的詩人”[12],如果說惠特曼的時代可以用國家精神與民主思想來代表,那么田漢也許是想把它們移植到五四時期的中國。
又比如對泰戈爾的翻譯和介紹,“哲思”往往成為了關注的中心。張聞天的《太戈爾之“詩與哲學”觀》一文中開篇即說:“太戈爾是大詩人,也是大哲學家,他的詩就含有他的哲學,他的哲學也就是他的詩。”[13]王統照在《太戈爾的思想與其詩歌的表象》中宣布:“思想為詩歌的源泉。偉大的詩歌即為偉大哲學的表象。”[14]另一位泰戈爾的譯者黃仲蘇,在譯序中頗費筆墨地對泰戈爾的哲學思想概括了一番,還在《太戈爾傳》中直接稱為泰戈爾擅長“以極優美的寫詩之文筆為最玄妙的哲理之討論”的“詩哲”,認為其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兩方個面是“生之現實”的樂觀精神以及“鼓吹人道主義”[15]。
與之相似,這時期對波斯詩人海亞姆的譯介也強調詩人的哲學思想。最早發表了海亞姆譯詩的應該是胡適,他在介紹詩人的小序中說:“這首小詩的原著者Omar Khayyam 乃是波斯國人,他的數理和天文學是波斯文明史上的一種光榮。他不但是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詩人。”[16]另一位海亞姆的重要譯者郭沫若也不僅僅將其視為詩人,1922 年郭沫若翻譯并出版了《魯拜集》,其所作序引《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前一部分“讀Rubaiyat 后之感想”,討論的盡是宇宙觀與詩人的人生哲學。不僅介紹海亞姆和《魯拜集》是這樣,郭沫若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言中對歌德及其詩歌的引介也是如此,強調的主要是歌德的“狂飆突進時代”的性格和泛神思想。對此,也有人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聞一多在讀過“郭君底那洋洋大篇的讀Rubaiyat 后之感想”之后,提醒讀者:莪默詩歌的價值在于其詩本身的價值,在其藝術而不在其哲學。他指出:“讀詩底目的在求得審美的快感。讀莪默而專見其哲學,不是真能鑒賞文藝者,也可說是不配讀莪默者。因為鑒賞藝術非和現實隔絕不可,故嚴格講求,讀莪默就本來不應該想到什么哲學問題,或倫理問題。”[17]
然而,聞一多所批評的,正是那一時期接受和引進外國詩歌資源的主要情形。情形之普遍,以至于不僅僅是像泰戈爾、海亞姆這樣以哲思而聞名的詩人,即令是引介丁尼生、勃朗寧這樣以運用語言見長的詩人,關注的重心也不免還是在“思想”上。胡愈之就曾在介紹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時,將“尋求真理”或者說“思想家的態度”概括為19 世紀英國詩壇的一個主要傾向,而“這一派的代表詩人要算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和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丁尼生的詩是平明暢達,白朗寧的詩是深奧曲折,但注重思想不注重藝術,兩個人確實完全一致。換句話說,他們是以思想家的態度來作詩的”。[18]其實,我們單從題目上就能感到這時期對于思想精神的偏重,如《英國詩人勃來克的思想》《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泰戈兒的思想與其詩歌的表象》《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而其他一般性的介紹的文章也都是從思想、精神立論的。這里潛在的觀念是,倘若不首先了解一個詩人或流派的精神理想與思想主張,就無法認識和欣賞他(們)的詩,又或者可以這樣說,對于詩歌來說,“人”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詩人,技巧、形式等其他的一切都是末端的。
這其實仍然是浪漫主義的詩歌觀念,只不過從此前求生存、求反抗的民族情緒轉化為了對自由和自我的體認與追求。崇尚自由與自我,差不多是五四時期一切新文學和新文化的基本品格,在對詩的理解與認識上,則同時落實為表現內容與呈現形式上的自由,于是成就了一個自由詩獨領風騷的年代。《詩》月刊的主要編輯之一劉延陵就曾以“自由的精神”作為討論新詩的“結論”:
把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兩個特點總括言之,一則可說新詩的精神乃是自由的精神,因為形式方面的不死守規定的韻律是尊尚自由,內容方面的取題不加限制也是尊尚自由。再則新詩的精神可說是求適合于現代求適合于現實的精神,因為形式方面的用現代語用日常所用之語是求合于現代,內容方面的求切近人生也是求合于現代咧。[19]
“自由的精神”不僅是詩中,而是一切近代藝術的共同精神,是“近代與現代的精神”,是“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基于這樣的對詩之自由的理解,“自我”得到了最大的伸張,如朱自清所說,“這是發現個人、發現自我的時代”[20]。“表達自己”甚至在詩歌翻譯中也是一樣,郭沫若在他譯雪萊的序言中說:“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21]新的、現代的詩歌就這樣地被理解為了自由與自我之詩,就連不是那么激進的俞平伯也要立場鮮明地為詩的自由和詩人的自我進行辯護:“我對于作詩第一個信念,是‘自由’。詩的動機只是很原始的沖動,依觀念底自由聯合,發抒為詞句篇章。我相信詩是個性底自我——個人底心靈底綜和——一種在語言文字上的表現,并且沒條件沒限制的表現。”[22]
這種對于自由詩的認同其實根源于五四時期解除歷史負重、關心當下與個人、創造未來的強烈需求。誠如有學者所說,“自由詩是在一個沒有歷史重負的天才詩人手中得到最充分的實踐并產生廣泛影響的。惠特曼作為自由詩之父,最大的特點是把詩歌的夢想與歷史的夢想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詩歌中的世界不是依據歷史而是需要依據未來才能闡述的世界”[23]。這樣一來,“自由詩的始祖”惠特曼也就被視為了打破桎梏、放眼未來的理想化身。從形式的解放看,惠特曼的詩為當時的新詩提供了理論參照與創作范式;從個性的解放看,惠特曼的詩有對自由、民主、平民以及勞動等大眾社會的關注,這都與當時中國詩歌以及中國社會的現實需求相吻合,或者用郭沫若的話說,“與五四時代的暴飚突進的精神十分合拍”[24]。作為這一時期對中國詩歌發生了絕大影響的詩人,惠特曼的詩歌和他的思想幾乎出現于這一時期每一個重要的詩人和研究者的筆下,最大的影響也許是郭沫若,稍后的徐志摩、聞一多以及艾青等重要的中國新詩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惠特曼及其自由體詩的影響。
然而,人們在理解西方自由詩或者說在認識詩之自由的問題上,常常存在一個前文所提到的特征,即學習和認識西方詩歌與尋求和理解現代性往往成為了一回事,也就是說,對作為詩歌體式的自由詩的認識和接受,并存著對作為現代概念的個人、個性等問題的理解和體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更容易明白在這一時期何以“平民詩人”的稱號備受推崇,何以那些抒寫勞動的詩與詩人備受關注。那些取材平凡、取自現代生活的詩歌,那些肯定尋常、歌頌“神圣的常人”的詩人,不僅打破了舊詩“非神奇的、驚人的、異常的事實不能作詩的信條”,更符合、寄托了新一代年輕詩人尋求重塑詩歌、重塑社會與自我的愿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深受青年喜愛的《三葉集》,以及有關詩與戀愛、詩與自然、詩與科學等議題的討論。
三、原理與方法的引進
這一時期引進和借鑒外國詩歌資源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對詩學原理及研究方法的重視。從白話可以寫詩起,關心詩歌的人們無論持何種立場,都盡力援引各式觀念與理論的資源,呼吁者為求得“白話詩”或“新詩”的合法性,穩健者力圖糾正變革所帶來的對于詩歌認識的混亂。雖然意圖上的差異常常顯出不可調和的分歧,但在尋求和學習外國詩歌觀念與研究方法上,兩方都有各自的貢獻。
如果說“新詩”運動在初期所受到的外國影響“多半是無意識的接收”[25],那么到了1923 年前后,對于外國詩歌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引進,除了研究的意圖,還明確地致力于改變傳統詩歌與文學的觀念,甚至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這項工作。從前文所列舉的譯介情形看,初期譯介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學介紹”,如梁實秋所說,這些介紹主要是抄錄作者傳略、列出作品,再加以注釋,“他們研究外國文學是采取欣賞的態度,沒有目標,沒有計劃,沒有師承,他們像海上的漂泊者一樣,隨著風浪的飄送……”[26]。而對于一向注重批評和原理譯介的文學研究會來說,這項工作同時具有研究和培養讀者的雙重意義。《文學旬刊》改革后,時任主編的鄭振鐸曾指出讀者鑒賞力的薄弱是作家與讀者社會間的障壁,若是新詩只供少數人閱讀,新詩運動自然也要宣告破產,因而培養讀者似乎是更重要的任務。1923年鄭振鐸接手《小說月報》,更有意將“概論”與“原理”的部分“大加擴充”,旨在彌補“中國讀者社會文學常識的缺乏”[27]。在他看來,包括詩歌觀念在內的一切傳統的文學觀都需徹底的改革,因為讀者所持有的舊觀念不破,對于新詩與新文學就不免要持反對和誤解的態度,他舉例說:
譬如他們先存一個凡是詩必是五七言的,或必是協韻的傳統觀念在心中,則對于現在的新詩,必定要反對要攻擊了。……這是何等不幸的事!但我們要打翻這種舊的文藝觀念,一方面固然要把什么是文學,什么是詩,以及其它等等的文學原理介紹進來,一方面卻更要指出舊的文學的真面目與弊病之所在,把他們所崇信的傳統的信條,都一個個的打翻了。[28]
在此意圖背景下,這一時期陸續出現了傅東華、金兆林翻譯勃利司·潘萊的《詩之研究》、林孖翻譯埃德加·坡的《詩的原理》、希和翻譯莫爾頓(R. G. Moulton)的《論詩的根本概念與功能》,以及王希和參考大量西方詩學論著而寫作的《西洋詩學淺說》和《詩學原理》。
具體地看,詩學觀念上的改變主要是傳統的“載道”“無邪”以及“詩必有韻”的思想被徹底否定或動搖了,取而代之的是對美與情感的推崇。沖擊傳統“載道”觀念最有力的,無疑是“為詩而詩”這一詩學觀念的引進。埃德加·坡的這一重要的詩學主張曾深刻影響了歐洲文壇,尤其是啟發了波德萊爾、馬拉美等人所代表的法國象征主義詩學。坡在《詩的原理》中指出只有“美”是詩的本分,認為“教訓詩”是一個“絕不可容讓底的邪說”,而且“為害于詩底文學有過于全文學底仇敵聯盟之勢力”,所以他提出:
若此刻把我們作詩底意說出來,說我們止為詩而作詩,那么沒有別的止得被認為根本上不配也不會作詩罷了。……察一察自己底心靈,在那里便要找見一首詩,是時間沒有而且不能有比它還高尚貴重的詩,這就是詩其自(the poem perse),這詩是首詩并不是別的——這首詩是因其為詩而作底。[29]
坡進而將“真”與“美”的觀念對立,明確地劃分了“純智”(Pure Intellect)、“興味”(Taste)和“道德意識”(Moral Sense)的邊界,認為“純智”與“真理”有關系,“興味”與“美”有關,而“道德意識”只與“本分義務”有關。在坡看來,只有“美”才是詩歌真正的元素,因為“在人心靈底深處有種永世不朽的本能,就是美底意識。”此外,坡所主張的好詩不能過長的觀點也為當時小詩和短詩的流行提供了理論依據。
希和所譯的《論詩的根本概念與功能》同樣討論了詩與道德的問題。這一部分是譯自莫爾頓所著的《近代文學批評》中第四章《傳統研究的混亂與現代研究的重建》中的第一節。在這一部分中,莫爾頓與以近代文學批評的眼光指出,藝術與道德的沖突長久以來持續存在,然而兩者的范圍卻可以清楚分開,對此他提出了三點看法:
1.“藝術淺視道德”一語不知驚動了多少人,其實此語很有完美的意義。……我們絕不應設想表現專制魔王的音樂當如何含有道德上的意味;果如是,便非藝術了。是故我們應排斥“凡欲作偉大的詩的人,他的生活本身應成一首詩”的格言。
2.有時道德侵入藝術氛圍,就是我們所稱的教訓目的。此種藝術以道德為主要思想,是為道德的作品;形雖藝術,實則非真藝術。批評此種藝術當用道德來衡量,藝術本身是不負責任的。
3.反之,藝術侵入道德范圍時,便無良妙的目的了。……我們與此當歸咎藝術家,蓋藝術家以藝術行其不義,是不應該的,藝術本身固無罪也。[30]
在討論詩歌題材的時候莫爾頓也談到了詩與道德的問題,認為任何題材無論是否道德、是善或惡,“都能夠構成最高格的詩的材料”,重點在于處理這些題材的方法。
對比之下,依仗傳統詩學資源的人們在談論詩歌時,即使是主張“緣情”的一方,也還是念念不忘“溫柔敦厚”的品格,更不要說持功利性觀念的一方了。比如,同一時期潘大道的詩論,雖然在討論趣味等問題上有些不俗的見解,但卻一方面承認詩歌應合于“人類美的要求”,另一方面反復強調“詩之為教,溫柔敦厚”,甚至將“溫柔敦厚”視為“詩的精神”、“詩的宗旨”[31]。又如,吳宓在分析英國女詩人萊茨(Winifred M.Letts)的《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一詩時批評歐戰詩歌“失溫柔敦厚之旨”,而稱贊萊茨的這首詩“純用詩人溫柔敦厚之心,悱惻纏綿之意”[32]。
差不多在林孖譯出《詩的原理》的同時,坡的詩歌名作《烏鴉》也被翻譯出來,刊于《文學周報》,還引起了一番討論④。其實,坡所代表的“為詩而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詩學觀念此前已經有不少翻譯和介紹,例如周作人介紹波德萊爾時稱其為“頹廢派文人的始祖”[33]。二十年代后期“為詩而詩”的詩學觀念日漸傳播,一度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詩學與美學的趣味,“為詩而詩”的“純詩”觀念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擁護者,穆木天還明確提出了“純粹詩歌”(The Pure Poetry)的詩學主張,不僅如此,一些此前持有“平民的”、“為人生的”詩學觀念的詩人如俞平伯、周作人也轉向了“純詩”的觀念。
此外,韻律問題也是這一時期引介西方詩學的焦點。通過引進西方的散文詩、自由詩等非格律詩體,既打破了“無韻非詩”的成見,又從建設的方面為“新詩”提供“增多詩體”的參照,而且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新詩運動以來,有關詩歌散文化問題討論的一種延續。鄭振鐸還曾專門作《論散文詩》討論詩與散文和韻文的關系,在援引了從亞里士多德到埃德加·坡等十幾種西方詩歌定義后,他主張詩的特質不在于有韻無韻,而在于是否有“詩的本質”,有詩的本質而用散文來表現的是“詩”,沒有詩的本質而用韻文來表現的,決不是“詩”。至于“詩的本質”,鄭振鐸則是借鑒了溫徹斯特在《文學評論之原理》中所提出的四要素,即情緒、想象、思想和形式,認為只要具有這四點詩的本質,散文還是韻文并沒有什么分別,因為無論形式怎樣變都還是“詩”。最后,他援引莫爾頓的觀點總結道:“‘古代的詩歌大部分是韻文,近代的詩歌大部分是散文。’這確是極辯顯現象。”[34]與之類似的,李思純在《詩體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見》中將西方詩分為“律文詩體”與“非律文詩”兩大類,進而比較全面地介紹各式詩體。“律文詩體”如“無定韻律文詩(blank-verse)”“抒情詩(ode)”“諷刺體詩(satire)”“十四行詩(sonnet)”“十二言詩(alexan?drine)”等,“非律文詩”則有“散文詩(prose-poem)”與“自由句(vers libre)”。值得注意的是,李思純不止單純地輸入西方詩學的基本概念,還嘗試進行中西的比較闡釋,比如在介紹西方戲劇詩(Dramatic poem)時與中國詩體式相聯系,認為傳統詞曲其實就是“中國的‘戲劇詩’”,都有戲劇詩的意味。
在譯介西方詩學知識的同時又自覺進行中西詩學比較的,是吳宓。不同于文學研究會致力于理論和原理的輸入,吳宓更重視引進西方詩學的研究方法,即認為逐字逐句不厭繁瑣的闡釋才是研讀詩歌的妙法。在對Letts,Herrick 和Arnold三人詩歌的細讀中,吳宓將英詩的音節(sall?able)、分段(即章節stanza)以及葉韻(rhyme)、首韻(alliteration)等押韻方式和輕重、抑揚等音律形式靈活地加以介紹。當然,細讀闡釋的過程最難得的還是貢獻了讀詩的方法,對欣賞詩的藝術和技巧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比如《英詩淺釋》中分析《挽歌》一詩:“原文第三首第一二句,以歌場回旋之舞態,比生涯流轉之情形。衣裙蹁躚,笙管吹沸,繁華縟麗,擾攘紛紜。”另外,同一時期,吳宓對于外國詩歌的韻律問題也有獨到的論述,他在《詩學總論》中曾將拉丁、英文以及中文詩歌在音律方面的特征相比較,進而提出:
然吾國以平仄為詩之音律,利用相間相重之法,以成時間中極有規則之節奏,此則與希臘拉丁及英國之詩,均全相同,可謂不謀而合也已。茲更列比較表如下:
一、希臘拉丁詩之音律,以長音及短音之部分,相重相間而成。
二、英國詩之音律,以重讀及輕讀之部分,相重相間而成。以音波波幅之寬狹定之。
三、吾國詩之音律,以仄(高)聲及平(低)聲字相重相間而成。以音波振動數之多寡定之。[35]
以上發表于1922 年9 月的《學衡》,應該說,吳宓率先運用比較詩學的研究方法,開放了中國詩學比較的研究視野,但或許囿于年代立場的局限,略顯突兀地提出中文詩與拉丁詩和英文詩相似以及中文詩之用韻有著千年歷史經驗所以不可強廢的結論,而不像稍后的葉公超和朱光潛那樣,能更細致地辨認中文詩與其他語言在節奏上的差異,從而為現代漢語詩歌提供節奏上可行的建議及其用韻的意義。
四、結 語
胡適發起的白話寫詩運動,將中國詩歌的現代性尋求帶入了新的紀元。現代漢語詩歌,作為一種現代漢語的實踐,也由此介入國家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20 世紀初,中西思想資源的勢力在新一代知識階層中發生了變化。不同于此前嚴復、梁啟超一代,雖引進西方資源卻仍然以漢語思想資源為主導,而新詩與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們則開始以外來的知識資源逐步取而代之。從詩學層面看,依仗了世界風潮,或者說“西洋血脈與精神”,中國詩歌的確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拓展了表意的自由,開放了詩體的可能性。不僅如此,更具建設性的貢獻是詩學觀念的更新。對于西方詩學原理與問題的關注,促進了人們對于詩的概念、技巧、功能和理想等認識的轉變,配合論證了“新詩”的合法性,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立場以返觀傳統詩歌,從而可能對中西詩歌的比較與融合展開更深的探索。
時代賦予的局限性總會在其他方面有所補償,反之亦然。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譯介活動與研究的展開,盡管與其他領域一樣,對西方詩歌、文學的思想觀念存在過度信任和重視的情況,但外國詩歌資源的輸入和引進,不論是積極的、激進的,還是穩健的、保守的,無疑為修正舊觀念、建設新詩學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與此同時,各方尋求者們各自努力于詩歌觀念與理論建設,為現代漢語詩歌擬定了一個理論與創作齊頭并進的基調。
注釋:
① 《歌德詩中所表現的思想》一文中所錄歌德詩歌,《天黎孫》一首由田漢翻譯,其余《即全》《東西詩集》《遺言》《暮色垂空》《神性》《Ganymed》《遺亞呂》《掘寶者》《藝術家的夕暮之歌》《寄厚意之人》《藝術家之歌》為郭沫若翻譯。
②“太戈爾”今譯為“泰戈爾”。
③“莪默伽亞謨”今譯為“奧瑪·海亞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