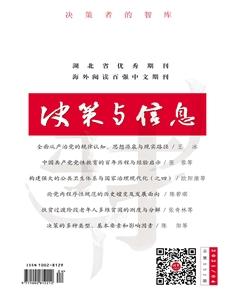強化綜合協調能力是提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能力的關鍵
馮占春
關于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能力的提升,結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經驗,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重新審視。
一、相關背景和綜合協調的意義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說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社會后,遇到的非常大的一個挑戰。疫情什么時候可以完全結束,會演變到什么程度,現在還很難預測。之前有人預測很可能像“鐘擺”一樣,夏天跑到南半球,冬天又會再回來。但是自2020年6月北京新發地一度成為國內本土感染新的發生地,雖然當時北京的氣溫已達到35度,結果還是發生了。原來很多人猜想的鐘擺式發生被證實是錯的,病毒可能一年四季都不會離開。另外,這一次的病毒和以往發現的病毒不太一樣,一些人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個“杰作”,懷疑其是人造產生。究竟怎樣產生的,這是科學問題,科學問題還是應由科學家來溯源揭秘。從新冠肺炎病毒的生命力來說,首先,它的潛伏期不短不長,據現有研究數據表明,其可以潛伏14天甚至更長,而其在潛伏期就已經有了傳染性,這樣就增加了它的傳染概率。其次,它的病死率不高不低,這樣就導致感染者可以感染更多的人;另外,從傳播途徑來看,之前的結論是主要通過飛沫和接觸傳染,后來發現通過污水、糞便也可能傳播。北京新發地疫情的暴發,經調查無論是從加工三文魚的砧板,到三文魚的口腔,都檢測出了新冠肺炎病毒;另外,從變異性來看,近半年來收集的毒株已經全部報告給世界衛生組織,基本上都被認為與歐洲的病毒高度同源,其毒株和武漢早期的不太一樣,這種差異使傳染性進一步增加。重慶醫科大學研究了重慶幾十位有癥狀和無癥狀感染者,發現這些人體內的抗體持續的時間最長的有三個月。感染病毒后,抗體會使人體獲得免疫能力。研制新冠肺炎疫苗也是通過激發人體自身的免疫能力,新冠肺炎病毒還兼有流感和肝病毒的某些特性。所以就這類傳染病而言,由于現代生物技術主要通過疫苗來幫助人體產生抗體,新冠肺炎病毒在今后有可能會是可控的常態化存在。
目前,在還沒有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前,我們更多的還是采用傳統的傳染病控制原則:隔離傳染源、切割傳染途徑、保護易感人群。但是,在交通發達、經濟一體化、人們崇尚自由的時代,要做到這一點,光靠衛生系統、或者一個部門是很難長時間做到的。疫情發生前期,我們能夠應對疾病的醫務人員比較少,因為在這次疫情之前,傳染病發病率在逐漸地降低,感染科的醫生數量有限,呼吸科也僅僅是內科里面的一個科室,再加上重癥科,也沒有多少醫生,以至于到后期幾乎所有科室的醫生都加入進來。此外,包括醫療、防護物資供應等方面,都需要進行大量全面的協調,疫情前期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都與協調有關。如垃圾車拉食品事件的發生,就是綜合協調缺失的表現。另一個受人關注的亂象是前期口罩等防護物資沒有得到合理調配,后來媒體呼吁非一線醫務人員盡量不要戴N95口罩,把N95口罩和隔離服留給一線醫務人員,真正要穿隔離服都是在最危險崗位的醫護人員。在物資緊缺時就應當優先保證一線,但是誰來保證?這就是綜合協調的關鍵所在。
二、綜合協調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對中的內涵
什么叫協調?從管理學角度給它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即正確地處理組織內外各種關系,為組織正常運轉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最終保證目標的實現。
對于這次疫情來說,綜合協調首先是國際上的協調。美國在我國發生疫情時最先中斷和中國的航空聯系,結果美國隨后自己卻成為全球最重的災區。特朗普政府還一度污蔑稱這個病毒叫“武漢病毒”,而如今,包括歐洲的病毒和美國的病毒在內是怎么發生的都還不太清楚。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團結是抗疫的最有利武器,我們要形成命運共同體、生命共同體,這就需要國際層面的協調。其次是國家內部的協調,我國有一個名詞叫做“聯防聯控”,中央建立了聯防聯控機制,它實質上是32家部委等單位組成的綜合協調平臺,所以聯防聯控的本質就是綜合協調。
簡單回顧這次疫情中國際合作的情況可以發現,新冠肺炎帶來了很多混亂,包括美國退出WHO等行為。但是,后疫情時代,通過這次事件也有可能促進國際社會在疫情防控方面的進一步合作。國內方面,現在要確保的仍是疫情控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兼顧,這也是需要協調的。另外,對衛生體系來說,一方面要考慮包括中央、省、市、縣、街道(鄉鎮)、社區在內的縱向協調,另一方面也要考慮部門之間橫向的協調。
三、疫后應急體系建設策略的建議
從具體的策略建議來說,首先,還是要鞏固國務院提出來的聯防聯控機制。可以說聯防聯控機制是武漢在疫情暴發以后,經過前期的混亂,通過反思建立起來的協調機制,這個是非常正確的,要堅持下去。就湖北來說,應該建立一個應急管理體制改革示范區,武漢這次是重災區,同時也具有比較好的條件。國家應該支持湖北武漢建立一個應急管理體制改革示范區,形成一個跨部門、跨區域的綜合協調系統,包括醫療衛生、物資生產供應等,形成完整的體系。
其次,加強醫療衛生體系整合。2020年6月20日北京4家醫院被國家衛健委通報院內感染防范工作不到位。疫情前期,武漢一些醫院處于風口浪尖,院內感染比較多,從專業的角度看,當時對新發傳染病認識不清,加上一些管理問題,出現感染的情況情有可原。但是北京這4家醫院,特別是在有武漢和當前國內外的經驗教訓的背景下,作為國家頂級的醫院還出現這類問題,也提醒我們要進一步思考應該建立何種醫療衛生體系。湖北出臺了建設公共衛生體系的方案,要加強疾控系統建設,這其中一定要注意醫院也是公共衛生體系的一個有效組成部分這一關鍵點。這次疫情在武漢發生后,包括金銀潭醫院、武漢中心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在內,出鏡率都很高。因為病人感染以后,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醫院,所以醫院是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前哨陣地,如果把醫院和公共衛生體系完全隔離開就大錯特錯。而怎么樣使這兩個體系有機融合起來,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如果公共衛生和醫療,還是“兩張皮”,缺乏有機的整合和協調,最后再碰到類似問題大概還會犯。再次是物資的儲備。物資儲備不一定是現成物質的儲備,同樣要思考能否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儲備制度,將生產、流通、使用環節都協調好。
最后,這次武漢之所以能夠戰勝疫情,筆者認為最關鍵的還是社區。光靠醫院的救治,病人是越救越多,最終我們還是要借助社區阻斷傳染鏈條。在封城前期,我們并沒有封住病人和社區,病人和疑似病人四處奔波就醫,家里又沒有隔離條件,就形成了一個“死結”。在這種情況下,社區動員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鐘南山院士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他當時眼睛含著熱淚,為什么含著熱淚?因為武漢當時冒了巨大的風險,而社會動員最終在我們戰勝疫情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醫藥衛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