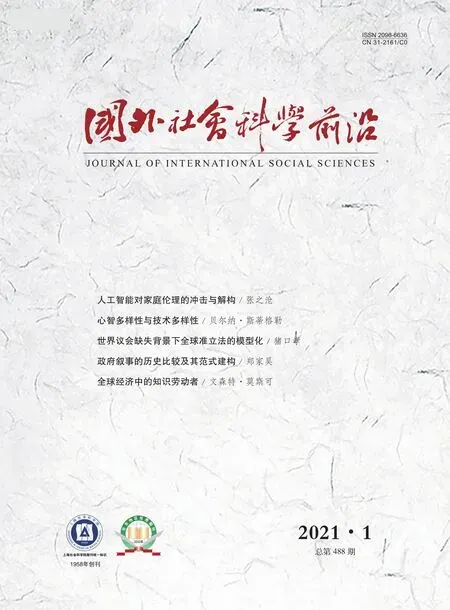心智多樣性與技術多樣性:建立在理論計算機科學基礎上的新經濟的諸要素*
貝爾納·斯蒂格勒/文 陳明寬/譯
[譯者按] 斯蒂格勒認為,我們這個數字化時代正是充滿技術所釋放的毒性的人類世時代,而且正處于其毒性最大化的時期。他的這個論斷正在為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影響全球各個國家的新冠疫情所強化。而當今人類世之所以出現如此的局面,是因為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過于相信科學技術所致。在斯蒂格勒看來,人類的進化是體外進化的模式,在這個進化過程中,人類的生存會不斷地更加依賴外在于其軀體的技術和技術物體,也即斯蒂格勒所說的第三滯留。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以人工智能的諸種形式為偽裝的數字技術,以異常強大的力量將人類軀體內器官的感知、知性、理性等心智功能不斷地外化于人類軀體之外的所謂高新技術物之中。這些技術物如今已到處雷同泛濫,它們是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的最新形式。于是,雷同的提示記憶的方式導致了雷同的心智思維方式,而雷同的心智思維方式導致了系統性的愚蠢,導致了人類熵在全球范圍內的急速增長。在此意義上,斯蒂格勒才說,人類世已經達到其毒性最大化的時期。當然,斯蒂格勒并非是完全貶斥技術的人,因為在他的理論中,技術既是毒藥也是解藥。當今數字化的科學技術導致了人類世毒性的最大化,但要化解這種毒性卻依然需要依賴于這些數字科技。這也就是斯蒂格勒為什么在這里要重新反思理論計算機科學之基礎的原因。只有主動地反思科學技術才能構建心智的多樣性,才能認識到科學技術并不是唯一的技術形式,進而才能保護并發展技術的多樣性。斯蒂格勒似乎將這場疫情看作是能夠促使人類反思當下人類世狀態的契機。可是,他本人卻又對當下人類世的諸種狀況非常地失望,他在這個大流行病的2020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哲學家并非一定是相信自己哲學理論的人,也并非一定是勇于踐行自身哲學理論的人。蘇格拉底相信并踐行了自己的哲學理論。那么,于斯蒂格勒而言,其為是耶?其為非耶?
一、“關于技術之追問”與對真理的考驗
無論我們是誰,今天,我們所有人都要面對“關于技術之追問”①包括(甚至是經常)對此問題的否認以及默認其存在,此種否認和默認之態度的存在正是“關于技術之追問”的問題處于極端緊急狀態下的征兆。②斯蒂格勒最近幾年思考的關于技術的問題,許多是對海德格爾當年所思考的“技術座架”問題的回應。這里斯蒂格勒使用了“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的表達,對應于海德格爾同名的一篇論文,即“Fragenach der Technik”。中譯版本可參閱海德格爾《技術的追問》(載《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譯者注的問題,并且現在(2020 年3 月29 日),我們必須在因新冠疫情而不能外出的情況下來面對這個問題。隔離迫使我們直面我們的生存方式:我們雖然能夠獨處,但網絡卻又使我們彼此聯系或者被迫聯系起來。疫情似乎以某種獨特的方式開啟了生物圈—技術圈之病理學意義上的體外因素(exosomatic factor)的問題。而這種問題正是阿爾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所謂的“體外進化”③A.Lotka, The Law of Evolution as a Maximal Principle, Human Biology, vol.17(3), 1945, p.192.意義上的體外化。
從這種情況來看,我們需要非常仔細地重讀喬治·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的《正常與病態》(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這樣,我們才能最終意識到,“生命政治學”歸根到底是一種技術政治學。這是一種心智生命(noetic life)的政治學,當然也是動物、植物、細菌和病毒等生命的政治學,它能夠形成一種非常獨特的群島(archipelago)結構。在“數字研究網絡”協會(The Digital Studies Network)中,我們將其稱為“生命有機體的群島”(the archipelago of the living)。
計算技術將我們的生活方式具體化在各種應用程序、服務、數據庫、軟件和算法中。而依靠計算技術所建立的一些主要平臺實際上只掌握在兩個國家手中。在此次疫情之前,我們所有人之所以都或多或少遭遇著“關于技術之追問”(Fragenach der Technik)的問題,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計算技術已經顛覆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這種(西蒙棟意義上的)具體化導致一種技術—地理聯合環境①G.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C. Malaspina and J. Rogove (Trans.), Minneapolis:Univocal, 2017, pp.57-58.②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D. Ros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6, p.22.③聯合環境這一概念是西蒙棟技術哲學中所使用的概念。西蒙棟認為,人類所生活的環境并非是只能使自身去適應的自然環境,人類也可以主動地營造使自身更舒適地生存的人工環境或者技術環境。而這兩種環境聯合起來的環境就是聯合環境。參見G.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2017, p.49。——譯者注的建立。構成這種聯合環境的要素已經不是西蒙棟所研究的甘巴爾渦輪(Guimbal turbine)運行環境中的潮汐水域,而是由個體所供給的“人力資源”。個體成為了“信息有機體”(inforgs)④“ inforgs”,即的“informational organisms”的縮寫,參見L. Floridi, Marketing as Control of Human Interfaces and Its Political Exploitatio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32(3), 2019, p.379。——譯者注,進而無數個這樣的個體就構成了覆蓋在地球之上的外在化的網絡有機體(reticulated planetary exorganism)。但這種有機體是極度脆弱且具有危險的依附性。
未來,計算技術可能會對生存方式(但也不只是生活方式)做出更深一步的改變。對計算技術的功能、缺點、極限和危險的重新思考,必須成為我們要討論的“希望后疫情世界的自然和文化會是什么樣的”這一問題的中心。同樣地,這也是后數據經濟世界的中心問題。數據經濟建立在對機器的使用之上,并且正是通過機器,這種經濟才能夠利用服務于機器的人。但數據經濟的發展正急劇地偏向它的深淵:熵。
二、病毒學與毒性:新的爭論
在過去的27 年中,因普遍的網絡化——根據阿梅利(Sophie Amsili)和莫雄(Florian Maussion)提供的數據,截止2019 年2 月,網絡的普及已涉及44 億人⑤S. Amsili and F. Maussion, L’usage d’Internet dans le monde in cinq chiffres, Les Echos, 9 Feb. 2019.——所帶來這種改變引發了一系列無法化解的難題,如今又加上了病毒學的新難題。這些因而也成了有關毒性(virulence)的問題。毒性這個詞從拉丁文“virulentus”而來,其最初的意思是“分泌毒液的、具有毒性的”。
正是從這個視角,我們應該閱讀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對他的朋友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回應,阿甘本指責各國使用“與正常流感沒有太大差別的東西”作為維持例外狀態的借口。對此南希回應道:
例外事實上成了世界的規則。在這樣的世界中,各種技術之間的相互連接(各種移植和傳輸)正達到一種迄今為止伴隨著人口增長而來的前所未有的強度。同樣,在富裕國家,人口增長伴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因此,老年人數量就會增長,總體上處于風險中的人口也會增長。
我們必須小心,不要擊中錯誤的目標:整個文明都處在問題之中,這是不用懷疑的。有一種病毒性的例外狀態,即疫情;它同時是生物學的、信息論的和文化上的例外狀態。政府只是冷酷嚴苛的執行者,對它們的攻擊指責更像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慣用策略,而不是什么政治反應。
如果真有事實上的例外狀態的話,南希對阿甘本的回應就是“一種病毒性的例外狀態”。考慮到“關于技術之追問”以及技術與生命之間的關系,以下表述就包含著對真理的考驗。我想在這里展示一下:
(1)尤其是疫情之后,對思想的挑戰將總會是如何將技術(科技)所引起的難題(problems)轉化為關于技術之追問(questions),即,將技術變為思想最切近的對象。
(2)事實上,例外狀態的問題是本質的,同時也是中心的和邊緣的。這個問題不僅要與卡爾·施密特、瓦爾特·本雅明、馬丁·海德格爾和米歇爾·福柯等人思想放在一起考慮,而且要與弗拉基米爾·維爾納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喬治·康吉萊姆和阿爾弗雷德·洛特卡等人的思想放在一起考慮;并且要將例外狀態的問題當作熵、負熵和反熵(anti-entropy)之關系的問題來思考。
(3)至于就生命的心智形式而言,必須從洛特卡所發展的體外化視角出發,通過負人類學(neganthropology)的視野重新反思人類之現狀,將反熵的問題轉換為反人類熵(anti-antropy)①“antropy”是斯蒂格勒發明的一個概念,由“anthropos”(人類)和“entropy”(熵)這兩個單詞構成,因此我們這里將其譯為“人類熵”。人類熵特指人類的愚蠢程度,相應地,反人類熵則是指人類的明智程度。斯蒂格勒在《休克狀態:21 世紀的愚蠢與知識》(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5)一書中專門討論了“愚蠢”問題。——譯者注的問題。
(4)根本上,這些問題將會為建立在宇宙技術之技術全球化尺度(technospheric scale)上的政治經濟學和由此產生的批判,構建新基礎。當然,我們必須通過重新評估計算機科學和認知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來探索這些概念上和理念上的問題的意義。新自由主義如今已經變成了極端的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論。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就要求從基礎科學、哲學、經濟學和法學等學科出發,為理論計算機科學建立新的基礎,以便更好地去理解技術全球化時代(technospheric era)網絡社會中的機器計算與自動化計算之功能的反人類熵和負人類學概念。
當南希說,“政府只是冷酷嚴苛的執行者,對它們的攻擊指責更像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慣用策略,而不是什么政治反應”,但沒有對他所說的“病毒性的例外狀態”做進一步解釋時,我不能確定我是否完全抓住了南希的觀點。這顯然不是“攻擊指責”任何人的問題(正如尼采在很多年前警告我們的)。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種藥學之毒性的危機,同樣也是體外化之病毒學的危機,這些當然不能使我們擺脫衰退。而衰退趨勢燃起了民眾對作為替罪羊的政府的憤恨之情,這憤恨之中隱含著潛在的(蓄意謀殺的)“罪惡”。我們只有通過塑造新的批判武器才能對抗這種“罪惡”。這種新的批判武器既包含科學權力、技術權力,更是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批判武器,因而也是政府以及那些服務政府的人直接或間接的批判武器。
三、以“關懷、沉思”(pansements)①“ pansements”是“panser”的名詞形式。“panser”是法語詞,意為“包扎,敷藥,(為馬匹)梳理”,其詞根為“panse”,也可以寫作“pansée”。斯蒂格勒通過考證后認為,“panser”在18 世紀之前一直寫作“penser”,后者具有“去思考,去關懷、去照料”的意思。斯蒂格勒在此使用“panser”一詞,是為了說明“在精神上進行思考”與“在身體上進行照料”是一致的,這兩種“關懷、照料”行為具有相同的起源。這也是斯蒂格勒以“What is Called Caring?”(見B.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pp.188-270)為標題作文來回應海德格爾的“What is Called Thinking?”(中譯文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中的《什么叫思想?》,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第135~151 頁)一文的原因。在本論文中,我們將根據上下文具體環境,而將“panser”翻譯為“沉思”、“關懷”、“照料”,將“pansements”翻譯為“繃帶”、“包扎”、“關懷、沉思”。關于斯蒂格勒對“panser”的考證,參見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pp.214-216。——譯者注 的態度去重建理論計算機科學
問題的關鍵正在于與這種衰退趨勢做斗爭:
(1)首先,問題在于知道這種趨勢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那種聲稱可以客觀地反思新冠病毒的思想。②這是斯蒂格勒在《國民陣線之藥學》(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中所研究的問題,不過,目前還沒有被翻譯成英文。——英譯注這個問題部分地就是我所說的對心智繃帶(noetic bandages/ pansements)的關懷沉思(careful thought/pansée)。但這種心智繃帶最終總免不了被病毒所感染。③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1:L’immenseregression,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8.
(2)同時,這也是發展出一種新的政治反思的問題。無論是這些問題的上游還是下游,這種反思都會挑戰上述那些政府,并將其置于質問之中(就像任何形式的哲學思考必須總是心智理療或心智繃帶一樣)。對這些政府的挑戰和質問將伴隨對支持和操控政府的經濟權力的挑戰和質問,伴隨著對那些或近或遠、或直接或間接、既積極又消極地與這些政府團結一致的人們的挑戰和質問。
處于“消極團結”之中意味著參與進好人與壞人的“親密無間”的角色扮演中,所有的角色都要努力成為這場表演的一部分,這樣一來,就既不用改變演員,也不用改變劇本,而只需重新安排布景和舞臺。正是這種景象產生了所謂的“姿態”(postures)。
以這種方式妥協,就不再是壞人之腐敗的問題,而變成了一個非常令人苦惱的心智之藥學的問題。我們所有人都會被迫周期性地落入這樣的問題當中。因此,這種妥協就與我們每個人相關,尤其是與遵守學術原則的專業思想家相關。④妥協在此的意義是認識論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不過,要在這種妥協的不計其數的細微差別中劃定其“近”與“遠”,既是不可或缺也是漫長而又困難的,有時又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休克狀態》(States of Shock)以及隨后的一些作品中討論過這個問題。它在根本上涉及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開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討論的問題,以及對海德格爾的“座架”問題的重新闡釋。據我所知,德里達對此問題總是不可思議地保持沉默。
大體而言,學術在原則上(即在原理的層面上)具有普遍性;并且,在這種原則的名義上,即在專業的名義上,作為教授們的專業,它總是一種“信念(faith)的專業”。學術對社會(“政府”是社會的一個關鍵維度:決斷)的貢獻(原則上始于arkhē[本原、基礎]),被社會和政府所遭遇的難題所鉗制。這些難題包括總是趨向于變得空洞的普遍性難題,它因此會成為消除多樣性(diversal)的證據。這種多樣性既可以是本地的(local),也可以是邊緣的(如黃馬甲、移民,等等)。
這個社會所遭遇的難題,首先就是它作為整體以及通過它自身的矛盾行為所挑起的問題。這些矛盾行為也是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的動態矛盾。在這樣的社會中,作為“人文學科的公職人員”的學院思想家們必須要把這些難題當作既定的問題來看待。(并且,在這些既定問題出現的地方,已經根本不是重新恢復由“現代形而上學”所組成的“統治權”之形象的問題了,正如雅克·德里達的每位繼承者都傾向于以守舊和狹隘的態度所相信的:他們傾向于去做法語中所說的“躲在某人的小拇指后面”之類的事情。)
理論計算機科學已經被關懷沉思(pensée qui panse)所拋棄,尤其是被歐洲哲學,以及作為馬克思思想和精神分析的繼承者的“法國理論”所拋棄,只有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是個例外。他們已經不會去關心我們這個時代的這種特殊面相,這些問題已經遺棄給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而這些人只會躲在建立在科學與量化研究(認知主義意義上)混淆之基礎上的計算機偽科學的背后。這種事實的出現同時是由于:
(1)哲學不再實踐數學;
(2)數學已經傾向于與數學物理學合并,并通過它與一種陳舊卻專制的機制相結合。在《歐洲科學的危機》中,胡塞爾已經將這種趨勢追溯到代數化;
(3)這些受數學物理學啟發并應用于算法的數學形式已經被初級階段的、貧乏的控制論所挪用,已經被僅僅是拼湊起來的信息論所挪用,而且已經被那種消除對技術的任何思考、任何心智式的關懷沉思的對技術的使用所挪用。
于是,這種方式就取代了“關于技術之追問”。對技術的追問是我接下來要做的事。這是我與許煜(Yuk Hui)展開所謂的(如今已只剩夕陽殘照下、斷壁頹垣中的)西方文明與(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的)中國文明之間對話的一種方式。
四、體外化的資本主義階段的熵增指向與哲學工程的失敗
如果以我過去十年所發展的概念框架來分析當前的問題,我們會發現,科技引起的難題已經引發了體外化器官不同尺度上的藥學問題:基于彼此關系的不同尺度間的相移是以不同層面間的差別為前提的,這就構成了從細胞到生物圈,再到環繞生物圈的外大氣圈的不同尺度上的本地性(locality)問題。通過這種環繞著生命和人類的圓圈,就構成了技術圈(technosphere),而它們就像是一只巨大眼睛的虹膜和瞳孔。
今天,我們生存的各個維度上都因普遍的數字化而發生了改變,這種總體性自身引起了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問題。我們生存方式中那些已經完成或者正在到來的改變,似乎都正朝向一種單一的方向傾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每一天都越來越不可避免地更具有破壞性:這種單一的方向正是不斷地熵增。
數字化變革(digital change)如今已經被具體化為由網絡效應、羊群效應、因而也是由病毒式傳播(virality)——作為“模因”(memes)①在理查德·達爾文意義上。和“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②在彼得·泰爾(Peter Thiel)對這個由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提出的概念的使用意義上。——所主導的地球行星尺度上的網絡化(planetary reticulation)③G. Longo, Letter to Alan Turing,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36(6), 2019, pp.73-94.過程。日復一日,越來越讓人失望;在過去的20 年(大約自1985 年到2005 年)之中,每一天都讓人感覺看不到希望。
這些現在看來反而是已經丟失的幻想的希望,最初出現在免費軟件工程師這種有限的圈子中。這個圈子是一個以新知識產權為基礎、基于知識共享的軟件開發組織,其基本原則于1985 年左右形成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學院,它完全不同于古典勞動分工的工作模式。在亞當·斯密、馬克思和涂爾干所關注的工業勞動分工專制霸權的兩個世紀之后,只有安德烈· 高茲(André Gorz)從根本上看到了這種知識共享的軟件開發組織的新基本特征。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創建了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該基金會孕育了基于“哲學工程”(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經常使用這一術語)的權利哲學的種子。該基金會介入10 年后,這些希望越來越普遍地被萬維網的公共開發所分享——這也引發了“科技泡沫”和納斯達克的“瘋狂”投機行為。
然而,所有的這些都將被證明只是20 世紀70 年代早期最初由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④納斯達克既是一種市場指數,也是一個自動化市場的組織。1990—1993 年,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成為納斯達克主席,之后他(因金融詐騙)被判處監禁150 年。早在1971 年,麥道夫就是自動交易報價系統的創始人之一。所援助發起的自動金融化(automated financialization)運動的初步基礎。毫無疑問,麥道夫最初的那些援助促成了金融化的進程,而金融化本身又為眾所周知的“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革命”的新浪潮鋪平了道路。
有兩種“希望”開始衰落了:一是從發源于文化工業和愚蠢(Dummheit)——尤其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所說的野蠻(barbarism)⑤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mund Jephcott(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2, p.xiv.——時代的“單向度的人”的境況(阿倫特意義上)中逃脫出來的“希望”;二是從已經建立的控制論—核能時代中逃脫出來的“希望”,這個時代占用了包含在網絡去中心化與基于反饋回路和遞歸(recursivity)①我一般稱之為“再發生”(recurrence)。再發生是我所說的“特殊文本”(idiotext)的動力學原理。關于“再發生”的一般認識,參見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 Barker (Trans.),Stanford: Stanford UP, 2011, p.144;關于“特殊文本”的論述,參見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Stephen Barker(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9, p.64, p.243,以及B. Stiegler, Postface: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3. Paris: Fayard, 2018, pp.862-868。計算方法的萬維網的可編輯化(editorialization)中的潛能。當與智能手機相連通的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s)開始終結社會網絡(social web)——也即網絡2.0,并一同終結網絡(web)本身的邏輯時,所有這些“希望”就已經開始衰落,并且在事后看來,都會成為危險的幻覺。
這里讓我們來澄清一下,藝術—工業協會(Ars Industrialis association)的成立首先是以上述科技內在固有的藥學特征為前提假設的。在那些沖擊了西方(及其貨幣與市場)的線性文字文碼化(grammatization)②文碼化過程是一種文碼系統對某種連續流程離散之后,而使用其文碼標準對之進行重新表達的過程。而所謂的“文碼”(gramme)則是指包括文字、字母、基因、細胞符號、痕跡等一切可被重復引用的有限標準。典型的文碼化過程,如,離散數學中的離散化過程:將物理世界中具體事件的某些節點用數據表示,然后根據這些數據建立起這個事件的離散模型的過程。不過,斯蒂格勒所說的文碼化所涉及的范圍要大得多,線性文字文碼對口語這種連續流程的離散化,機械文碼對軀體的肌肉骨骼的連續流程的離散化等,都屬于文碼化過程中的類型。對斯蒂格勒而言,他則認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文碼化過程是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出現的,其標志是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的出現。目前對人類進化具有重要作用的文碼化過程共有三個,即:書寫技術文碼化、印刷技術文碼化和科學技術文碼化。現在我們正處在科學技術文碼化過程中的數字技術文碼化階段。關于斯蒂格勒的“文碼化”思想,參見B.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1: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B. Norman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53-59;J.Tinnell,Grammatization,Bernard Stiegler's Theory of Writing and Technology, Computers & Composition, vol.37, 2015, pp.132-146;陳明寬:《技術替補與技術文碼化——斯蒂格勒技術哲學中的文碼化思想分析》,載《自然辨證法通訊》第40 卷,2018 年,第128~134 頁。——譯者注和機械文碼化(自動機器使這一過程成為可能)過程發送之后,上述這些科技就成了文碼化過程新階段的標志。我們也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社會正是使用了中國的印刷術、航海技術和火藥等技術才可能完成自身的原始積累,正是這樣,現代西方社會才能夠將其對全球的支配力強加到正在成為一個統一的技術圈的世界上(而且,現在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去西方化的過程)。
“社會網絡”的“終結”開始于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的出現,隨后與2008 年的金融危機結合在一起,進而導致了“平臺化”(platformization)③D. Ross, Carbon and Silicon, Stiegler and the Internation Collectiv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ch.10.的迅猛加速。這些希望因此會走向幻滅,然后它們就會被自由主義或是超人主義運動大量地工具化。自由主義或者超人主義運動是定義了20 世紀末期之社會形態的撒切爾—里根保守主義革命(Thatcher-Reaganit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所引發的新自由主義的變種,此一變種通過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所說的“智能化”(smartification)④E. Morozov,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3.過程而變得具體。
五、反烏托邦與不可能性
我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不堪重負地(overwhelmed)清楚地相信,除非某些極端不可能之事發生,否則,這種似乎注定會每天變得更加“反烏托邦”的趨勢將會持續地越來越系統化且無法扭轉:直到斷裂出現。并且,我們所有人都想知道,目前的這種病毒性的元事件(viral archi-event)是否將以某種方式被證明就是這種斷裂。當然,出現這種斷裂并不必然就是好事,除非此次斷裂能夠引發大規模的重新發明(reinvention)。
關于數字化事態之當前現狀的反烏托邦特征應歸因于希爾特·洛文客(Geert Lovink)所說的“平臺虛無主義”①G. Lovink, Sad By Design: On Platform Nihilism, London: Pluto, 2019.,以及我們在藝術—工業協會所說的“網絡抑郁”(net blues)②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D. Ros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6, p.13.。至于“斷裂”在此次疫情狀態下的意義,我們所有人都能夠理解,這是一次更新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所說的“休克主義”③N.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之涵義的機會,預示著一種朝向網絡的、技術圈的利維坦的總體激進化的新跨越。如果這種休克主義存在的話,那么,它到底會是什么?它的相反學說又會是什么?
根據我自己早先的分析,在此,我們首先需要追問的是:在這個可能性(probability)計算的霸權時代,不可能性(improbability)意味著什么?此種不可能性是多樣性,在此情況下,是指生物多樣性、心智多樣性。而可能性的(它總是相對于最可能而言④它是指從本土意義上(locally)臨時地偏離而出現的相對性,比如,由某種秩序或者組織而構成的可能性。)則是指消除多樣性的熵增趨勢。然而,這種不可能性也是無法預知的、意料之外的,它是“黑天鵝事件”,也就是說,它是可能性之崩潰的起源處的缺陷(flaw)。
不堪重負的感覺尤其來源于這種清晰的事實: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是建立在計算(calculation)之上的,而通過使用信息機器,計算本身已經成了霸權性的了。因為信息從功能上就是可計算的,那么,以此方式來構想信息(這種方式本身就是計算的結果),計算就獲得了清除多樣性的霸權。對多樣性的清除也意味著是對有益的不可能性的清除,這種不可能性能夠獨立地延遲無法預見的、毒性的災難性事件的增殖。
與“軟件極權主義”(soft totalitarianism)的運算符(operators)通過其總體化強加計算于萬事萬物之上相反,計算本身并不能夠計算所有的事物,它倒是能夠引發那些災難性的事情。而只有不能被計算的多樣的不可能性才能夠對抗這些災難性的事情。這是重新開始進行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計劃的出發點——不過,其中心論點在此就不再重述,它已部分地在《作為認識型和熵世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s Epistēmē and Entropocene)⑤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pp.139-151.一文中提過了。這里,我只重述三點:
(1)資本主義是一種認識型(Epistēmē),它已經被資本構成的網絡生產設備的固定資本所實現。這種認識型從功能上將計算工具整合為①在西蒙棟所描述的“功能整合”的意義上,此即為具體化過程。因為這一過程導致了西蒙棟所說的技術—地理的聯合環境(associated techno-geographical milieus)的出現。關于對這種環境近期發展變化的論述,參見斯蒂格勒的《世界的再魅》(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2014)《自動化社會》《崩潰的年代》(The Age of Disruption, 2019),以及《克服熵世》(Au-delà de l’Entropocène)等書。西蒙棟生活年代的科技發展水平,使他沒有機會來分析這種進化態勢。統計、測量、仿真、建模、觀測、生產、物流、移動、引導、文獻計量、科學計量、市場營銷和自我量化(“量化自我”)等過程的工具,進而專制地重新構造了所有的計算工具。
(2)信息是這種認識型的交換性的(allagmatic)②G.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s forme et d’information, Grenoble: Jér?me Millon, 2005,pp.529-536.運算符,它是一種能夠完全與資本主義同質化的計算科技,然后迫使所有由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構成的交換服從市場計算法則。并且,這種信息計算基于認知主義建立了網絡人工智能,而認知主義正是所有知識形式的普遍范式。
(3)然而,認知主義的認識型是一種反認識型(anti-epistēmē):它只有在徹底的無知化(generalized proletarianization)③此處的“徹底的無知化”是在艾倫· 格林斯潘的例子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我在《自動化社會》第一章中談論了這個例子。④這里的“proletarianization”一詞即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化”。斯蒂格勒從馬克思那里借用并發展了這一概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化”主要指的是“貧困化”(pauperization),而斯蒂格勒使用這個概念表示的則是“知識的喪失”(the loss of knowledge)。因此,這里我們將其翻譯為“無知化”。在斯蒂格勒看來,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大生產對人類勞動的“異化”只是現代科學技術對人類所具有的“怎樣去做”(how to do)的知識的剝奪,它是無知化的第一個階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所具有的“怎樣去生活”(how to live)、“怎樣去思考”(how to think)的知識也會不斷地被剝奪,即人類會繼續地被無知化,直至成為徹底的無知者(proletariat),而達到這里所說的“徹底的無知化”。——譯者注過程中才能夠發展。例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理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ory)一文中提出的所謂“大數據”指導下的相關主義的(correlationist)神話,就是通過認知主義范式和市場營銷,使得意識形態被重構的一個完美例子。⑤C. Anderson,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23 June 2008.而這種市場營銷自身現在已經成了網絡化的、擬態性的數據計算。⑥對意識形態與市場營銷之關系的論述,參見B. Stiegler, Pharmacologie du Front national, Paris: Flammarion, 2013,p.11.
在剩下的部分中,我們將集中研究不可能性和體外化形式之關系的問題,尤其是與標準化相關的問題。同時,我們將嘗試進入與許煜所寫的涉及技術多樣性和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的論文的對話中。
六、“第三世界”的動態支撐與當前理性的分解
我們已經感知到,一種從系統上對多樣性的清除正在發生,這一過程迫使所有事物都與科技、與可計算性聯系起來。科技是被合理化的(rationalized),依靠著合理化,科技就內在地與計算聯系在一起。經驗性的技藝并不會與這種合理化聯系在一起,合理化只會與“知道怎么去做”(know-how [savoir-faire])的知識聯系在一起。這種清除過程使我們痛苦,但我們并不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我們不“知道”它,而且因為一個非常特殊的原因:那種允許我們沉思和關懷這種事實并因而將此種事實帶到立法階段的知識,仍舊沒有發展出來。無論是對此次新冠疫情的后果而言,還是對理論計算機科學的重建而言,這種知識的構建都將是關鍵的議題。
重啟理論計算機科學的研究計劃需要從功能上將多樣性的需求考慮在內,這就預設了對一種負人類學的建構,以便于對人類世時代向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的分叉(bifurcation)產生影響。這種負人類學的建立是以數碼研究為前提的,其原則和主要目標已在2012 年蓬皮杜藝術中心的會議上提出過。它催生了一個非正式的網絡——數字研究網絡,以及一本書——《數字研究:知識器官學和認知技術》(Digital Studies: Organologie des savoirs et technologies de la connaissance)。
我在《自動化社會》和《技術與時間》的法語新版——這一版加了一個題目為《新系科沖突與諸種官能》(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①這個文本更早的版本有英文譯本,見B. Stiegler, The New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and Functions: Quasi-Causality and Serendipity in the 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Qui Parle, 26(1), 2017, pp.79-99.的新后記——中曾討論過這樣的問題:自動化的可計算性能夠將知性(understanding)的分析能力委托給自動化的滯留系統(retentional system),而這就會導致康德意義上的知性的過度增長和理性(reason)的退化。作為做決定的官能(faculty),理性是通過綜合能力(也被稱作判斷力)而起作用的。阿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他的后熱力學的(post-thermodynamic)對康德這些問題的恢復過程中,重新復活了綜合官能(synthetic function)的這種特殊性,即綜合官能并不能分解為分析官能(analytical faculty)。而且,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客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中同樣強調了他所說的“第三世界”②波普爾將跟人類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世界分為三個部分,即三個世界:物理自然世界為“第一世界”,人類的內在主觀經驗世界為“第二世界”,承載人類思想內容和精神產物的物質載體所構成的世界為“第三世界”。參見 [英]波普爾:《客觀知識》,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年,第78 頁。波普爾的“第三世界”概念與斯蒂格勒所說的體外化的“第三滯留”概念非常接近,后者正是指承載人類所生產的各種記憶和知識的外在于軀體的技術和技術物體。——譯者注和體外化(exosomatization)之間不可通約的聯系。
這種對知性之過度生長的態度和對理性之官能的態度是從我在《技術與時間3》中所開啟的討論而來的。在那里,我認為,想象(正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所定義的)和圖式(schematism)(正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所解釋的),并不是心智(mind)的先驗維度,而只是心智被配置出的經驗結構(configurations)。這些心智結構通過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hypomnesic tertiary retentions)①斯蒂格勒的“滯留”(retention)概念是從胡塞爾的《內時間意識現象學》而來。胡塞爾使用“第一滯留”表示當下的知覺,使用“第二滯留”表示對當下知覺的想象;并且,第一滯留決定了第二滯留。但胡塞爾從來沒有使用過“第三滯留”概念。斯蒂格勒受到胡塞爾的啟發,發明了“第三滯留”概念,指那些人類所創造的在人類軀體之外的技術和技術物體,比如燧石、斧頭、弓箭、車船等。而隨著人類的進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第三滯留,即這里所說的“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這種第三滯留是人類大腦記憶外在化的產物。斯蒂格勒之所以認為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最早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是因為這個時期發現了許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的巖洞壁畫,這些壁畫記載著人類過往社會的神話和歷史事件,它們提示著人類社會過往的記憶。典型的是1940 年在法國發現的已存在1.5 萬年之久的拉斯科(Lascaux)巖洞壁畫。關于斯蒂格勒對“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的論述,參見B.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pp.218-223。——譯者注而被建造并處于亞穩定狀態中。所有這些都與波普爾的“第三世界”相關: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正是此種第三世界的動態支撐。
通過自動化的知性來消解理性的特殊性,此種可能性的存在正構成了計算認知主義的基礎。計算認知主義與所謂的分析哲學一道,并與數字化的推廣同步,在最近幾十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它的這種主導優勢將被證明是與新自由主義完全同質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司馬賀(Herbert Simon)在朝圣山學會(波普爾也曾經參加過這一學會)恢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的過程中相遇,他們認為,市場是一種信息系統,一切好的東西都是可以通過這種信息系統進行計算的東西。
然后,哈耶克和司馬賀都將自由的觀念規定為一種能夠使信息自由流通的空間。但是,在這種空間中,所謂的自由實際上意味著是將所有現實(reality)都還原為可計算性的自由,也即,是將所有的現實化(realization)可能性(所有的未來)還原為市場之霸權規則的自由,是將所有的知識還原為這種熵增之條件的自由。不幸的是,波普爾自己在這場針對真正民主的政變中也妥協了。真正的民主總是保護,但不是對多數的保護,也不是對少數(這些是會計學概念)的保護,而是對多樣性的保護。每個公民的內心中都必須培養起多樣性的觀念,因為它具有產生負人類熵(neganthropic)和反人類熵(anti-anthropic)的潛能。
七、為什么在人類世末期,技術多樣性問題如此重要?
當許煜提出關于中國之科技的問題,并且首先將這種科技問題(在進入中國的技術問題之前)呈現為技術多樣性的問題之時,他就將多樣性這一觀念作為挑戰普遍的可計算性之霸權的方式。對下述兩者進行安排(這些安排本身也是可計算的)的機器可以實現這種普遍的可計算性:
(1)一方面是這種機器以及它運行其中的技術系統,機器能夠在此技術系統中同時成為計時器、儲存器和中心單元,也即(作為處理單元的)運算符;
(2)另一方面是社會系統,同時還有生物系統和地理系統,作為徹底的計算技術系統的機器通過計算能夠掌控這些系統,進而通過反饋回路就分解了這些系統。反饋回路能夠連續不斷地實時運行,能夠將每一筆交易都還原為市場計算。反饋回路是基于遞歸函數而建立的,皮埃爾·利維(Pierre Livet)之前強調過它的困境。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
(1)認知主義者錯誤地將計算機定義為圖靈機。計算機已經成了通過反饋回路來收集、處理和分配數據的計算網絡的細胞元件(在計算機已經可以縮小為智能手機的意義上)。計算機反饋回路的運行速度要快于形成本地網絡(local networks)的神經系統數百萬倍。而這種本地網絡則是依賴于文本、精神個體、公民或者消費者而形成的。
(2)隨著盧西亞諾· 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所說的“信息有機體”——也就是心理—技術設備(apparatuses)——的聚集,技術圈就成了路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說的巨型機器(megamachine),進而以此方式,技術圈就構成了一種新的復雜性更高的器官外化的有機體(exorganism)①B. Stiegler, The Neganthropocene,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18, pp.132-134.②B. Stiegler, Nanjing Lectures, D. Ross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2020, p.286.。在此有機體中,使用這種巨型機器的平臺聲稱將用完全無視形式因、目的因和材料因的計算效率主權取代由其自身目的所定義的政治主權。
(3)正是在此背景下,今天,所有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都將被迫面臨技術多樣性的問題。然而,從許煜的視角來看,這一問題首先是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并不能夠被還原為西方。對西方而言,中國已經變成了它強大的挑戰者。
在當前的形勢下,比如就非常有必要回到萊布尼茨所密切關注的、構成中文書寫條件的問題上來,這種條件可能包含了一種或許永遠不會被西方思維所理解的精神的主權維度。③德里達《論文字學》的一個重要成就正是對此一問題的關注,以及對西方自以為是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的關注。許煜和我一直希望能夠在中國組織一場關于這些問題的學術會議,可以冠以“通用表意文字、理論計算機科學和書寫游戲”(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and Games of Writing)的名字。
現在作為蹤跡工業(industry of traces)④“ 蹤跡”(trace)是德里達和斯蒂格勒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其重要程度幾乎等同于“存在”這一概念在海德格爾哲學中的地位。對于德里達而言,存在從來不會在場,在場的永遠只是存在的蹤跡或痕跡。它們是對存在之不在場的替補(supplement)。形而上學家之所以遺忘了存在,是因為他們把存在的蹤跡當成存在本身。斯蒂格勒這里所說的“蹤跡工業”正是通過數字技術等手段試圖捕捉人們日常生活蹤跡,進而控制人們需求的工業。人們在各種程序軟件中留下的數據蹤跡,本身是可有可無的,因為沒有這些程序軟件就不會有這些數據蹤跡。但這些數據蹤跡一旦被捕獲,“蹤跡工業”就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對它們進行計算,模擬出人們的需求規律,進而制造和控制人們的需求。這種所謂的“數據經濟”實際上就瓦解了人們主動地去思考什么是自身真正需求的理性能力。關于“蹤跡”的論述,參見J.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A. Bas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20-29;關于“蹤跡工業”的論述,可參見B.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pp.22-26。——譯者注的“數據經濟”正在瓦解理性,不過,這一過程卻是在20 世紀隨著文化工業的發展而開始的。文化工業正在將理性替換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現代性(modernity)正是以此為代價成了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種字面上的分解和過度理性化的瓦解(邏各斯完全被作為算法的比值[ratio]所取代,因為在會計學的意義上,一種比值一旦出現,就是意味著一種算法的出現),就等同于普適性(universality)的這一概念的瓦解。并且,通過對機器這一概念的濫用,這種瓦解過程在今天已經完成。此種情況下,這里的機器概念就正是指阿蘭·圖靈已經理論化的抽象機器概念。
正是這樣,西方的普世主義沒有變成尊重人類之多樣性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而是成了根據其自身(即西方的)利益來異化一切資源的理性化過程。這個由認知科技①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這一系列的數字科技構成了一種新的認知功能。我們將這種新的認知功能描述為一種理性之官能的軀體之外的外在器官發生。參見B. Stiegler,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所強制實行的過程在完全不同于精神技術(spiritual technologies)②精神技術是依納爵·羅耀拉(Ignace de Loyola)和他的傳教士為回應路德派精神技術的傳播,而實施的服務于精神修煉的技術。它首先是將《圣經》翻譯為適合每一個人閱讀的書,然后以此方式,將信仰和忠誠(fidelity)重新定義為一種閱讀訓練。之后,本杰明·富蘭克林根據加爾文派的教義重新定義了這一方案。他將信仰和忠誠觀念引向有“比率”(ratio)出現的記賬簿中,并因而將“忠誠”(“fidelity”亦可翻譯為“保真度,精確度”——譯者注)重新定義為“計算”。的區域(register)上繼續并完成了由文化工業③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本雅明之后也討論了文化工業的問題,不過,他們沒有完全理解本雅明所說的可復制性(reproducibility)的重要性。關于“什么是可復制性”,參見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ch.6.所開啟的進程。
因此,所出現的問題正在于,現代性是否就意味著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歷史過程中所發展出的,尤其是作為科技的那些趨勢的普適性。科技的發展已經將普適的科學法則具體化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牛頓的物理學和可計算性的數學。為了接近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回到安德烈·勒魯瓦-古蘭(André Leroi-Gourhan)的普遍技術趨勢(universal technical tendencies)的概念,許煜在其《論中國的技術問題》一書中簡要地重述了此概念的主要特征。④Y.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o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pp.8-10.
正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接近地球生物圈中的狀態轉變”(Approaching A State Shift in Earth’s Biosphere,巴諾斯基等人撰寫)的簽署國、2018 年11 月13 日李普爾(Ripple)等人在《生物科學》(BioScience)上所做的呼吁以及2020 年2 月1000 名法國科學家所召集的反抗活動“法國千名科學家的呼吁”(L’appel de 1000 scientifiques)等各方所宣稱的:在人類世時代,上述這些問題已經沒有了獲得解決的可能性。因為,因生物多樣性和心智多樣性的消亡而導致的極端危險在人類世時代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了。其中,這種消亡的運算符正是以普遍的數字文碼化而運行的體外化的當前階段。
在這個或多或少地有點末世論意味(非宗教意義上)的人類世階段,我們該怎樣去理解勒魯瓦-古蘭的普遍技術趨勢之概念呢?
八、趨勢與環境
我們是應該,例如,跟隨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等加速主義者的觀點嗎?根據這種觀點,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網絡平臺技術引導向正確方向,即引導向社會正義和重建經濟合理性(rationality)的方向。或者,我們應該使技術—工業概念變得多樣化?這有點類似于1987 年美國股災之后的情況,當時,美國當局宣稱,為了避免股票指數系統性強勢下跌的趨勢,股票交易市場的自動交易程序的“習慣化”(idiomatization)是必不可少的。①C. Distler, Réseaux globaux et marches financiers: les le?ons du krach de 1987, Quaderni, 12,1990, pp.37-47.不過,根據此次事件之后的研究表明,當時的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曾公開表示股價太高,此種言論反倒誘發了股價強勢下跌的趨勢。
許煜似乎并不同意勒魯瓦-古蘭和我的觀點,因為我接受了勒魯瓦-古蘭關于普遍技術趨勢的論證。②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許煜《論中國的技術問題》一書所堅持的“具體化過程”的立場。西蒙棟是就機器的生成過程而談論具體化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西蒙棟使用“具體化”這一概念是為了回應維納,以及他對機器與有機體之間的反饋問題的思考,也即遞歸的問題。遞歸是許煜最新的著作《遞歸與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London: Rowman, 2019)一書所探討的主題。因此,為了理解技術多樣性和許煜對此觀念的立場,必須考慮到以下兩點:
(1)勒魯瓦- 古蘭在《環境與技術》(Milieu et Techniques)中所提出的環境問題,以及作為“種族細胞”(ethnic cell)的環境的問題,它們總是已經在體外化的過程中被分割成了內在環境、技術環境和外在環境等彼此相互衍射的諸種環境。③以此方式,構成了體外化單體(exosimples)和體外化復體(exocomplexes)的體外化過程。關于這一點的論述,可參見G.Gilmozzi, et al., Localities, Territories and Urbanities in the Age of Platforms and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Anthropocene Era, Stiegler and the Internation Collective, ch.2,以及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3:Déconstruction et destruction,即將出版。勒魯瓦-古蘭以“外在化”(exteriorization)概念來表示“體外化”。這樣的話,從來就沒有單一環境(就像沒有單一語言一樣),有的只是從最開始就以某種方式被分割開來的諸種環境。這里,我們必須將環境與語言問題做一個對比:從來沒有單一的語言,有的總是俗語、個人習語、方言、土語等諸種語言。
(2)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區分軀體之外的外在器官發生(exosomatic exorganogenesis)和外化記憶的體外器官發生(exomnesic exorganogenesis):外在記憶化(exomemorization)④B.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2:La le?onde Greta Thunberg,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20.是提示記憶之支撐物(hypomnesic supports)的生產過程;并且,從這些不同的延異之差異化(differently différant differentiations)過程開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辨識出普遍技術趨勢之表達的條件。普遍技術趨勢包括諸多的趨勢,除了在頭腦中幻想之外,它們從來沒有被完全表達出來過。勒魯瓦-古蘭從原則上指出過一種衍射過程,此種衍射能夠摧毀從原則上制造負人類熵之衍射的所有東西,但西蒙棟在假設機器具體化(machinic concretization)之過程的時候卻忽略了它。機器之具體化能夠引導某種聯合環境(associated milieus)的形成,此種聯合環境憑借控制論擴張其網絡范圍,進而會構成海德格爾所說的“座架”(Gestell)。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對這兩點內容進行評論是非常有必要的。
九、什么是趨勢?
普遍技術趨勢之表達的條件會受到技術個性化(technical individuation)過程的限制和引導,因此,它的表達總是不完全的,它的條件會根據制造這些表達的外在記憶的文碼化的類型而變化。
從舊石器時代晚期(文碼化過程正是在此期間出現的)開始,體外記憶的文碼化就已經產生了社會系統的提示記憶的支撐物。吉爾(Bertrand Gille)和盧曼(Niklas Luhmann)認為,從薩滿教到學院、研究機構、法院、行政轄區、國會等,再到教堂、寺廟和所有類型的神學組織,都是這種支撐物。準確地說,普遍技術趨勢之表達的條件是根據先前的外在記憶化過程所產生的事物的類型而變化的,而此種過程與文碼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什么使趨勢成為趨勢,并且僅僅是趨勢?這首先是因為單一趨勢是不存在的:趨勢總是與其對立趨勢相伴而存在,它們因此共同構成了一種同源二極性(bipolarity),并進而擴展了西蒙棟所說的不確定的二分體(the indefinite dyad)。此種二元性也是一種沖突性,它正是尼采通過狄奧尼索斯和阿波羅兩種形象所構造出來的東西,也即“不和”(eris)。而且,這也是柏格森以其他術語所重新構想的內容:他把熱力學和生命的特異性(singularity)放到“宇宙的熱寂”過程中去思考。
趨勢相對于另一種(對立)趨勢而言,是一種(對立)趨勢。在此趨勢中,就形成了一種開放的動態系統。此種動態系統在受到多重因素更強限制的作用下,會形成一系列的互導關系(transductive relations)。其中也會生成次級系統。比如,體內化生命(endosomatic life)①所謂“體內化生命”指的是一般的純粹生命有機體,即病毒、細菌、植物和動物。在斯蒂格勒看來,人類生命是“體內化生命”在進化過程中所出現的特殊生命形式,因為根據勒魯瓦-古蘭的“外在化”思想和洛特卡的“體外化”思想,人類進化是逐漸地將其器官功能外在化于技術和技術物體之中而進化的,人類是“體外化生命”(exosomotic life),人類的出現是與純粹生命的斷裂。關于“人類生命與一般生命的斷裂”的論述,可參見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The Fault of Epimetheus, R. Beardsworth and G. Collins(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pp.134-142。——譯者注的有機體就是一種動態系統,它由器官構成,而器官則是由細胞構成。在人類生命中,什么又使得對立趨勢成為對立趨勢呢?這是由柏格森所提出的問題,他將其描述為一種在任何力學中都在發生的神秘的開放性(mystical opening)問題。②H. Bergs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Trans. R. Audra & C. Brereton (Trans.),Westport: Greenwood,1974, ch.4.此處所謂的力學,不僅包括牛頓力學及其“機械論”,也包括品達(Pindar)意義上的“機器”(mekhanē)。③B. Stiegler,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D. Ross (Trans.), Cambridge:Polity, 2019, p.92, p.157, p.290.
在有時被稱為“臨界狀態”(disruption)所誘導的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技術多樣性的問題就會出現。然而,技術多樣性本應是作為抵抗單一趨勢之事態而出現的。所謂單一趨勢實際上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術語,因為它不再是一種趨勢而只是一種狀態。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種狀態,即我們所說的死亡,這里的問題就成了“文明的死亡”。而這種臨界狀態的特殊性實則是基于下述事實而出現的:體外化的科技和外在記憶的科技現在已被數學機器(mathematical machines)整合起來,這就形成了文碼化的數字階段,并因此建立了一個完全無法比擬的體外化階段。
十、趨勢與熵
這種整合正是基于算法的“平臺”——正如弗蘭克·帕斯奎爾(Frank Pasquale)所描述的——所具有的特征,這相當于這種新計算的“一般等價物”:它傾向于取代貨幣。但是,這種趨勢迫使自身成為一種事實狀態(state of fact),而不再僅僅是一種通過其歷時化來擴展其共時化的趨勢,它的“普適性”就產生了一種對生物圈和技術圈都非常致命的無法抵抗的人類熵。
這一挑戰因此重新引入了在體外化和外在記憶化之間再建心智多樣性之可變性的條件。很明顯,心智多樣性的可變性也是技術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以培育能夠阻止技術圈去破壞生物圈的生物多樣性。這就要求從體外化視角和心智發生(noogenesis)的視角來重新反思“什么是心智”以及心智的官能和功能等問題。①B. Stiegler, Postface: 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3.Paris: Fayard, 2018, pp.862-868.
體外進化是不同于體內進化的進化模式,我們在體外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體外科技(exosomatic technologies)是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問題。西蒙棟將這些問題看作是機械學(mechanology)的問題,康吉萊姆則將其看作器官學問題;而在洛特卡之后,體外科技問題則屬于我們應該以體外進化的視角來考慮的問題。體外進化確實會受到體內(器官構造)的束縛,康吉萊姆就曾在《正常與病態》一書中嘗試分析過這個問題。但是體外進化會超脫這些束縛,即使并不能完全擺脫。舉例來說,斯蒂芬·霍金正是在幾乎擺脫內在器官束縛的處境下,進行自己的生活的,但他并沒有完全擺脫;因為,如果他在某種程度上完全超越內在器官之限制,他就不會死了。
說到這里,在進一步討論之前,讓我們來談一下第三點。在《環境與技術》一書所做的定義的意義上,技術環境總是超越內在環境,并且,技術環境正是通過將自身貫通于與其他內在環境(其他“種族細胞”)所處的共同外在環境中,而與其他內在環境的技術環境之間發生共振,進而使自身與其他內在環境形成聯系的。
今天,技術環境的貫通浸透于所有外在環境之中,以至于不再有任何外在環境;并且,除了其自身缺乏培育異質性之潛能并因此變得貧瘠的內在環境之外,也不再有任何東西。也就是說,技術環境會貫通和連接內在環境,與它們形成聯系,并進而使內在環境本身崩潰。最終,技術圈不再有任何異質的成分,而只是一種單一的技術環境。
外在記憶化導致了三個層面上都出現的體外器官化(exorganization):
(1)生理層,比如與體內器官相連接的非提示記憶(non-hypomnesic)的體外化器官;
(2)神經層,它構成了體外化的、外在器官化的大腦的主要特征,并從提示記憶的意義上作為神經層而存在;所有這些都是以作為社會規則的教育模式(對神經層的塑造)為前提的;
(3)邏輯層,它在很長的時間內(在西方)是邏各斯(logos)、悠閑(skholē)和休閑(otium)的問題,但是,隨著邏輯機器的出現(這種機器本身是基于物質的微觀物理學特征而發明出來的),邏輯層的問題已經變成了科技問題。
在第二層和第三層之間,象征的體外器官化(exorganizations)(首先是習語)被編織起來。這三個層面的編排正是更高級的復雜體外化有機體(exorganisms)的特征。
這些問題的巨大挑戰,尤其是在后新冠疫情時代,將會構成基于負人類學、以期到達負人類世時代的、為一種負熵經濟服務的新的理論計算機科學。而在此科學理論的中心,將進行著貫徹整個想象過程的知性與理性之不可計算性和不可化約的延異過程。在這里,提示記憶的第三滯留構成著想象本身;在這里,勒魯瓦-古蘭的普遍技術趨勢構成著技術—邏輯之圖式(techno-logical schemas)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