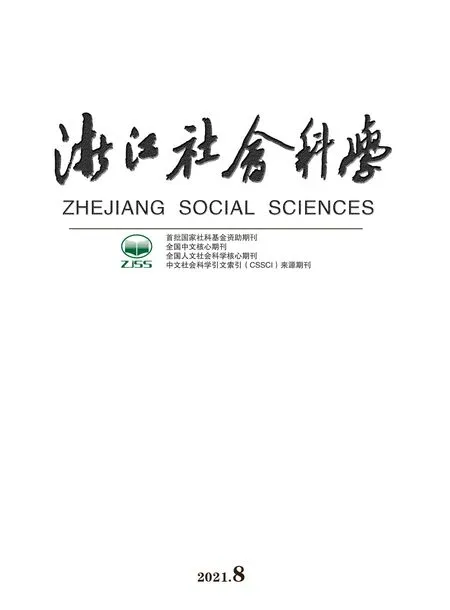略論浙學與蜀學的歷史互動
□ 舒大剛 胡游杭
內容提要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誕生了眾多以區域文化為背景、以地域名稱而命名的學術文化,不同的地域學術之間通過學習互鑒,交融互動,孕育出更為豐富而深邃的學術思想。以浙江、巴蜀兩地的區域歷史文化為底色孕育而出的浙學與蜀學,在歷史上展開了長時間、多時空、跨維度的學術文化交流,彼此互學互鑒、交相輝映,共同推動了中國的學術文化向更新的形態和更高的階段發展演化。
引 言
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包容互鑒、和諧共生的文明,中華文化因其豐富燦爛的內涵而博大精深,中華學術也因其多元互補的結構而歷久彌新。地域學術是在特定的地域和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與該地域的歷史文化相關聯的學術形態。中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誕生了眾多以區域文化為背景、以地域名稱而命名的學術文化,諸如齊學、魯學、洛學、閩學、湘學、關學、蜀學、浙學等等。這些地域性學術在中華文化的主要元素、核心內涵與思想價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并在傳播主流文化、塑造國民心理、凝聚民族意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不同的地域學術之間通過學習互鑒、交融互動,孕育出更為豐富而深邃的學術思想,共同推動了中國的學術文化向更新的形態和更高的階段發展演化。
巴蜀與浙江分別位于中國的西南腹地與東南沿海,二者以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成為早期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并在悠久的歷史積淀中孕育出了豐富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典籍,分別形成了蜀學、浙學這兩支典型的地域性學術形態。浙江與巴蜀雖相距千里之遙,卻在歷史上不乏人文的互動與思想的交融,并展現出許多類似的特征。縱覽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史可以發現,浙學與蜀學互學互鑒、彼此聯動、交相輝映,共同影響并推動著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進程。
一、先秦時期:文化發煌,千里神交
浙學與蜀學分別是以浙江、巴蜀兩地的區域歷史文化為底色孕育而出的學術形態,兩地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誕生了燦爛的人類文明。據現代考古發現,浙江與巴蜀都存在大量的早期人類文明遺址或遺址群,如浙江有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良渚文化古城遺址,四川有成都平原古城遺址群(寶墩文化)、三星堆古遺址、金沙遺址等。這些遺址代表的是距今七千至三千年前的古越人和古蜀人的文明狀態,從其中出土的各種青銅器、玉器、金器等文物來看,都顯示出較高的生產力水平、藝術造詣和精神追求,其中許多文物,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鳥舁日”象牙雕刻、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人面、鳥冠、獸身三位一體的玉琮神徽、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人像鳥獸桐樹、天地人合體的青銅神壇等,都反映出古越人和古蜀人在天地宇宙、人與萬物、神靈圖騰等方面都具有共通的意識。①三星堆金沙出土玉琮與良渚玉琮的高度相似性表明,古蜀人與古越人在史前時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傳播與交流,特別是從兩地古遺址中發掘的文物所反映出的文化哲學涵義則表明,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天地人三才”等觀念意識在古越文化與古蜀文化中就已經萌芽。雖然此時的古越文化與古蜀文化還屬于物質文化、風俗文化的范疇,尚未有文字記錄其已形成有觀念形態和理論體系的學術思想文化,但稱其為浙學與蜀學的雛形應該是可以的,而且二者在早期文明中就已然隔空呼應、神交千里了。
大禹文化是浙、蜀文化的第一個交集點。禹生于蜀地,②而卒于越域,③對巴蜀與越地的學術文化、風土民俗具有深刻的影響。據傳禹曾得“《洪范》九疇”以平治水土、疇畫九州,因伏羲氏《河圖》而演繹為《連山》之易。④《連山》之“陰陽”,《洪范》之“五行”,后來都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概念和共同范疇,為儒、道所共遵,⑤同時也深刻影響了后世浙學、蜀學重視天人合一、儒道兼融的治學風格。
先秦時期,儒學就已經對蜀、越兩地產生過深遠影響。孔子弟子商瞿據傳為蜀人,據《四川通志》載:“商瞿,雙流人,孔子弟子,生于瞿上,鄉歿,亦葬于瞿上,至今墓碣猶存。”而據《史記·儒林列傳》載:“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葘州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⑥而楊何就是漢武帝時期所立“五經博士”中的楊氏《易》,司馬遷父司馬談還曾“問《易》于楊何”。而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貢則直接影響了越地的歷史,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⑦因而“子貢思想中的儒學種子,在當時即已播撒在古越大地。”⑧由此可見,孔子開創的儒學通過其弟子傳播到了蜀、越兩地,而越人、蜀人又通過政治軍事活動、學術文化傳承等方式影響乃至反哺中原大地。
二、兩漢時期:學術發端,別開生面
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為文教的傳播推廣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交流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浙學與蜀學也在這一時期正式形成。
蜀學、浙學的形成與儒家教化的推行密不可分。西漢景帝末年,廬江舒城人文翁為蜀郡守,在成都修起學宮,派遣郡中子弟詣京師求學,歸則傳授儒家經典,用文化知識培養并選拔人才,這一事件史稱“文翁化蜀”。⑨“文翁化蜀”使得巴蜀地區的文化獲得了極大發展,蜀地由“僻陋有蠻夷風”的化外之域一躍成為“與齊魯同俗”的文化勝地,從此蜀士欣欣向學,涌現出如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作為浙學開拓者的王充也曾進入東漢太學學習儒學,師從班彪、桓譚等大師,歸鄉后潛心著述教學。可見,蜀學與浙學都是從中原輸入后又在當地形成了獨特風格的學術形態。
揚雄、王充分別是漢代蜀學、浙學思想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二者雖非在同一時代,卻在許多方面表現出高度的默契。揚雄和王充皆出身寒微,在學術上不喜章句訓詁,不慕世俗功名富貴。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⑩王充也是“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不好徼名于世,不為利害見將。”?王充更是對揚雄十分欣賞,多次表達出對揚雄的傾慕,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還將揚雄與古代圣賢大家并列,曰:“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也。”?
在思想上,揚雄與王充也有眾多的共同點,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天是沒有意志和目的的自然之天,反對將天神秘化。在人性論上,揚雄主張“性善惡混論”,王充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揚雄的人性論,曰:“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雖然性有善惡,但揚雄、王充都主張人性是可以通過學習教化得以改變、導惡向善。揚雄曰:“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惡。”?王充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
針對兩漢之際經學逐漸走向神秘化與讖緯化,揚雄、王充都對此進行了否定和批判。揚雄《法言》中多有否定神怪、反對神化圣人的論說,如:“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當有人詢問圣人有何特異時,揚雄答曰:“圣人德之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王充也是明確反對“虛妄”的讖緯迷信,“疾虛妄”是貫穿《論衡》全書的主旨,王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針對當時盛行的天人感應、災異譴告等學說,王充云:“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而所謂的災異,不過是純粹的自然現象,不是天意志的表達,沒有任何的神秘色彩,曰:“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王充認為生命的存亡也是氣凝聚和消散的自然過程,因此人死不能為鬼,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 ”
在揚雄和王充的思想中,都顯現出援道入儒、融攝儒道的特征。揚雄少年時曾在蜀中從學于精通《易》與老莊之學的嚴遵,嚴遵所著《老子指歸》中“神明”“太和”的宇宙觀解讀與“修身正法”“隨時循禮”的儒家思想成為揚雄一生學術思想的底色。揚雄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遂主張融攝儒、道的“道德仁義禮”五德觀,曰:“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揚雄認為“道德仁義禮”五者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這一觀念將道家的“道德”與儒家的“仁義禮”相結合,比之傳統的儒家增添了道德源泉與終極關懷,具有虛實結合、體用兼備的特征。王充雖然在天道自然觀上采用了道家的立場,明確稱其“試依道家論之”,但也極為肯定儒家的價值,贊成儒家養德、用賢、禮義等政治與社會倫理思想。王充曰:“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示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又曰:“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矣。”“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
作為蜀學與浙學在漢代的代表,揚雄、王充二人的學術思想在天道自然、人性善惡、批判迷信、融攝儒道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特質,甚至以桓譚為紐帶使二者存在思想上的前后傳承。在漢代經生墨守章句訓詁、嚴格師法家法、宣揚讖緯迷信的學術風氣下,揚、王二人無疑為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
三、兩宋時期:學統繼起,鼎峙會通
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戰亂頻仍,而前、后蜀政權和吳越政權統治下的巴蜀與浙江則相對安定,社會經濟未遭到重大破壞,其統治者保境安民,以文治世,使兩地文化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持續發展。前蜀王建禮敬文人,多次恢復庠序、崇飾孔廟、收集圖書;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始刻“石壁九經”,奠定了“蜀刻十三經”的主體。吳越錢氏亦重視文教,倡導儒家道德倫理。
兩宋時期,蜀學與浙學相繼進入學術蜂起、學派林立的繁盛時代。慶歷之后,“學統四起”,宋學主要學派均開始形成,時有以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兄弟三人為代表的蘇氏蜀學,與王安石“新學”、二程“洛學”鼎足而立,是以南宋四川學者李石曰:“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圣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辟其說,是為元祐學人謂之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頤;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以攻新說。”
浙江是蘇氏蜀學東傳的重要方向,“三蘇”之一的蘇軾曾出知杭州,賑濟災傷、疏浚西湖,現存之“蘇公堤”即是東坡造福一方的明證,蘇氏蜀學亦因得以入浙。蘇轍長子蘇遲,南宋紹興初年知婺州,生子籀、簡,為蘇氏子孫在浙江的支脈延續,是以浙江亦得蘇學浸染,陳傅良、陳亮、葉適、呂祖謙等“皆以文名,皆蘇氏之后昆。”
兩宋之際,“中原衣冠不南渡,則西入于蜀”,浙江、巴蜀成為中原學術南傳的主要方向,蜀學、浙學也在南宋時期與洛學逐漸合流。
譙定是兩宋之際四川的著名學者,兼具蜀、洛兩家學統。據《宋史·譙定傳》載:譙定“學《易》于郭曩氏,……郭曩氏者,世家南平(今重慶綦江),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后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點易洞’。”譙定之學流衍甚廣,閩學、湖湘學、浙學、蜀學中不少學者皆可溯源至譙定,王梓材云:“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胡憲)與白水(劉勉之)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儒》言魏公(張浚)嘗從譙天授游,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據當代學者考證,譙氏門人有劉勉之、胡憲、張浚、張行成、馮時行等;再傳有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三傳有蔡元定、黃干、輔廣、魏了翁、陳埴、杜煜、陳淳、袁燮、舒璘等;四傳有王應麟等。張浚、張栻父子、張行成、馮時行、魏了翁等為蜀人,呂祖謙、輔廣、陳埴、袁燮、舒璘、王應麟等為浙人,張栻開創湖湘學派,金華婺學呂祖謙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袁燮、舒璘與楊簡、沈煥合稱“甬上四先生”,為象山心學在浙東的主要傳人。可見,譙定是上承伊洛二程,下啟南宋學術的一重要樞紐,有功于理學在蜀學、浙學中的傳播。
張栻為南宋宰相張浚之子,自幼從父問學,并授業于二程再傳弟子胡宏,主講岳麓書院,開創湖湘學派,“續周、程之學”。呂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旁通博覽、參貫經史,啟金華婺學之先。張、呂二人與共同的好友朱熹相與講論,“鼎立為一世學者宗師”,并稱“東南三賢”。
張栻與呂祖謙曾先后在嚴州與臨安共事,又有數十年書信往來論學,二人“聲同氣合,莫逆無間。”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呂祖謙任嚴州教授,同年張栻亦知嚴州,二人在當地頗有惠政。次年,二人先后赴臨安供職,呂祖謙特地與張栻同巷而居,在寫給朱熹的信中說:“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張栻也頗喜二人論學之歡,曰:“伯恭鄰墻,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乾道七年,二人分別后遂以書信往來論學,其討論的范圍十分廣泛,包括讀史的次第順序、張栻所著《論語解》《孟子解》,以及理學的修養方法等。呂祖謙曾就讀史次第的問題致書張栻,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鑒》,欲其體統源流相承耳。”張栻后來回信說:“所示讀書次第皆著實。”張栻刪修其所著《論語解》與《孟子解》時,曾向呂祖謙詢問意見,呂祖謙遂撰《與張荊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答之,對其中的二十八章提出了修改意見,多被張氏所采納。張栻對呂祖謙在理學的修持工夫上頗多指點,告誡呂氏注意“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的工夫,曰:“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體察之功。某每思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為美。然在學問,不可不防有病……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張栻還在“存養省察”“篤敬之功”等工夫論上提點呂祖謙,故呂祖謙在與陳亮的書信中道:“長沙張丈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另外,張栻與呂祖謙的通信中對朱熹的學說著作亦多論辯。
縱觀兩宋蜀學與浙學,二者都在這一時期走向興盛,并展開了頻繁的、多層次的交流與互動。雖然蜀、浙之學起初與洛、閩理學不甚相合,北宋有洛黨與蜀黨之爭,南宋有朱熹與陳亮之辯,但蜀學、浙學都在與程朱之學的交流與論辯中深度參與了理學的構建。《宋元學案》曰:“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后溪(劉光祖)與先生兄弟(李壁、李埴)出,鶴山(魏了翁)繼之,遂合其統焉。”劉光祖為資中學派李石的傳人,亦為朱熹“同調”,李壁、李埴為丹棱學派李燾之子,李石、李燾之學則多得于蘇(蘇洵、蘇軾、蘇轍)、范(范鎮、范祖禹)之蜀學,魏了翁私淑張栻,開鶴山學派,其學脈可上溯于譙定,可見蜀、洛最終合流。“浙學”雖多為朱熹所斥,但在南宋,其前有呂祖謙主持“鵝湖之會”意欲調和朱陸之爭,其后有黃震、陳埴、何基、王柏、金履祥等浙中朱學的傳承流衍,亦歸于理學。由此可見,蜀學與浙學都在建構理學的同時而又不失自身鮮明的特色:蜀學兼收并蓄,主張融攝三教;浙學求實致用,崇尚經制事功,最終也與洛閩之學從鼎峙走向會通。
四、元明清初:蜀學賡續,在浙之濱
南宋末年,四川地區屢遭戰火蹂躪,包括文翁石室、蜀刻十三經在內的禮教文物皆毀于兵燹,其時蜀學遂衰敗不振,但不少祖籍巴蜀的學者士人僑居浙江,推動了浙江當地學術文化的發展,蜀學亦在異鄉得以繼續傳承,因此近代蜀人學者劉咸炘說:“元兵略蜀,蜀士南遷于浙,浙人得此遂成文獻之府庫,江南文風大盛。”
浙學至明清兩代而發展至巔峰,明代浙學“由宋濂、劉基開其端,方孝孺繼其緒,而由王陽明成其大,劉宗周殿其后。”自程朱理學尊為正統,科舉以之考核士子,其末流僅得其皮毛以為進身之階,其學僵化支離之弊愈顯,是以明代新說迭出以圖救之。黃宗羲有曰:“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將王門學術的流衍以地域劃分為數個學派,然而,彼時亦有蜀中學者與王學互有關涉。席書(四川遂寧人)與王陽明介于師友之間,亦是陽明的平生知己,席書不僅在陽明困厄之時給予其巨大的寬慰,于王陽明危急之時予以全力支援,而且二人相與論學,互有啟迪。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因忤逆宦官劉瑾而被貶謫貴州龍場驛,正德四年(1509年),席書出任貴州提學副使,延請陽明教授文明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也正是在此時陽明首發知行合一之論。據《王陽明年譜》載:“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同異,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可見王陽明對“知行合一”的闡發也因緣于席書的疑難論辯,而席書也成為陽明心學的首批信眾,更推動了陽明學在貴州等地區的傳播。正德十四年(1519年),寧王朱宸濠叛亂,時任福建左布政使的席書在接到王陽明的求援文書后“急募兵二萬討之”,全力策應王陽明的行動,為王陽明迅速勘定叛亂做出了貢獻。嘉靖初,大禮議起,席書曾多次與王陽明交換意見,曾一度舉薦王陽明入閣。可見,席書不僅是王陽明一生的知己學友,更是在政治事功等方面于陽明有知遇之恩,而王陽明亦對席書情誼甚篤,曾“駐信城者五日”等候席書,只為與其“信宿之談”。席書死后,王陽明撰《祭元山席書文》,贊其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
王陽明學說合心體與性體、本體與工夫為一,良知成為最高評判標準,自我主宰,當下具足,使得人心得以獲得充分的自由與解放。然而其流弊亦因此而日益凸顯,明末大儒劉宗周曰:“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是以后學紛紛思以救之。劉宗周、黃宗羲開啟的浙東一脈承王學之傳而多有修正。劉宗周倡“慎獨”宗旨,以“慎獨”“誠意”而欲施救王學末流蹈空近禪之病。黃宗羲承蕺山之緒,在秉承陽明心學的基本立場的同時,更開辟了以“明經通史”為特色的清代浙東經史學派,萬斯同、萬斯大、邵廷采、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等皆其流衍,是以近代蜀中學者劉咸炘曰:“南雷雖衍蕺山之傳,而經史之業特勤……史學傳之萬、邵,下開謝山、二云、實齋,為二百年所獨。昔之敘儒林者,多類之漢學,有以也。”明末清初,長期的戰亂和動蕩致使巴蜀教育不振,學術頹敗,但彼時蜀學亦有學者可述,如丹棱彭氏(彭端淑、彭端洪)、潼川張氏(張問陶、張鵬翮)、新繁費氏(費經虞、費密、費錫璜、費錫琮)等,蜀學與浙學的交流亦未中斷,如費密曾以其父費經虞所著《紀奢寅亂蜀事》及先父《行狀》呈與明史館,襄助“以布衣參史局,不置銜,不受俸”“不居纂修之名,隱操總裁之柄”的萬斯同編修《明史》。
五、近現代:變革轉型,返本開新
鴉片戰爭之后,伴隨著國門的打開,各種思潮在中華大地上相互激蕩,思想學術異常活躍。浙學與蜀學也在這一歷史時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眾多杰出學者的涌現推動著浙學與蜀學由傳統學術向近現代學術轉型。如浙學龔自珍、黃式三、黃以周父子、俞樾、孫詒讓、章太炎、魯迅等;蜀學亦人才輩出,有楊銳、宋育仁、廖平、吳之英、劉咸炘,以及謝無量、張瀾、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等一大批著名學者與革命家。
這一時期,浙學與蜀學交流頻繁、相互促進。清末張之洞提督四川學政時創辦尊經書院,欲仿杭州詁經精舍學制,以“紹先圣,起蜀學”,曾一度邀請浙江學者俞樾、李慈銘等出任山長,而最終為尊經書院主講的錢保塘、錢保宣亦是浙人,二錢“以注疏課士”,促進了經學在蜀地的復興。此外還有不少名家學者或往來浙、蜀,或接續前賢,為二學互動之典范。
劉咸炘為“川西夫子”“槐軒學派”開創者劉沅之孫,自謂其學既承家學淵源又得益于浙東章學誠,曰:“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于辨先天與后天,實齋之言總于辨統與類。”劉咸炘十分欣賞章學誠之史學,劉咸炘承襲了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思想理路,但對其又有所推進,將章氏“六經皆史”為“先王之政典”之說推本溯源于更為廣義和根本的意義上,認為宇宙以人為中心,萬物皆賴人而有其存在意義,是以世間之一切流衍變化與學問對象皆不出“人事”,故謂之“人事學”,曰:“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即在此。……實齋名此曰史學,吾名之曰人事學。”章學誠校讎之法最為劉咸炘所推崇,曰:“校讎者,乃一學法之名稱,非但校對而已,不過以此二字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章實齋先生全部學識從校讎出,吾之學亦從校讎出。”章學誠校讎思想的要義在于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劉咸炘則進一步指出校讎學的要義在于“辨體”與“知類”。所謂“知類”,章學誠將其視為治六藝群書的必要方法,曰:“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故學者之要,莫貴乎知類。”所謂“辨體”,即六藝與諸子群書之體例和義理源流。而劉咸炘則又將其推進一步,曰:“劉咸炘進以一言曰: 為學莫大乎明統,明統然后能知類。”劉咸炘認為章學誠“雖亦言統,只明類而已。”而劉咸炘之“明統”不僅僅是六經諸子群書之體統,更是超越文史經典而上達先天性道之本體,也只有體悟此先天性道方能統貫各類事物,是為“知類”。劉咸炘私淑章學誠校讎之法,加之得之于家學的“先天之學”,又將其推致于“人事學”上,遂成就了劉氏四部融通的“推十學”。
馬一浮為現當代杰出的儒學大師,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現代儒學三圣”。馬一浮原籍浙江上虞,出生于四川成都,六歲隨父返浙,青年時游歐、留美、旅日,學貫中、西、印,自謂其學“初治考據,繼專攻西學,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又轉治佛典,最后始歸于六經”,倡導“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抗戰時期,馬一浮先生曾講學于浙江大學,以張橫渠“四句教”激勵師生“樹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馬一浮對古代書院教育十分向往,于1939年在四川樂山烏尤山側的烏尤寺內創辦復性書院,認為“學術人心所以紛歧,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同然焉。……教之為道,在復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于習而不知有性。”馬一浮倡導“六藝統攝一切學術”的學說,是以書院以六藝為教,意在講明性道,以深造自得為歸,培養通儒醇儒,曰:“講明性道當依六藝為教,而治六藝之學,必以義理為主。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不分諸科,但可分通治、別治一門。通治明群經大義,別治可專主一經。凡諸子、史部、文學之研究,皆為諸經統之。”馬一浮始終堅持書院的獨立性和學術純正性,曰:“書院之設,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不隸屬于現行學制系統之內”。在1939年至1941年一年多的時間內,復性書院除馬一浮主講外,還邀請了熊十力、趙堯生、賀昌群、謝無量、錢穆等眾多名家大師前來講學,另刻有《儒林典要》《群經統類》等數十種書目,培養出如金景芳、張德鈞、杜道生等學者名家,其學統流衍,至今不絕。
結 語
浙學與蜀學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彼此交融互鑒、共榮共生,展開了長時間、多時空、跨維度的學術文化互動。二者之間的互動經歷了先秦萌芽、兩漢興起、兩宋繁盛、元明清初承續、清末近代轉型等多個主要的歷史階段; 其互動的實現形式主要包括文化內涵與特質上的暗合呼應、學術思想上的先后傳承、鄉賢和寓賢推動兩地文化交流等多種方式。浙學、蜀學相比于中原學術表現出自身強烈的特色與風格,并在與其交流論辯中影響乃至反哺主流學術,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與學術思想的進步。浙學與蜀學的歷史互動為地域學術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共同繁榮提供了上佳的研究樣本,也為進一步探索研究多元一體、和諧共生的中華地域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引入了獨具意義的觀察視角。
注釋:
②⑤舒大剛:《蜀學的流變及其基本特征》,《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 期。
③《史記·夏本紀》曰:“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載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3 頁。
④羅泌:《路史》卷三二“論三易”引《山海經》佚文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
⑥⑦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27、2201 頁。
⑨⑩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625~3626、3514 頁。
?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2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