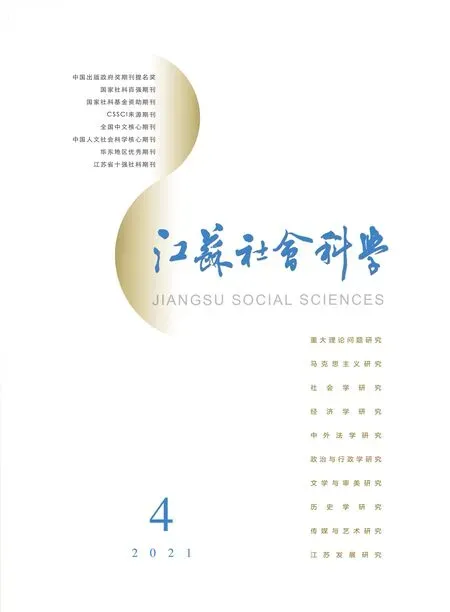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三重邏輯及當代價值
梅景輝 駱祥慧
內容提要 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價值邏輯”三個維度,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進行哲學維度的探討并結合時代背景予以考察,能夠深刻闡釋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在當代的現實意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繼承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精髓,是通向“真正的共同體”的重要環節,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對于當代社會發展的時代價值,為當代世界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
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維度對以“人的依賴關系”為主體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和以“物的依賴關系”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深刻的剖析,深入挖掘了古希臘羅馬城邦思想、黑格爾“國家”核心觀念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烏托邦式設想的理論精髓,逐步構建了以“人的本質”為核心的共同體思想。縱觀馬克思經典原著,德語“Gemeinde”“Gemeinschaft”“Gemeinwesen”的含義均指向“共同體”,但此三個詞在實際運用中蘊含著不同的含義。“Gemeinschaft”“Gemeinwesen”皆包含“共同”的語意,都由詞根“Gemeinde”延伸而來。“Gemeinschaft”更多運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本源共同體”和未來社會的“真正的共同體”,因此,有學者從“沒有異化、沒有階級所有”這一維度去理解“Gemeinschaft”的含義。“Gemeinwesen”意指以共同體為基礎的所有制,如政治社會和國家。但馬克思并未在文本中直接解釋何為“共同體”,因為“共同體”在詞源學意義上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在馬克思的思想視域中,共同體是生產力推動下的人類生存模式,其建構不僅是哲學問題,而且是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因此,只有從“歷史、理論、價值”三個維度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進行文本探討與實踐分析,才能跨越時空,比較馬克思所處時代語境下的共同體含義和當代社會多樣化共同體的理念,契入“人類發展”的核心問題,在新時代歷史坐標中充分展現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對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啟示意義。
一、歷史邏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淵源
想要深刻理解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就必須追根溯源,梳理其理論生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并闡述其內在邏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理論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哲學家在政治領域的探討。
1.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共同體思想:共同體思想的萌芽
古代哲學家孕育出“共同”與“整體”的思想。赫拉克利特認為,“logos”為永恒的世界秩序,宇宙是“萬物自同”的整體,這種“整體”的思想蘊含了共同體思想的萌芽。古希臘哲學家從倫理學的角度對共同體問題進行探討,他們開始追求現實中永恒的價值——“善”,試圖找到“善”的最大公約數,并在邏輯的思辨中發展共同的“善”,即從哲學的角度追求“至善”,從政治學的角度推崇“共善”。
在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維護公民共同利益的“城邦共同體”,是“共善”思想的實踐形式。蘇格拉底從倫理維度打開了探討“共同體”思想的大門。他認為,“共有制度”是城邦共同體中最大的“善”,即共同占有同樣的物品,建立財產公有制度,從而達到城邦的統一[1]〔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黃穎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頁,第45—51頁。。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城邦共同體思想中的“共善”的色彩,在《理想國》中構建了由哲人統治的小國寡民的理想城邦制度,勾勒出獨具特色的“烏托邦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將城邦分為統治者、衛國者和生產者三個等級,其中統治者由極具智慧的哲學家擔任。柏拉圖認為,三個等級間有著各自的分工,城邦公民各司其職才能獲得共同的“善”,但他對于這一共同體如何實現并未做詳細說明[2]〔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黃穎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頁,第45—51頁。。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只有生存于“共同體”內,才有其存在的意義。他在《政治學》中指出,城邦國家是囊括一切社會團體、以實現“最高的善業”為最終目的的共同體。在辨析個人與城邦的關系時,他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城邦共同體”思想。他認為,在處理個人與共同體的關系時,既要肯定維護城邦共同利益的必要性,又要肯定維護個人私有財產的重要性。由此形成了以追求“共善”為目的、個體通過分有“共善”而擁有道德的共同體思想,即個人只有處在城邦中才具有價值和意義。他認為,在財產共有制度上不應追求絕對的整體性,而應當發揚樂善之心,追求“產業私有而財務公用”[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9—13頁。。亞里士多德將“城邦共同體”的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雖未能挽救古希臘城邦制度的衰落,但對后人的共同體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古羅馬時期的西塞羅深受古希臘“德性共同體”思想和斯多亞學派“自然法”和“世界國家”思想的影響,立足于國家的現實,從“共同體”的維度闡述了對政治國家的認知。“國家乃是人民的事業,但人民不是人們某種隨意聚合的集合體,而是許多人基于法權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4]〔古羅馬〕西塞羅:《論共和國》,王煥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第87頁。他認為國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天然的聚合性,將“國家”等同于“人民的事業”。國家這種共同體不是柏拉圖《理想國》中任意的人群集合,而是基于法律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形成的穩定的政治共同體。西塞羅認為,國家不是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建立的,國家的發展不應該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決定,所以王權統治和貴族集團統治下的國家具有不穩定性。反之,“如果在一個國家里,同一事物對大家都有利,在這樣的國家里最容易達到協和一致”[5]〔古羅馬〕西塞羅:《論共和國》,王煥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第87頁。。西塞羅認為,“混合政體”最大程度地滿足了人民的共同利益,從而保障了國家的穩定性。西塞羅基于羅馬共和國歷史對政治共同體思想的探討,雖局限于政治領域,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宗教共同體”向“契約共同體”的轉化:政治共同體的思想建構
隨著中世紀宗教的興起,基督教逐漸成為歐洲人的精神支柱,歐洲構建了以信仰“上帝”為核心的“宗教共同體”。只要歸屬于“宗教共同體”,不同性別、年齡、地位的信徒在上帝面前都同樣渺小和平等。個人與共同體的關聯基于由信徒對上帝的盲目崇拜而產生的精神聯系,依托于教會舉辦的宗教團體儀式。此種“宗教共同體”阻礙了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但其倡導的仁愛、平等思想卻一直延續至今。
近代社會“契約共同體”的思想最早源自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他提出著名的非神學形態的“自然法”概念。在他看來,“自然法”至高無上,其立法的依據不再是按照神靈的指示,而是基于“自然狀態”中人的社會本性[1]〔荷〕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何勤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216頁。。自然法概念奠定了“契約共同體”的理論基石。在啟蒙運動時期,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思想家都以“自然狀態”和“自然法”為切入點構建“契約共同體”。這些思想家大多認為,在人們逐漸走出原始的“自然狀態”進入新型社會后,為了維護社會安定,人們簽訂了社會契約從而形成共同體。對人們處在何種“自然狀態”、“共同體”權力如何分配等問題的不同回答,體現了啟蒙運動思想家對近代政治制度設計的不同理念。霍布斯認為,自然狀態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戰爭”源于人的本性——趨利避害的利己欲,為了結束“戰爭”,人們需要“共同體”來制約人的本性,所以必須讓渡個人權利給代表共同意志的某一個人或者某一集體,簽訂社會契約,從而形成強權共同體。“國家”的主權者(君主)擁有著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如“利維坦”(威力無比的海獸)般的國家的誕生對人們的行為起到約束作用,從而維護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生命安全[2]〔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1頁。。洛克認為,人生存的“自然狀態”不是戰爭狀態,而是自由和平狀態,但這種自由不是肆意妄為,每個人都有捍衛私有財產和生命安全的權利。為了保障個人利益不受到傷害,大家都應共同遵循每個個體皆可使用的“自然法”,個人的行為受到理性的“自然法”的約束,從而擁有更廣泛的自由。洛克在《政府論》里指出了“自然法”的主要內涵——“人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3]〔英〕洛克:《政府論》(下冊),葉啟力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頁。。因此,要通過契約建成“共同體”,從而更好地維護個體權利。相較于霍布斯君主集權的政治思想,洛克更傾向于君主立憲式的分權學說。盧梭是“契約共同體”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人的“自然狀態”應當是原始的公有關系,沒有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人生而平等且自由。但私有制的產生,打破了這種祥和的狀態,人們不得不在平等的前提下簽訂契約,組建利益共同體,從而保障共同體成員的權益。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盧梭“契約共同體”的簽訂基于人人平等,提倡“主權在民”,共同體的權力掌握在每一個成員手中,共同體代表著人民的“公意”,共同體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同時,個人權益也只能在“契約共同體”內才能得到實現[4]〔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9—21頁。。縱觀歷史,雖然并未有任何團體簽訂成立共同體的“契約”,但自然法派思想家關于“契約共同體”的思想極具進步意義,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對于構建“共同體”制度以保證個人利益的渴求,推動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構建。
3. 黑格爾國家主義共同體思想: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思想邏輯建構
黑格爾在一定意義上傳承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共同體思想,但他也吸收了契約共同體的相關理論。他從抽象思辨的角度出發,打破市民社會與國家相統一的傳統共同體解釋框架,指出市民社會和國家不可混淆。一方面,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東西”[5]〔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53頁。,代表作為“神”的意志的絕對理性精神。這就意味著,國家作為代表絕對精神的共同體,其制度的制定和未來的發展不受任何個人主觀意志的影響和控制,具有客觀合理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5頁,第254頁。,國家代表著人們共同的現實利益。也就是說,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具有同一性,個體是國家的一部分,離開了國家的個體是無法界定的,“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2]〔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5頁,第254頁。。黑格爾認為,倫理性是存在于個人意志的自由精神,也就是說,個體只有成為國家公民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按照這一思想邏輯,個人必須遵從共同體的統一意志,因為人生來就被打上了國家公民的烙印,遵從國家意志是個體與生俱來的內在屬性,而國家意志不會被任何個體改變。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衍生物是其不可分割的分支,國家的屬性決定市民社會的發展方向,國家是市民社會內在目標的體現。
《萊茵報》時期之前,馬克思也認同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國家是代表倫理理性的共同體、個人在國家這一共同體中得到自由的思想。但在對現實進行考察后,馬克思很快發現黑格爾國家觀具有的矛盾性和虛假性:國家代表的不是公眾的普遍利益,而是將統治者的特殊利益上升為普遍利益,具有欺騙性。這種從先驗理論出發所構建的“國家共同體”思想,無法正確把握“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實質含義和現實關系。應從物質基礎和人本學出發,顛倒黑格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觀點[3]〔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頁。。
4. 空想社會主義的藍圖:對共產主義共同體的反思與展望
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生活在這一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批判了資本發展造成的失業、貧困、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他們基于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從衣食住行等方面闡述了對福利共同體社會的構想,并將這些天才的想法以試驗的方式付諸實踐。大量涌現的“法郎吉”“新和諧公社”“烏托邦島”“太陽城”等共產性質的理想共同體,閃耀著和諧平等的福利思想。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堅信,只有生活在共享共有、勞動自由的共產主義共同體中,人們才能擁有真正的幸福。
在現代化技術支持下,建立智慧園區的總體構想,綜合考量地塊信息化差異。其一,應用系統層,主要包括園區控制云、園區管理云和園區服務云;第二,應用支撐平臺層;其三,網絡通信層;其四,智能感知層;其五,基礎設施層。
傅立葉有關“法郎吉”公社的暢想,是空想社會主義對未來共同體形式的美好設想。“法郎吉”源于希臘文,意指“有規則的矩陣”。誠如其名,這一共同體有其嚴格秩序,每個“法郎吉”公社的“最佳人數”為1800。公社內部明文規定選舉平等、人人勞動、同工同酬、集體消費、義務教育等規章制度。這些理想制度消滅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收入差異、分配差異和城鄉差異[4]《傅立葉選集》第2卷,趙俊欣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27—236頁。。這一共同體基于對未來公平社會的暢想,也凸顯了對勞動本質的追求,即勞動不應是一種被剝削的行為,而應是一種主動的享樂。但是“法郎吉”公社保留了私有財產和私有制,想通過實驗的方式和平進入理想共同體,這一脫離實際的理論導致美國近30個“法郎吉”公社實驗均以失敗告終。不同于傅立葉,英國的歐文對未來共同體社會的構建,徹底否定了私有財產[5]《歐文選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56—368頁。。現實中,由于大部分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統治階級(資本家)手中,被統治者(無產者)逐步喪失勞動積極性,階級間矛盾不斷激化。唯有把生產資料徹底公有化,才能從根本上消滅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新和諧公社”是歐文理想的試驗田,這一共同體取締了私有財產和階級壓迫,勞動者回歸自由自覺的勞動生活。但這一脫離物質基礎的和平實驗方式只存在短短數年就以失敗告終。總體來說,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從政治公平、飲食公平、教育公平、住房公平、公共醫療公平乃至服裝公平等各個層面詳細勾勒了未來共同體社會的樣貌。雖然這些理想化的設計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對市民社會共同體弊端的抨擊與對未來理想共同體的天才構想,卻深深影響著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的靈感來源。
二、理論邏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內涵
“共同體”作為一個廣泛使用的概念,在不同文化、不同時代和不同語境下含義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在此探討“共同體”,不是探究這一詞匯的明確定義,而是回到馬克思文本中對其進行考察。目前,學者們大多從“三種社會關系”的維度解讀馬克思共同體思想,但這只是切入該思想的一種理路,馬克思一生都在不斷完善其共同體思想。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大量使用“共同體”概念,是要突出人在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中實現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不是最終的解放,政治共同體不能代表普遍利益,馬克思由此揭示了國家具有“虛幻性”。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虛幻的共同體”源自市民社會所帶來的人的普遍異化,“勞動是為每個人設定的天職,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1]〔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頁。,所以必須揭露“資本家共同體”的虛幻性,通過社會變革徹底消除異化,才能走向真正的共產主義,完成人的復歸。《德意志意識形態》闡述了民族分工所帶來社會形態的差異,描述了原始時期的“部落共同體”、奴隸社會時期的“古代古典共同體”、封建時期的“封建的共同體”等社會形態,按照社會關系將人類社會分為“自然的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他在批判中構思未來社會將何去何從,由此提出走向“真正的共同體”,構建其共同體理論的基本雛形。《共產黨宣言》闡述了著名的“自由人聯合體”概念,指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馬克思的研究重心聚焦于本源形式共同體。他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深刻探討了市民社會前的“亞細亞共同體”“古典古代共同體”“日耳曼共同體”。恩格斯也沿著這一理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詳細探尋人類社會共同體的起源和古代共同體的樣貌特征。
從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生成脈絡來看,他并非孤立靜止地關注和考量人的生存,而是結合特定歷史階段并立足唯物史觀,把現實的人置于不同社會關系的邏輯中予以考察研究。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邏輯對應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規律,表現為不同的“共同體”形態,我們唯有緊扣唯物史觀,從人類社會發展的三種社會關系[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725頁,第725頁。和五種所有制[3]〔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5頁。發展階段的雙重維度全面探討馬克思共同體思想,方能探究其本質內涵。
1. 前資本主義——“自然的共同體”
“自然的共同體”是馬克思在論述“前資本主義形態”時提出的,是對私有制產生前不同共同體形式的概括總結。這種最初級的共同體并不是人們有意為之的,而是自然進化的結果,它證明了人類自起源至今一直依托共同體而生存,也有學者將其稱為“本源共同體”。人們面對強大的自然,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維持生活,二是繁衍后代。因此,為了種族延續,人們自發形成以血緣和土地為紐帶的集體,通過合作獲得生存條件。在對不同形式共同體的探究中,馬克思指出,這種自然生成的共同體以不發達的生產力、分工和交換為背景,以血緣、語言、習慣為紐帶,以家庭為最基本單位,是“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725頁,第725頁。。人依賴于自然而存在,維持生存所需要的必備條件來源于自在自然;人同樣也依賴于共同體而存在,人的活動方式(如游牧、耕種)不由自身所決定,而是由共同體的群體性質所決定。這一共同體并非能推動社會發展,只是旨在保障自給自足和生存需要的自發聯合。但“自然的共同體”的自身局限性也體現在對自然的過度依賴上,由此導致共同體具有不穩定性,不利于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隨著生產力不斷提高,獨立個體不斷發展,對人的依賴關系轉化為對物的依賴關系,“自然的共同體”必將走向解體。馬克思晚年為探索市民社會共同體何以產生,對“自然的共同體”進行進一步探究,依托大量史料解剖出前資本主義的三種共同體形式。其一是生成于東方世界的“亞細亞共同體”。土地是共同體公有財產,人們進行自給自足的勞動生產。馬克思從“單個的人”和“總和的統一體”與土地的關系深刻剖析這一共同體的實質。“單個的人”雖在共同財產——土地上勞動,但實質上不是土地的所有者,“總和的統一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實際的公社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這種東方專制下的共同體,“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換言之,個體相對于共同體不具備獨立性,只有臣服于統一體才能獲得土地財產,這一因素導致個體不具備與共同體相分離的條件。在這一共同體中,如果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那么即使統一體變遷,也不會改變其所有制關系,而且會不斷加強個人同共同體的緊密聯系,鞏固統一體的君主專制制度,所以,此種共同體不可能過渡到市民社會共同體中。其二是以古羅馬和古希臘為首的“古典古代共同體”。不同于“亞細亞共同體”,土地不再是“古典古代共同體”的根基,“耕地表現為城市的領土”[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城市則是成員的主要居住地,也是其軍事組織的基礎。個人和共同體關系緊密且相互依賴,但個人又具有相對獨立性。自由且平等的個體聯合組成共同體,共同體保障個體的生活。城市中土地財產表現為共同體公有土地和個體私有土地并存的雙重形式,“存在著國有土地財產和私人土地財產相對立的形式,結果是后者以前者為中介”[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但是,個體獲得土地的條件為歸屬于共同體,只有同時擁有私有者和共同體成員的雙重身份,才能朝著共同利益進行勞動聯合從而保障其集體的穩定性。這一土地財產的前提也決定了個人與共同體的不對等關系,個體(公社成員)“屬于”共同體,“這種‘屬于’是由他作為國家成員的存在作中介的”[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馬克思指出,“屬于”關系迫使公社與公社成員緊密聯合,個體自由是公社賦予的,所以個體自由是相對的,“個人被置于這樣一種謀生的條件下,其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個人必須維護想象中和現實中的共同利益。這種體制注定無法走向現代社會。其三是歐洲世界的“日耳曼共同體”。日耳曼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相隔較遠,公社只能通過集會的方式召集成員。相較于前兩者,成員對共同體的依附程度最弱。馬克思認為,這一共同體蘊含著生成市民社會的條件。語言、血統和歷史是單個成員間聯合的前提,但成員不再是公社的分支,而是獨立的有機體,“公社便表現為一種聯合而不是聯合體,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一種統一,而不是表現為統一體”[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在這里,私人土地沒有中介前提,完全屬于個人所有。這種公社的形式不以國家組織的存在為前提,這種公社基于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聯合,“它是被每一個個人所有者以個人所有者的身份來使用,而不是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羅馬那樣)來使用的”[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頁,第735頁,第726頁,第728頁,第735頁,第730頁,第730頁,第734頁,第736頁。。個體成員及其自由造成此共同體不具備穩定性,但也為市民社會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
2.資本主義社會——“虛幻的共同體”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分工的不斷完善,少數人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剩余財富,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銳,人們逐漸擺脫了對原有共同體的依賴,以人的依賴關系為根基的“自然的共同體”逐步土崩瓦解,走向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虛幻的共同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逐步轉移到少部分人手中,大部人逐步轉變為貧困的無產者。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實質上是虛幻虛假的,它表面上以“國家”的形式采取民主的方式捍衛國民的“共同利益”,實質上將資本家的“特殊利益”上升為國家的“共同利益”。在全面物化的社會關系中,無產階級作為被統治階級,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是不自由的、受限制的。在馬克思的文本中,“虛幻的共同體”往往代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和社會形態。
“虛幻的共同體”根源于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分工的不斷分化,其產生是為了調和勞動分工帶來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分工導致不均衡的分配(勞動和勞動產品的分配在數量和質量上皆具有不對等性)和社會階級不斷分離,而個體利益與所謂的共同體利益不一致所產生的矛盾也日益尖銳,“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1]〔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第29頁,第46頁,第65頁,第65頁。。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者)為了防止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犯,將本階級利益上升為普遍利益,以“國家”的名義調節日益尖銳的階級關系。馬克思從三個角度闡述了“虛幻”這一概念。第一,意識形態具有虛幻性,“普遍的東西一般來說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2]〔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第29頁,第46頁,第65頁,第65頁。。統治階級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和群眾的支持,必須將“共同利益”解釋為“普遍的東西”并將這一解釋灌輸到個體的觀念中。將統治階級利益冠冕堂皇地提升為社會的整體利益,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3]〔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第29頁,第46頁,第65頁,第65頁。,其實質則是赤裸裸地壓榨無產者們的剩余勞動。第二,市民社會中大多數人未獲得真正的自由。資本家們擁有自由,而對于數目眾多的被統治者而言,他們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事實上,“虛幻的共同體”的不斷異化導致工人不得不屈服于“物”的統治,不僅無法分享“共同體”的利益分紅,而且只能不斷地把個人權益讓渡給“國家”這一“虛假的共同體”。第三,多數社會成員與共同體分離。資本家的聯合體捍衛的是本階級的利益,對于廣大無產者來說,這種共同體不但不能保障私人利益,而且以“國家利益”為名嚴重損害了無產者的利益。這種宣揚“自由平等”的共同體,甚至無法保障無產階級的生存。誠如馬克思所言,“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4]〔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第29頁,第46頁,第65頁,第65頁。。
從應然和實然角度可以更深層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共同體”為何“虛幻”。應然是指人們對事物發展趨勢的設定,實然是指事物存在的現實狀態。人們常從應然視角審視實然,甚至混淆二者。標榜“普遍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恰恰刻意混淆應然與實然,所謂的“普遍”實質是統治者們的個人利益,并未體現出分工細化所帶來的個體之間不可分離、全面發展的共同利益。資本主義政黨正是利用這一點將自己的私人利益上升為公共的普遍利益,所追逐的是資本主義政黨的特權,其標榜的國家利益與廣大無產者的利益相矛盾。這種“普遍利益”對于現實的人來說,是異己的、虛幻的、抽象的,這種共同體也具有虛幻性,不能給普羅大眾帶來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3.“真正的共同體”——自由人聯合體
“真正的共同體”是馬克思的理論精華和價值旨趣,他對未來社會的描述并非烏托邦式的預設,也不是空洞的倫理構想,而是基于唯物史觀的通向人的最終解放的現實革命。“真正的共同體”在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雙重領域中實現了人的最終解放。其一,人在自然領域中獲得自由發展。在未來社會中,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將使人們擺脫自然界的束縛,勞動分工的消滅將使個體回歸自由自覺的勞動本質。其二,人在共同體內獲得自由發展。以往社會內的“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5]〔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頁,第29頁,第46頁,第65頁,第65頁。,即使借助“國家”形式完成了政治領域的解放,實質上大多數人仍無法獲得自由解放。而在未來的共同體中,不再有階級對立,個人以自身的特殊利益為單位進行聯合。這種自由人聯合體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6]〔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頁。。
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虛幻性”的同時,找到了走向未來社會的鑰匙——消滅分工。勞動本是人類自由自覺的活動,但分工出現后,勞動者只能在強加于他的特定范圍內生產,否則會失去生活資料,“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1]〔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頁。。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的共同體”應當打破勞動的特定范圍,個體不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勞動部門,而且可以選擇勞動時間,生產則由社會進行宏觀調控。在這一社會中,勞動回歸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再受到異化的支配,個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趨于統一。因此,“真正的共同體”必須是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統一體。也就是說,生產資料不再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共同體的目標也不再是捍衛某一階級的特權,而是保障每一個獨立的共同體成員愿景的實現。
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同體”應當建立于物質資料極其豐富的未來社會中,在其中,獨立個體的個性、尊嚴、權益能夠得到充分尊重。在他看來,真正的共同體應該有以下三種特征。其一,生產力高度發達,以公有制為基礎,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真正的共同體”中,生產與分工高度發展,社會生產資料人人共享,社會按照個人自由發展的需要制定不同的生產計劃。其二,社會成員自由自覺地勞動,社會財富按需分配。由于物質資料極其豐盈,在這一共同體中的人是自由的存在,其勞動不再受資本家的壓榨,可以自由能動地選擇職業,參與到社會生產的任一環節。勞動產品,不是按生產要素或勞動時長分配,而是按人的需求分配。其三,消除階級和國家,人民是共同體的主人。公有制完全消除了市民社會的階級矛盾,隨著矛盾的消失,作為調節階級矛盾工具的國家也將不復存在。個人不再作為某一階級成員存在于不可控制的共同體內,而是作為控制著自己生存條件的獨立體參與到聯合體中。
三、價值邏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創新性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頁。,人類共同面對現實問題,共享發展成果。在政治哲學視域中,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基于馬克思共同體思想,是對西方資本邏輯主導的虛假共同體的超越,是引導社會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的中國智慧。我們有必要探尋蘊藏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的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內涵和價值旨趣,從而把握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時代價值。
1. 以唯物史觀為根基,應對全球現實挑戰
唯物史觀貫穿于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社會的發展是由“現實個人”的實踐活動所推動的,歷史維度下社會關系的更替史就是共同體從低級至高級的演進史。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和三大社會關系,共同體的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中都有與之相對應的物質基礎。按照這一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石,以當今世界所遭遇的挑戰為歷史條件,以中國騰飛發展的大國經驗為實踐基礎,破解了人類社會面臨的多方面難題。針對治理、信任、和平、發展等方面的“四大病癥”,習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上提出“四大良方”,即建設“公正合理、互商互諒、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命運共同體,在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協同發展、互利共贏。
2. 以“共同體”為載體,聚焦人類發展問題
在馬克思的思想視域中,“共同體”作為人類社會關系的載體永恒存在,人唯有生存于“共同體”中方能獲得最終的解放。“共同體”既是人類進步的載體,又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基于對資本主義虛假共同體的批判,馬克思提出“真正的共同體”的理想愿景。遵循馬克思的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聚焦于“人”的發展前途,致力于緩解由經濟發展需求導致的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間難以調和的矛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以西方為主導的傳統國際治理觀,以“共同體”為人類存在的實踐形態,通過不斷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等多重聯合體,不斷推動人類社會的共生共贏。
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核心為“人”本身。生活在共同體中的個體,要處理人與自在自然、人與人化自然的關系問題,獲得最終的解放和自由,達到人對人本質的回歸。馬克思認為,“在真正的共同體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聚焦于民生福祉,其關切的不是某一國家或某一階級的特殊利益,而是將整個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作為研究的重大命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政治、經濟、安全、生態等各個維度聚焦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聚焦如何在當今世界創造人類美好生活這一時代命題。世界正日益緊密地連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面對資本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風險和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當今世界各國的共同進步貢獻了不一樣全球治理視角,即世界各國凸顯各自的優勢,打破發展壁壘,共享人類發展的成果。
3. 以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為價值旨趣
實現“人的最終解放”是馬克思的畢生追求,其共同體思想指向基于唯物史觀的人類解放進程。馬克思認為,“最終解放”就是人對人本質的徹底復歸,所以必須建立一種消滅現存共同體的聯合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頁。。基于此,馬克思認為,“真正的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其出發點為“現實中的人”,落腳點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檢驗標準為“人的本質的真正復歸”。但是,這種理想的共同體只能在階級和國家消亡后產生,難以在生產力有限的今天實現。縱觀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相互交融和博弈的狀況仍將延續較長時間,“無產階級時代”到來的條件尚不成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基于真理,立足現實,面對全球治理中的眾多挑戰,將“真正的共同體”作為價值旨趣,以“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3頁。作為發展目標,構建共惠的發展環境。
我們有必要對“真正的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進行學理辨析,從而把握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時代價值。從時空維度來看,前者提出于19世紀資產階級主導下的市民社會,后者則是立足于解決21世紀人類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在當今中國和世界的最新發展成果。從主體維度來看,前者是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聯合,不是某一國家或階級的聯合;而后者是以當今社會民族國家為主體,通過國家間合作達到共贏。從內容維度來看,前者要求階級和國家的消亡從而達到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后者著眼于不同制度、不同發展程度和發展道路的國家如何和諧發展。從實現方式維度來看,前者的實現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后者的實現方式是全球各國攜手共商共建共享。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體現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時代價值,為當代世界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證明了全球治理并非只有西方“資本至上”這一條道路。 在理論維度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并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文本中描述的未來社會的聯合體,但在實踐維度上,它是從不同的社會制度并存的現實社會形態走向共產主義“真正的共同體”的現實橋梁和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