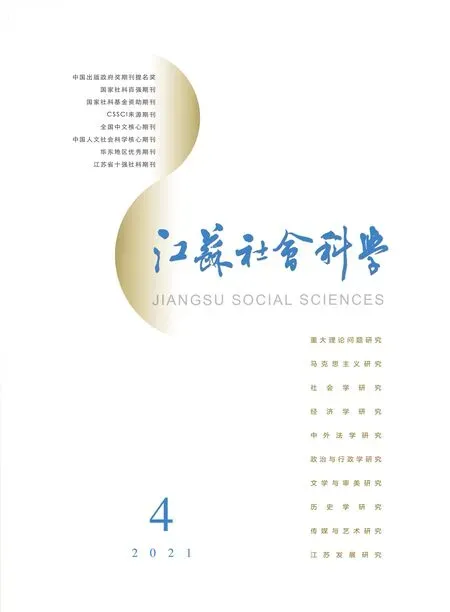青年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觀及其當代價值
賀銀垠
內容提要《〈倫理學原理〉批注》包含豐富的生命哲學。在其中,毛澤東主要從天人相通的自然主義視角看待人的生死問題,在中國古代生死觀與近代西方哲學的碰撞交融中發展出生死自然、發達身心和超拔個人的獨特的生命觀。青年毛澤東的生命觀源于對近代中國歷史任務的深刻反思,體現出其自覺將個體生命與爭取民族生存權、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緊密結合的鮮明的現實旨趣和價值關懷。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觀對于青年樹立理性的生命觀、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實現個人和集體價值的統一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十八大以來,黨將教育作為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1]習近平:《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頁。。毛澤東青年時代對生命價值的求索反映了一代優秀共產黨人成長成才的心路歷程,折射出青年共產黨人將個人生命和民族振興密切融合、互相促進的人生理想。1917 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而中國正經歷著軍閥混戰、社會動蕩。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西方倫理學課上,老師楊昌濟用德國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作為教材。作為學生的毛澤東花了近一年時間將全書通讀,留下超過12000字的批注。《〈倫理學原理〉批注》(以下簡稱《批注》)作為青年毛澤東獨特生命觀形成的關鍵性文本之一,對于新時代培育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具有典型教育意義。
一、生死自然:宇宙人生的基本規定性
生命問題之所以被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視為質疑問難的關鍵問題,是因為它不僅是個人道德鍛煉的修養功夫,而且切合中華民族救亡與啟蒙的緊迫現實需要。從個人修養來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及配套的舊式教育給人們灌輸恪守等級尊卑、順從家長權威的奴隸思維,使人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和積極進取之心。對此,毛澤東批評道:“惟少年亦多不顧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學講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問題都不求解釋,只顧目前稊米塵埃之爭,則甚矣人之不智!”[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從近代國家救亡圖存的具體實踐來看,鴉片戰爭后學習器物與文化、改革與革命、憲政與共和等各種主張,“你方唱罷我登場”,掀起一時熱潮又以失敗告終。毛澤東認為,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領袖既無內省之明又無外觀之識,他們所領導的改革和革命運動不過是在舊有政治體制基礎上進行細枝末節的修補,未能抓住世界的大本大源,因而是失卻根本方向的盲目沖動。其中,大本大源即指哲學和倫理學。“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增進個人修養和挽救民族命運都要求將生命問題視為重大的哲學、倫理學問題,進而為鞏固理想信念提供根本依據。
生死自然是青年毛澤東生命觀的核心。他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自然屬性是人之為人的第一屬性。人的生命過程首先是一種自然現象,生死變化遵循著自然的普遍規律。“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毀之法則。”[3]《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由此可知,毛澤東是從宇宙自然出發來理解人的生命和生死,帶有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學色彩。受樸素唯物主義宇宙觀影響,毛澤東認為,世界是物質和形式的結合,物質本身不生不滅,而物質存在的形式變化不居。人的生死不過是物質和精神聚與散的結果,物質聚而為人,解散以后又重新聚合為其他形式。“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滅,吾人固不滅也。不僅死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團聚而已矣。”[4]《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事物形式的聚散變化、接續構成了時間流變和人類歷史的階段性發展。“余意以為生死問題乃時間問題,成毀問題乃空間問題。世上有成毀無生死,有空間無時間。”[5]《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總之,從形式上論,人遵循自然的必然性,有生有死,不可悖逆;從物質本體上論,人同宇宙自然一樣只有形式變化,實則不生不滅。此時,自然主義的生命觀是毛澤東以豁達樂觀心態面對生命和生死的主要哲學基礎。
毛澤東關于既生既滅、不生不滅的自然生命觀同樣適用于對中華民族命運的關切。在談到民族生存時,泡爾生以人的生命類比國家發展,認為國家和民族作為宇宙的一部分必然遵循生死自然的規律,隨著歷史經驗不斷積累、社會風俗習慣逐漸固化,國家和民族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就日趨衰減,不免走向死亡。泡爾生說:“征之歷史,國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縮之時,若思惟行為一定之習慣,若歷史沿襲之思想,若構造,若權利,與時俱增。于是傳說足以阻革新之氣,而過去足以壓制現在,對待新時代之能力,積漸銷磨,而此歷史界之有機體,卒不免于殄滅。”[6]《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毛澤東大為感嘆,中華民族正處于此地位。但與泡爾生不同的是,毛澤東站在自然主義宇宙觀的立場進一步闡述了國家死與生的辯證規律,奠定了他求解中華民族生存問題、恢復民族生命力的積極心態。“國家有滅亡,乃國家現象之變化,土地未滅亡,人民未滅亡也。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7]《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第73頁,第171頁,第171頁,第242頁,第175—176頁,第176—177頁。在他看來,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帝國主義殖民侵略和封建統治分崩離析的雙重壓力,正處于民族危難的關鍵時刻,國滅族亡的生死問題現實地擺在所有中國人面前,是民族之憂。與此同時,民族危難只是國家形式和建制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征兆,制度形式的變化不僅不意味著中華民族本身的覆滅,而且是扭轉民族危機、重塑民族生命的契機。通過大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設新的國家,是使中華民族無憂的道路。民族命運之憂與無憂的辯證思維,正是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理論,既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又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毛澤東一方面深受德國哲學和倫理學影響因而發展出二元論的哲學觀,另一方面將生死的思考牢固扎根于中國傳統生命觀之中,在中西哲學和倫理思想的對話碰撞中鮮明地迸發出老莊哲學的光芒。眾多中國先哲主張從物質的自然聚散變化中理解宇宙和人生,早期的天命-道、五行-氣等理論莫出其外。老莊哲學的道法自然和辯證思維則將古代生死自然的理念發揮到極致。毛澤東關于生死自然和生死統一的理解大多來源于此。《批注》提出:“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絕時間感官者,想象即思維,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而言之,萬即一,變即常。”[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頁,第575頁,第75頁,第116—117頁,第178—179頁。不難看出,《批注》中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生命哲學帶有顯著的自然主義和相對主義色彩,距離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生命觀還有相當距離。
二、具足自我:個人主義的生命追求
盡管生死是人不可僭越的自然規律,但并不意味著人應該放任生死。在中國古代貴生思想和德國意志論哲學的影響下,毛澤東對自己和國人的生命主張進行了深入思考,他重視意志和自由的價值,強調精神獨立和個人自決,倡導過積極有為的人生。
青年毛澤東對個體的“我”的主張并非德國意志論和康德倫理思想的復現,而是在針砭近代中國人思想弊病基礎上進行的自主性發揮。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歷史的國家,文化習慣和社會心理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專制統治遺留下的弊病不可能隨著制度變更馬上消失殆盡。梁啟超提出過一個觀點:“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學之興廢系于一宗師,則常以一人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漸進,而重心移于少數階級或宗派,則常以若干人之首領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益進,而重心益擴于社會之各方面,則常以大規模的團體之組織分子為‘歷史的人格者’。”[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理解,國人在長期封建統治中形成了以一人為“歷史人格”的國民心理,喪失了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主體性意識,在政治上滿足于身處被治者的地位。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封建思想對個性的壓抑,直指當時社會上存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3]《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頁,第575頁,第75頁,第116—117頁,第178—179頁。等問題,人們因此在紛亂交替的社會變革中失去辨別能力和主動意識,“為強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卻其主觀性靈,顛倒之,播弄之,如商貨,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4]《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頁,第575頁,第75頁,第116—117頁,第178—179頁。。由此,他分析認為,近代中國數次變革的失敗是由于革命是局限于少數人參與的活動,沒有真正引起人民群眾的理解和同情。
《批注》中對于人如何生的主張是精神上的個人主義。泡爾生原文談到“彼等厭忌往昔之思想及生活法式,為以盲導盲,必欲以其獨立之意見,別辟世界”之時,毛澤東大發感嘆,“吾國二千年來之學者,皆可謂之學而不思”,“此吾國今時之現象”[5]《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頁,第575頁,第75頁,第116—117頁,第178—179頁。。毛澤東根據這段原文熱烈贊揚泡爾生的個人主義主張,大有引為知己的意思,實則泡爾生的真實意圖是調和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而毛澤東站在己方邏輯上視泡爾生為個人主義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個人之獨立和自由的熱烈渴盼。當然,毛澤東所倡導的個人主義雖出于近代資產階級精神,卻完全不同于自私自利的狹隘個人主義,而是指精神上的人格獨立和自決。其核心觀念在于“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個人”[6]《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頁,第575頁,第75頁,第116—117頁,第178—179頁。。
青年毛澤東以作為個人性主體的“我”來彰顯人格的獨立性,主張以“我”為中心,“我”的價值高于宇宙一切事物。“我”是指小我,即個人,與集體概念相對。毛澤東認為,從前主張無我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一定要主張有我。“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茍尤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尤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尤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也。”[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個人和集體是相互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既不存在抽空個人的集體,也沒有脫離集體的個人。但此時毛澤東認為,必須強調個人的地位和價值優先于集體。“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人我并稱,無起點,失卻本位。”[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毛澤東主張的個人本位思想,實際上構成了對中國傳統社會家庭本位、群體本位和國家本位的逆反。依照馬克思以人的存在方式劃分出的三大社會形態[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頁。,中國古代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制造出了人對人的人身依附關系。以家庭血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抹殺了人的獨立性和個性,主張國家和家庭的利益高于個人價值,片面強調個人對家庭和國家的義務責任,炮制出了“三綱五常”等虛偽道德。毛澤東堅決反對封建道德,對貶低和奴役個性的偽道德開展了猛烈抨擊。他指出,個人的地位和價值高于一切,人的所有行為選擇和道德評判都應以利己為唯一根本原則,奴役個體和個性的黑暗制度和封建思想應該被徹底廢除。當然,毛澤東對“小我”和利己原則的肯定以恢復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為限度,并不意味著導向徹底拋棄國家和集體的無政府主義方向。在強調人具有自我保存本能的基礎上,他肯定了人先天具有推己及人的良知。也就是說,利己與利他是一致的,利他作為內在良心天然地鑲嵌在個人的利己原則中,利他本身也就是個人通達利己的途徑。毛澤東的自利以利他、利人以利己的倫理主張實際上是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君子人格和墨家兼愛思想的新形式。
毛澤東指出:“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4]《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這就是說,發達身心、具足生活就是人作為獨立個體的道德律令。并且,倫理學上追尋的人生正鵠沒有統一標準,每個人應當根據自身資質秉賦的實際條件來調整發展自身的目標和方式。就毛澤東個人而言,立下真志、矢志踐行的就是發達身心和個性。在給師友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中,毛澤東表達了自己關于立志的愿望和苦惱。在他看來,立志不是隨便的事情,盲從大流或者渴羨他人都不是真正的立志。所謂立志必須經歷認真鉆研,得到一種關于大本大源的真理,然后堅定對其的信仰。“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5]《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正因為如此,那時毛澤東十分苦惱,“自揣固未嘗立志,對于宇宙,對于人生,對于國家,對于教育,作何主張,均茫乎未定”[6]《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在《批注》中,毛澤東進一步明確了追尋志向的步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種之知識,即建為一種之信仰,既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7]《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頁,第125頁,第218頁,第74頁,第76頁,第202頁。知之、信之、行之體現了毛澤東反對盲從、謀定后動的處世原則,也是毛澤東科學認識論的萌芽。如我們所知,盡管毛澤東對于立志有如此強烈的渴望和自覺,他實際上是在研究、比較和試驗思想界各種主義后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才樹立了真正的志向,并像他所說的,堅定不移地踐行了社會主義理想。
三、超拔個人:舍我其誰的浪漫品格
《批注》中的生命觀既與中國古代傳統中貴生輕死的生死觀一脈相承,又刻上了湖湘士風的深刻烙印。在面對生死大考時,毛澤東始終以貴生善生為前提強調珍惜生命和自我保存,同時將人生理想從狹隘的個人利益之中超拔出來,以理性思考賦予生死之變以豐富的浪漫色彩,并彰顯出在民族國家大義面前豁達生死的態度和樂于犧牲的精神。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保存自我及延續種族是人的本能,人應該遵從生物天性保存自身、強勁身心,而不應荒廢身體、輕視生命。這與儒家珍視人的生命、過積極有為生活的基本倫理取向和人生價值導向是吻合的。有學者認為:“儒家的生死觀具有強烈的功利、倫理色彩,在對待生與死的問題上總要與社會的價值取向與功名利益緊緊地交纏在一起。”[1]徐宗良:《當代生命倫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儒家生死觀的實用取向,一方面可以被視作世俗經驗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視為儒家君子超越生命有限性的一種途徑,即借助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使有限的個體生命獲得永恒價值。盡管毛澤東接受了傳統生死觀中貴生的基本主張,此時受近代西方思潮熏陶的他卻是從人的生物性本能出發來論證自我保存的價值。《批注》提道:“人類者,獸格、人格并備。”[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毛澤東認為,人作為智識更發達的動物保有動物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主張非自殺、反對不珍重身體的行為。圍繞長沙新娘趙女士花轎自殺事件,毛澤東提出,自殺僅在個人層面上具有自我保存的價值,即“消極之自殺,亦系為自存。因彼于遇事不能解決或愧悔其前日之罪過,以謂與其生不如死,故以一死了之。此生不如一念,即彼之自我也”[3]《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但從根本上來說,自殺導致身體死亡違背了自我保存的本能,不過是由于外部環境的迫使,在社會倫理層面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體現了毛澤東把個人生命和國家社會發展聯系在了一起,嘗試從政治革命入手尋找個人生命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具備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現實取向。
在“非自殺”的基礎上,毛澤東主張,青年人應該強健體魄、磨煉精神,達致身心具完的目標。1915年,毛澤東在第一師范的同學易昌陶因病逝世,他寫作兩首(其中一首篇幅長達40行)五言古風悼詩表達哀思。“胡虜多反復,千里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4]《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明確表達了毛澤東對同學因體弱早逝、無法實現救國抱負的遺憾。這件事情促使毛澤東開始反思學校重德智輕體魄的教育方針,列舉歷史上許多大才大智者因身弱或早逝導致德智不顯的例子來勉勵自己勤加鍛煉。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雜志的著名文章《體育之研究》更把體育鍛煉和個人修養與扭轉民族命運緊密聯系起來。“善其身無過于體育。體育于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后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5]《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他認為,體育鍛煉可以強健體魄,增強意志,改善民質,徹底改變中國國力衰弱、武風不振、民族體質孱弱的現象。為此,他還發明了一整套獨特的體育鍛煉方法,以達到“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目的。
當然,毛澤東強調的自我保存主要針對本能和實效的層面,他對待生命的基本態度無疑仍是基于理性思考基礎上的浪漫主義——死又何懼。毛澤東在《批注》中對生命的長度和厚度展開了深刻思考。他提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6]《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即是指,既然組成身體的物質永遠不會滅亡,那么死后人的身體也不會消失,不過是以另外方式存在于其他物質形態中。而人之所以恐懼死亡,只不過是因為生死之間的跨度過大,且人對死亡以后的未知事物總是心生恐懼。此時,毛澤東盡管沒有直陳死亡的意義,卻將死亡稱為奇事、奇境和奇遇。在他的奇人眼光中,死亡不僅不帶有痛苦和悲情色彩,反而是雄壯奇異的景象。“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以為壯,況生死之大波瀾何獨不知引以為壯乎!”[7]《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第219頁,第5頁,第58頁,第175—176頁,第174頁。
基于勇敢面對死亡、不懼死亡的浪漫想象,毛澤東對生死之問的回答是:敢于犧牲、樂于犧牲,在殺身成仁中發達個性。人生在世不斷趨向不可避免的終點,死亡時刻警示著人之有限性。因此,人的一生始終伴隨著對生命有限性的焦慮和超越個人死亡的沖動。古今中外哲人為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提出了諸多方案,卻始終無法超出借助宗教、作品、事業等外物延續生命的范圍。比如,泡爾生認為,個人死亡而人所留事業“不隨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頁,第171頁。。其實,將超越死亡的期望寄托于外物之上仍是一種精神固執,沒有實現對生死的真正超越。毛澤東在泡爾生原文旁批注:“即隨之而俱死亦何憾焉。”[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頁,第171頁。這種豁達態度構成了毛澤東對中國人長期以來精神不獨立、為外物所奴役的一種反叛。
總體上,青年毛澤東在《批注》中始終把對個人生命的思考與近代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生死存亡緊密結合,以爭取民族生存權作為個人生命的道德義務,同時也將社會變革作為個人生命和自由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他從近代民族國家生死利益的角度來考量個人生命,從哲學和倫理學層面解決了泡爾生拋出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兩難問題,實現了在服從民族國家利益的實踐活動中追求個人獨立性和自我價值發展的貫通。盡管以個人為立足點的生命觀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只占據一小段,但生死自然和生死統一的理念深刻地影響著青年毛澤東的哲學觀念;精神上的個人主義則是青年毛澤東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群眾史觀的萌芽,具有很大的進步性,而最為根本的關于生命的樂觀、自決、辯證、超然的態度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痕。盡管《批注》時期的毛澤東尚未接觸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的思想并不完全成熟正確,但是展露無遺的現實情懷決定了毛澤東的生命觀必定不拘束于純粹思維領域,而要到中國革命的風浪中踐行理想。在確立個人自決基礎上個體與民族命運相統一的生命價值后,毛澤東投身于中國社會大變局和民族獨立振興的試驗場,尋求個人價值和民族利益的相互促進、共同進步。我們應該注意,革命戰爭時期大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取代小我(個人的生命和價值)進入毛澤東的主體論域中,不應該視作大我對小我地位和價值的吞噬,而是小我發達個性、踐行理想、利人以利己理念的升華。到那時,毛澤東生命觀的探討范圍已經從自然意義上的生命擴展到象征意義上的生命,其生命觀承載著辯證唯物主義、反教條主義、走群眾路線、愛國主義教育等諸多內涵和目標,成為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理論資源和情感養料。
四、毛澤東青年時期生命觀的當代價值
培育正確的生命觀是在現代社會多元復雜的文化氛圍中處理好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所特別需要的,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毛澤東青年時期的生命觀是基于救亡圖存之時代任務和修養身心之人生旨趣而形成的思想結晶和倫理向標,它包含的關于生命價值的普遍尺度、原則和方法,在當今時代不僅沒有過時,而且仍散發著熠熠光輝,為有志于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樹立理性的生命觀提供了精神導引,為青年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和自我價值樹立了榜樣,為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和超拔指引了方向。
第一,為樹立理性的生命觀提供了精神導引。理性的生命觀不僅是任何時代個人正確看待生命、追問個體同一性的內在需求,而且是現代社會中個人特別需要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現代化的高速轉型和發展期,全球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使人們得以享受豐富的現代物質文化成果,與此同時也將人們充分暴露在物化、原子化、虛無化的現代性弊病之中,導致人們在多元社會中無所適從,耽于物欲橫流的享樂,輕視和荒廢生命,這對當代中國青年的精神造成嚴重侵蝕。毛澤東在認識到生死是不可逾越的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注重以拓展生命厚度、豐富生活內涵的方式克服個人生命的有限性,形成積極有為、置生死于度外的價值導向。他主張,人即便受自然律支配仍有自由意志,可以通過遂行意志、發達個性、磨礪品行來拓展生命的厚度。人如果樹立真正的志向、踐行理想,活著的每一天都有價值,就無所謂留有遺憾、懼怕死亡。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價值,使人不畏死,上壽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1]《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頁,第175頁。。相反的,人一旦渾渾噩噩、不對自己負責,那么生命長短與否也沒有很大區別。“其未達具足生活之正鵠因有此故,因有此故而未達具足生活之正鵠,曾何憾焉?”[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頁,第175頁。對于當代青年人而言,應該樹立理性的生命觀要求——正視生命的有限性,培養健康的心理和態度,珍視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發展和個人發展的雙重客觀規律性,準確認識現代社會個體成長面臨的新情況新挑戰,以踏實的自我培育和增進來回應生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和挑戰;思索和確立遠大的人生理想和志業,在把握時代脈搏和參與歷史宏業中獲得個人生命價值的延展。
第二,為青年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和自我價值樹立了榜樣。社會的現代化也就是人的現代化,即人不斷從物質的與精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個體和全人類自由的過程。經濟政治現代化并不是人的自由解放的唯一基礎,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價值實現仍是當今時代人的現代化的重要維度。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關于個人價值及其實現的主張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言仍不失其價值。人之本性大多趨利避害、喜樂惡苦,青年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善于發現抵抗的樂趣,有志于在磨礪鍛煉中發達身心。相較于從戰火硝煙中磨煉自我的革命先輩而言,當代青年成長于和平發展的時代,較少經歷歷史波瀾和社會挫折的淘洗,更容易產生安于現狀、趨樂避苦的軟弱性格,疏于對自我成長的磨礪和錘打。毛澤東所主張的樂于和善于在磨礪中發達身心的觀念對于當代青年培育堅強的自我主體意識、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榜樣示范作用。
第三,為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和超拔指引了方向。實踐證明,個人發展的方向總是與歷史發展的方向保持一致,個人價值的實現只有在主動把握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人民群眾的需要的基礎上才具備現實可能性。毛澤東個人的成長和成就正是這一歷史規律的生動體現。青年毛澤東自覺將個人的修養和生命與挽救國家民族于危亡結合起來,以天下興亡、學子有責作為自己至高的道德義務。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澤東提倡的為民族利益而超拔個人的犧牲精神更加明確地成為拯救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義務。那時,個人生命的犧牲再次被詩化、哲學化為浪漫景象,頻繁出現于毛澤東所作的詩歌和文章之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解放的革命活動本身也生動體現了毛澤東的革命浪漫主義生命哲學[3]李佑新、黃波:《偉人的終極關懷——論毛澤東的生死觀》,《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這種生命經驗仍向當代青年指示著,立志、求真和力行的根本方向和超拔個體生命價值的根本途徑在于將個體生命價值的彰顯和國家時代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將民族復興大業作為個人成長成才的終極指引,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