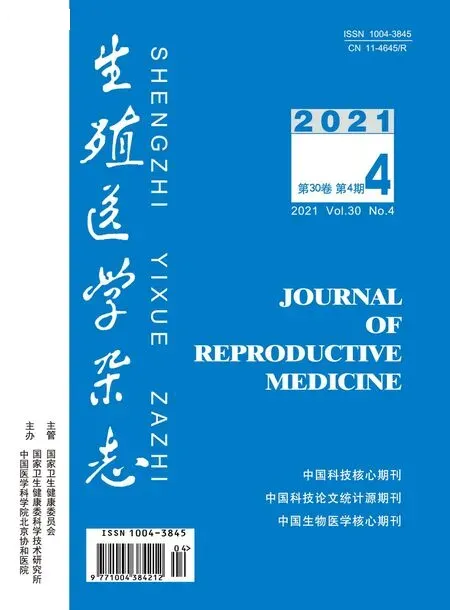兩種不同子宮內膜準備方案對FET周期單胎子代圍產期結局的影響
吳靜,黃劍磊,李博,王曉紅
(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婦產科生殖醫學中心,西安 710038)
隨著胚胎冷凍技術的發展與成熟,凍融胚胎移植(FET)逐漸成為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術。研究表明,FET周期復蘇后胚胎種植潛能、妊娠率及活產率等方面相較于新鮮移植周期更優[1-4],且因主客觀因素取消鮮胚移植的或鮮胚移植后剩余胚胎的,均可選擇FET,因此,FET的應用日益廣泛[5]。
子宮內膜準備是FET的重要環節,最常用方案為自然周期(NC)和激素替代周期(HRT)。NC方案是在自然排卵周期下監測卵泡及子宮內膜的生長,排卵后行FET,這一過程更符合人類自然生育規律,但易出現因卵泡內膜發育不同步或提前排卵而取消周期。HRT方案是外源性雌激素刺激子宮內膜達到理想厚度后外源性孕激素轉化,可控性強,簡單易操作,避免患者頻繁就診,備受青睞。但HRT方案不產生黃體,大劑量、長時間作用的外源性雌孕激素對胎兒安全性仍存在爭議。已有研究認為,兩種方案的妊娠率、流產率及活產率等幾無差別[6]。然而,不同方案圍產期子代安全性如何呢?查閱國內外文獻,報道較少。本文旨在對NC方案及HRT方案行FET的單胎子代圍產期結局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為臨床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分組
選取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就診、獲得單胎活產的FET患者為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1)FET周期;(2)獲得單胎活產的周期;(3)選取NC或HRT的子宮內膜準備方案;(4)黃體支持方案為陰道給藥聯合口服或肌注黃體酮。
排除標準:(1)子宮畸形;(2)關鍵統計指標不完善;(3)雙移植或序貫移植周期,即同一周期內先后移植兩種不同時期胚胎。
共納入符合標準的976個周期,根據不同的子宮內膜準備方案分為2組:自然周期(NC)組544例;激素替代周期(HRT)組432例。
二、子宮內膜準備方案
1.自然周期(NC):適用于月經周期正常、有規律排卵者。從月經第8~10天開始B超監測卵泡大小及子宮內膜情況,監測期間若內膜較薄,給予口服戊酸雌二醇(補佳樂,拜爾,德國)1~2 mg,1次/d。當卵泡≥14 mm時,檢測LH、E2及P水平,根據LH峰出現時間及排卵后孕酮水平確定移植時間,排卵后給予黃體酮陰道緩釋凝膠(雪諾酮,默克雪蘭諾,瑞士)每日一枚,聯合口服地屈孕酮(達芙通,雅培,荷蘭)10 mg,2次/d,或聯合肌肉注射黃體酮注射液(浙江仙琚)20 mg,1次/d,轉化內膜。排卵后第3日移植卵裂期胚胎,第5日移植囊胚。
2.激素替代周期(HRT):適用于月經周期不規律、排卵障礙者。月經周期第3天開始口服戊酸雌二醇(補佳樂,拜爾,德國)2 mg,1次/d,連續3 d;隨后改為 2次/d,連續3 d;最后3次/d,連續3 d,共9 d。若子宮內膜厚度<7 mm,則繼續口服戊酸雌二醇2 mg,3次/d,3~6 d;內膜厚度≥7 mm時,給予黃體酮陰道緩釋凝膠(雪諾同,默克雪蘭諾,瑞士)每日一枚,聯合肌肉注射黃體酮注射液(浙江仙琚)20 mg,1次/d,或聯合口服地屈孕酮(達芙通,雅培,荷蘭)10 mg,2次/d,轉化內膜。內膜轉化的第4天移植卵裂期胚胎,第6天移植囊胚。
三、胚胎解凍及移植
胚胎均采取玻璃化冷凍技術保存。卵裂期胚胎解凍后培養4~5 h移植,囊胚解凍后培養2 h移植。移植術后第13~15天查血β-HCG,β-HCG>10.0 U/L為HCG陽性。HCG陽性者在移植術后28~30 d首次經陰道B超了解宮內是否可見孕囊,有孕囊者診斷為臨床妊娠,同時核實孕囊數目。
四、評判標準與觀察指標
參照《婦產科學》[7],出生結局判斷標準:活產是孕28周及以上的活產嬰兒的分娩;胎齡<37周的新生兒為早產兒;出生體重<2 500 g的新生兒為低體重兒(LBW);出生體重≥4 000 g的新生兒為巨大兒。
主要觀察指標包括:早產兒發生率(胎齡<37周新生兒周期數/總周期數)、低體重兒發生率(<2 500 g新生兒周期數/總周期數)、巨大兒發生率(≥4 000 g新生兒周期數/總周期數)及剖宮產率(剖宮產周期數/總周期數)。次要觀察指標包括:新生兒性別比(男性新生兒周期數/女性新生兒周期數)、平均出生孕周、平均出生體重及平均出生身長。
五、統計學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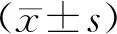
結 果
一、兩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976個周期,其中NC組544個周期,HRT組432個周期。統計結果顯示,兩組間女方年齡、男方年齡、不孕類型、不孕年限、不孕因素及BMI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而HRT組的AMH水平及PCOS患者占比均高于NC組,有統計學差異(P<0.05)(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s),n(%)]
二、兩組患者FET周期臨床實驗室數據比較
兩組患者移植次數、移植日子宮內膜厚度、移植日內膜形態及輔助孵化(AH)相比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但相較于NC組,HRT組的移植胚胎數及移植卵裂期胚胎占比均略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FET周期臨床實驗室數據比較[(-±s),n(%)]
三、兩組患者FET周期圍產期結局比較
兩組低體重兒發生率、新生兒出生性別比、平均出生孕周、平均出生體重及平均出生身長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而HRT組早產率、巨大兒發生率及剖宮產率均高于NC組,且具有統計學差異(P<0.05)(表3)。

表3 兩組患者圍產期結局比較[(-±s),n(%)]
四、兩組患者圍產期結局的多元回歸分析
在調整了AMH水平、PCOS患者占比、移植胚胎數及移植胚胎胎齡等混雜因素后,兩組的早產率無顯著性差異(P>0.05);而HRT組剖宮產率及巨大兒發生率仍高于NC組,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表4 兩組患者圍產期結局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討 論
近年來,多數研究表明,FET周期可獲得與新鮮移植周期相當甚至更高的妊娠率、活產率及更低的流產率,同時顯著降低了OHSS的威脅[2-4]。然而,隨著輔助生殖技術(ART)的發展與成熟,對ART助孕成功的定義已不僅限于理想的妊娠率及活產率,更加關注妊娠期及圍產期母兒安全。2016年Chen等[2]研究證實,PCOS人群FET與鮮胚移植相比子癇前期發病率顯著增加。2017年我中心周晶等[8]將3 961例單胎活產兒進行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與鮮胚移植相比,FET周期分娩的新生兒體重增加、巨大兒發生率增加、低體重兒發生率降低,與Vidal等[9]研究一致。2018年一項Meta分析同樣顯示,FET周期大于胎齡兒與巨大兒發生率顯著高于鮮胚移植組及自然妊娠組[10]。究其原因,Johnson等[11]認為新鮮移植周期促排卵產生遠超生理水平的雌激素刺激宮腔微環境改變,導致胎盤血管生成不足阻礙螺旋動脈的正常發育,最終引起前置胎盤、胎盤早剝、早產兒、低體重兒等發生率增加。然而,FET周期激素水平更接近生理狀態,為何仍會出現妊娠期高血壓、子癇前期、過期產及巨大兒等風險增加[12-13]呢?有學者認為,胚胎冷凍復蘇技術誘導胚胎表觀遺傳學的改變,進而影響其早期生長分化及子代宮腔內發育,出現產科并發癥[14-15]。最近亦有研究表明,FET周期上述并發癥可能與黃體缺乏相關。
在卵泡發育周期中,卵母細胞排出后,殘留的卵泡壁塌陷,卵泡膜的結締組織、毛細血管等伸入到顆粒層,迅速轉變為富含血管并具有內分泌功能細胞團的黃體。黃體細胞不僅產生妊娠必需的雌孕激素,而且產生松弛素、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及雌激素的血管生成代謝物等參與胎盤形成及母胎界面血管重塑的血管活性因子,這些活性因子還參與母體心血管系統對妊娠的適應與調節[16-17]。若黃體缺失,上述活性因子缺乏則子癇前期、子癇及胎兒發育異常等胎源性疾病的風險可能增加。NC方案指不用藥物干預的情況下自然排卵,排卵后FET,大部分患者產生黃體。而HRT方案是外源性雌激素刺激子宮內膜達到理想厚度后外源性孕激素轉化,一般不產生黃體。因此,從理論上講,相較于NC方案,HRT更易出現上述產科并發癥。臨床實際中是否如此呢?
本文將NC周期與HRT周期圍產期結局進行對比分析,一般資料中,HRT組的AMH水平偏高,可能與HRT組月經不規律、PCOS等患者占比更高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相較于NC組,HRT組早產率、剖宮產率及巨大兒發生率更高。調整了AMH水平、PCOS患者占比及移植胚胎數等混雜因素后,兩組間早產率無顯著性差異,而HRT組剖宮產率及巨大兒發生率仍較高。與上述理論分析基本一致。檢索國內外文獻,2019年 Ginstr?m Ernstad 等[18]研究認為,HRT方案行子宮內膜準備患者的妊娠期及圍產期并發癥風險高于NC或微刺激方案,可能與HRT方案中未產生黃體有關。同年Saito等[19]對105 234例FET周期患者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NC方案,HRT方案顯著增加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及胎盤植入等風險。2020年2月Singh等[20]對同類文獻進行了系統綜述,指出不產生黃體的HRT方案子癇前期、產后出血、巨大兒及過期產等風險增加,認為黃體對預防FET的產科并發癥有重要作用。
妊娠早期子宮螺旋動脈通過滋養層細胞的遷移、侵襲和替代內皮細胞,從高阻力、低容量向低阻力、高容量血管轉化,進而為胎兒提供充足的營養和氧氣。據報道,雌激素水平過高會抑制滋養細胞血管的侵襲[21],致子宮螺旋動脈重塑不全,胎盤血供缺乏從而導致胎盤源性并發癥[22]。在FET子宮內膜準備方案中,HRT周期需要補充外源性雌激素刺激內膜達到理想厚度,在胚胎滋養層細胞侵襲階段長時間攝入較大劑量外源性雌激素可能致螺旋動脈重塑異常,進而妊娠期及圍產期并發癥風險增加[23]。
50%~70%的PCOS患者存在肥胖、高雄激素血癥、高胰島素血癥及糖脂代謝異常等,可能干擾圍產期結局。研究表明,肥胖型較非肥胖型PCOS患者更易發生代謝紊亂,是妊娠期糖尿病和巨大兒發生率增加的獨立危險因素[24-25]。胚胎長期暴露于高雄激素環境中可能導致胎兒生長受限、低體重兒發生率增加[26]。對于糖代謝異常及胰島素抵抗的PCOS患者,孕晚期體內孕激素、胎盤生乳素等抗胰島素樣物質明顯增加,胰島素抵抗進一步加重,進而導致胰島β細胞失代償,最終發展為妊娠期糖尿病[27]。胎兒一直處于高血糖環境,會導致蛋白質與脂肪合成增加,分解減少,胎兒軀體過度發育,巨大兒發生率增加。本文中HRT組PCOS占比較高,但兩組患者間BMI無顯著差異;通常我中心基礎雄激素水平及空腹血糖水平正常、糖耐量及胰島素釋放試驗調整至相對正常才予以進入FET周期,且文中結果已將PCOS患者占比納入多元回歸模型矯正,以期將這一不平衡因素對結局的干擾降至最低,但仍不排除這類人群妊娠后出現內分泌紊亂及代謝異常,發生偏倚。
綜上所述,相較而言,兩種子宮內膜準備方案中,NC方案單胎子代剖宮產率及巨大兒發生率更低,圍產期結局更好。可能與HRT方案不產生黃體,缺乏對產科并發癥有重要預防作用的活性因子及外源性激素致使子宮螺旋動脈重塑異常有關[28],亦不排除PCOS人群妊娠期代謝異常對結局的干擾。因此,未來的研究中尚需大樣本量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同時對妊娠期并發癥進行系統分析,為這一臨床問題提供更多可靠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