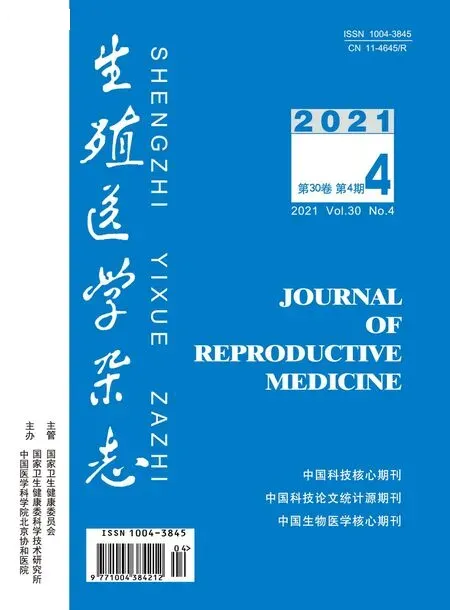被低估的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
卜祥靜,鄧姍
(1.銀川市婦幼保健院,銀川 750001;2.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內分泌與生殖中心,北京 100730)
病歷摘要
趙*,以“月經期腰部酸脹1年余,發現左腎積水復發1年,尿頻、尿急2月”為主訴于2020年7月17日入院。
患者2011年因“右側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原發不孕”于當地醫院行腹腔鏡下卵巢囊腫剝除+宮腔鏡檢查+輸卵管通液,術中輸卵管情況不詳;2016年自然受孕,因胚胎停育行清宮術。
患者2017年因月經期腰部酸痛檢查發現左側腎積水(考慮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給予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治療3個周期后積水消退。隨后開始接受輔助生育治療。2018年6月在我院取卵12枚,取卵后出現卵巢過度刺激而取消新鮮胚胎移植;后于2018年9月和2019年6月分別移植2枚凍胚均未成功,現存凍胚兩枚。
2019年7月再次出現月經期腰部酸脹感,嚴重時有惡心、嘔吐、下腹陣發性刺痛。2020年5月前出現尿頻、尿急癥狀,2020年6月查泌尿系B超提示左側積水伴輸尿管上段擴張,CT泌尿系成像(CTU)結果:左側輸尿管盆段與子宮左側壁分界不清晰;左側輸尿管、腎盂腎盞明顯擴張積水;左腎皮髓質變薄,灌注和排泄功能減低(圖1);Urea 4.77 mmol/L、Cr(E) 77 μmol/L、肌酐清除率85.42 ml/min;考慮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復發。門診予GnRH-a治療,同期囑患者泌尿外科會診,注射達菲林3.75 mg以縮小病灶;7月16 日于泌尿外科門診行膀胱鏡檢查,見膀胱粘膜光滑,未見明確腫瘤、結石,同時放置左側輸尿管D-J管。
此次入院后完善相關術前評估:血CA125 38.8 U/ml、CA19-9 28.1 U/ml、AMH 4.28 ng/ml。盆腔常規核磁共振(MRI):馬鞍形子宮;子宮底水平盆腔左側占位病變,似位于左輸尿管走形區,不除外子宮內膜異位病變(圖2)。
充分腸道準備后擇期行宮腹腔鏡聯合檢查和治療,術中見:子宮正常大小,左前壁膀胱腹膜返折處1 cm×1 cm質硬內膜異位病灶,局部與膀胱頂關系密切;后壁與側盆壁腹膜、直腸系膜粘連,子宮直腸窩封閉,以左宮骶韌帶粘連、浸潤為重;左輸尿管盆段最粗處直徑約1.5 cm,僵硬,與盆后壁致密粘連、活動度明顯受限。從高位游離左輸尿管至子宮動脈水平,局部組織堅韌、子宮動脈、左輸尿管及主-骶韌帶渾然一體,分離十分困難,分次切除左輸尿管表面僵硬內異病灶,擴張的輸尿管上段略有回縮。請泌尿外科大夫臺下會診:鑒于目前左腎盂重度積水、皮質明顯變薄且腎動脈纖細,腎功能可能已明顯受損,左輸尿管盆段受累部分長約4~5 cm,只能行輸尿管膀胱吻合術,因吻合口張力較大而出現尿瘺或返流繼發感染等并發癥的風險存在,目前左輸尿管D-J管置入后已解除泌尿系梗阻問題,建議3~6個月后完善腎血流圖評估左腎功能再決定后續治療。另術中證實雙側輸卵管通暢無積水,鞍形子宮無異常占位。切除膀胱腹膜反折左側深部內異病灶,直徑約1 cm,術后排尿和腸道功能恢復順利,如期出院。

左:冠狀位;中:橫斷面;右:血管灌注圖圖1 CTU顯示左腎積水,皮質變薄,灌注和排泄功能減低

左、右圖均為橫斷面;紅色箭頭示擴張的輸尿管;白色箭頭示輸尿管旁混雜回聲結節,符合深部子宮內膜內異癥影像圖2 MRI提示左側宮旁深部子宮內膜異位癥及擴張的輸尿管
術后繼續GnRH-a治療,3個月后查腎血流圖提示:左腎圖呈低水平延長線型;右腎圖呈高水平延長線型。腎小球濾過率(GFR,ml/min):左腎22.03,右腎48.77。擇期在泌尿外科行開腹左輸尿管膀胱再植術,術中探查左側輸尿管,見輸尿管中上段明顯增粗擴張,輸尿管壁水腫,沿輸尿管向下游離,自髂血管水平以下輸尿管與周圍組織粘連嚴重,仔細游離至髂血管下5 cm處無法再向下分離,遂于此處切斷輸尿管備用。膀胱注水后打開膀胱,膀胱活動度好,遂游離部分膀胱卷瓣并懸吊,4-0可吸收線行輸尿管膀胱再植,內置D-J管,術后尿管留置2周。另由于GnRH-a副反應明顯,改用地諾孕素維持治療。
臨床討論
一、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的臨床特點
在診斷為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癥的患者中,約有1%位于膀胱輸尿管,其中多數為膀胱受累[1]。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比較罕見,患病率約為0.1%。在泌尿系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中,輸尿管受累占10%[2]。近50%的患者可無典型臨床癥狀,而無癥狀的腎積水可能導致隱匿性腎功能喪失;25%患者可表現為腰部絞痛,15%左右患者可有肉眼血尿[1]。
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病理生理是異位內膜反復周期性出血導致炎癥反應、組織纖維化、粘連等,異位病灶種植浸潤輸尿管外膜、肌層或內膜,受累組織增生及纖維化導致管腔狹窄,引起輸尿管梗阻、腎盂積水、腎功能受損。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病灶多為單側(85%),其中左側最為多見(60%)[3],這種不對稱性也符合子宮內膜異位癥在其他部位分布的普遍規律。
輸尿管深部子宮內膜異位癥(DIE)根據病變侵犯輸尿管的位置分為:(1)外在型(80%)[4]:由于輸尿管周圍的異位病灶刺激輸尿管周圍組織增生纖維化,形成粘連,瘢痕組織壓迫輸尿管,病變只侵犯輸尿管外膜,造成梗阻,好發于輸尿管遠段1/3,其次為中段1/3,近段輸尿管較少累及[5]。(2)內在型(20%):異位的子宮內膜直接浸潤輸尿管肌層,固有層和輸尿管腔,可形成息肉樣或類瘤腫物,多來源于淋巴管和靜脈轉移[6]。內部型和外部型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均可導致輸尿管狹窄和梗阻、輸尿管積水和腎積水,嚴重可導致患側腎功能受損。
另一方面,Seracchioli等[7]提出可根據病灶的組織病理學成分將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分為異位內膜型和纖維組織型。異位內膜型,占此類分型的77%,指在輸尿管管壁內或輸尿管的上皮周圍組織中存在異位的子宮內膜成分,包括含有多量纖維成分的病灶;而纖維組織型占23%,此類僅有纖維組織成分。臨床中病例前者多見,提示輸尿管也可能是異位內膜細胞附著的原始部位之一。Knabben等[8]提出的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臨床分期方法是目前唯一的臨床分期系統。
二、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的術前評估
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可通過盆腔和腎臟超聲檢查,明確有無輸尿管病變、以及輸尿管積水和腎積水的發生[9]及其程度。超聲可以顯示輸尿管從腎盂至子宮旁組織的前部的走形[9]。經靜脈腎盂造影、CT和MRI等檢查可以明確輸尿管狹窄部位以及子宮內膜異位癥病灶位置,為手術治療提供判斷及依據。根據影像檢查提示重度輸尿管狹窄或梗阻的患者,建議在術前對腎臟行造影檢查以確定腎臟是否可以保留。必要時需行膀胱鏡檢查,評估病灶位置至輸尿管開口的距離,進而確定切除病灶時是否需行輸尿管部分切除和/或輸尿管膀胱吻合術[8]。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劉青等[10]報道,在其16例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中,超聲均提示輸尿管擴張腎盂積水,其中單側輸尿管中-重度積水伴腎盂擴張12例,雙側輸尿管中-重度積水4例。CT泌尿系成像(CTU)或磁共振泌尿系水成像(MRU)顯示輸尿管下端梗阻15例。所有患者行腎動態核素檢查,以腎小球濾過率(GFR)評估腎損傷程度,其中半數(8/16)已發生中-重度損傷(GFR<25 ml/min),其中包括腎臟無功能5例(5/16,GFR<10 ml/min)。16例輸尿管DIE患者中,9例行膀胱鏡檢查均無陽性發現,其中行輸尿管鏡檢查者1例,進鏡2 cm后無法通過。
三、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的手術方式
造成輸尿管解剖結構異常和梗阻的主要原因是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病灶的纖維化成分[9],所以手術治療是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的首選,目的是切除病灶、恢復輸尿管解剖、改善腎功能[1]。手術治療的效果與病灶類型、部位及其嚴重程度有關,術者的經驗及手術技巧也很重要。根據輸尿管的受累程度,手術方式可采用輸尿管周圍粘連松解、輸尿管切斷吻合、輸尿管膀胱吻合術,腹腔鏡因具有放大、精準的特點,是輸尿管子宮內膜異位癥手術的首選方案[11],但對于部分重度粘連的復雜病例,還需要采用傳統的開腹手術進行輸尿管膀胱再植術。進行輸尿管手術前,建議置入輸尿管支架,目的是盡可能降低術后發生輸尿管扭結和瘺的風險。
病例警示
根據患者既往輸尿管梗阻在短期藥物治療后即能緩解,且沒有局部手術史,此次癥狀復發時間不是很長,且術前放置D-J并無顯著困難,原以為能夠完成患側輸尿管的游離,最壞的可能是需要行輸尿管膀胱吻合。而術中輸尿管的梗阻受累病灶長度、近端擴張程度、與后腹膜的粘連程度,均超出預期。如果當時勉強行輸尿管膀胱吻合,由于間距較大,且輸尿管壁組織受積水影響不完全正常,即便采用膀胱皮瓣延長技術仍存在吻合口瘺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對挽救左腎功能的價值并不確定,如果左腎功能不能恢復,或繼發感染等最終需要手術切除則有得不償失的意味。
所幸我們此次采取的是微創手術方式,中止于無并發癥的階段是合理的,待3個月后根據左腎功能的情況再決定行輸尿管膀胱吻合是穩妥的。除此之外,也存在左腎功能無法恢復,撤除D-J后逐步梗阻衰竭的可能,必要時行左腎切除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