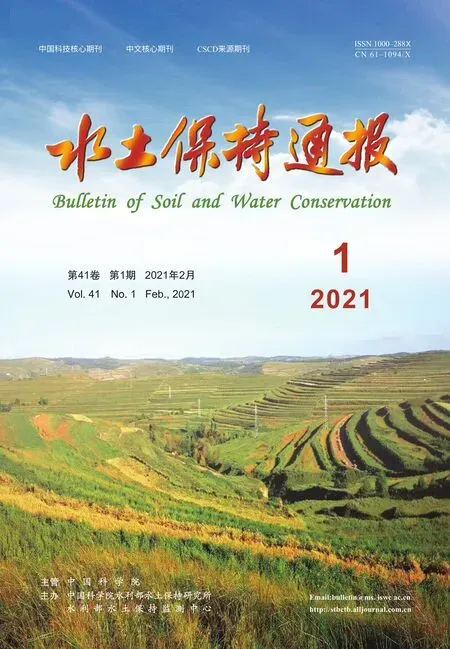巖溶槽谷區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坡地產流產沙規律
張彩云, 蔣勇軍, 馬麗娜, 汪啟容
(西南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 巖溶環境重慶市重點實驗室, 重慶 400715)
巖溶槽谷區巖溶面積1.32×105km2,是中國南方巖溶面積最大的地區[1],同時也是石漠化治理效果相對較差的地區[2],相比較其他巖溶地貌類型區,巖溶槽谷區生態環境惡劣,加上槽谷區的經濟條件差,有限的土地資源養活了巖溶槽谷區約8.00×107的人口[1],坡耕地(>8°)面積為20 064.2 km2,占巖溶總面積的15.2%,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高位水資源泄露,缺水現象嚴重,干旱頻發,強烈的巖溶作用和不合理的人為活動,加重了槽谷區的水土流失,石漠化治理難度大。水土流失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3-4],導致土地退化和自然生態系統遭到破壞[5-6],嚴重影響了生態環境和人類的發展[7-8]。增加植被覆蓋度已被廣泛認為是治理石漠化地區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徑之一[9]。不同的植被類型對地表徑流和水土流失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4],合理的植被類型不僅對減少對地表產流產沙具有積極作用,還能增加當地農戶的經濟收益,提高農戶參與石漠化治理的積極性。因此,定量評價巖溶槽谷區坡地產流產沙規律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
產流產沙過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地質地貌、地形、氣候、植被覆蓋和人類活動)[6,10-12],其中,降雨是導致地表產流產沙的直接動力因子[13],降雨落到地面產生濺蝕[14],使土壤顆粒產生位移[12],并隨著徑流,沖刷和搬運泥沙導致水土流失。一般認為降雨量、雨強、雨型、歷時顯著影響著坡面產流產沙[12]。在降雨強度較低的情況下,土壤流失量與降雨強度成線性關系,而在較高強度下成非線性關系,另外降雨強度越大,坡面徑流量越大,泥沙流失量越多[15]。O.González-Pelayo等[16]基于西班牙9個巖溶坡地的徑流小區研究了降雨強度與坡面徑流和土壤侵蝕的關系后得出,當降雨強度增加到20 mm/h時,徑流量和土壤流失量成倍數增加。戴厚全等[17]研究表明,隨著巖石裸露度的增加,產流產沙量先增加再減小。Peng等[18]基于徑流小區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產流產沙量由大到小為:放牧地、火燒地、耕地、混合植被地和幼林地。另外,研究表明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對水土流失的影響不同[19-20],合理的土地利用,不僅能夠提高土地生產力,增加經濟收益,還能有效控制和減緩水土流失。此外,還有許多學者進行了室內模擬試驗,如Fu等[21]根據在室內模擬了降雨對亞熱帶白云巖巖溶坡地產流的影響,對比低強度降雨,坡面產流和地下產流對高強度降雨的響應更為敏感。整體來看,學者們從降雨、巖石裸露率和土地利用類型等方面對產流產沙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是關于巖溶槽谷區坡地產流產沙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選取重慶市北碚區中梁山巖溶槽谷區為研究基地,根據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修建了4個標準徑流小區,監測徑流小區降雨量和產流產沙數據,分析自然降雨條件下坡面的產流產沙特征,降雨等級、降雨特征對坡面產流產沙的影響,并探討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產流產沙特征。以期為槽谷區坡面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理論基礎。
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重慶市北碚區中梁山,地理坐標位置為106°54′—107°27′E和28°46′—39°31′N。巖性為三疊系系嘉陵江組(T1 j)石灰巖,地貌上表現為典型的“一山三嶺兩槽”的“筆架”式地形,海拔高程480~640 m。土壤以三疊系系嘉陵江組發育的石灰土為主,土層厚度15~100 cm,厚度不均。氣候為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年均降雨量為1 090 mm,每年4月至10月是該地區的雨季,約占全年降雨量的80%,降雨季節分配不均。地下水向東北方向匯入嘉陵江。中梁山槽谷土地面積為37.2 km2,主要的土地利用類型是林地,耕地,建設用地,面積分別為21.6,13.3,2.3 km2。由于研究區耕地面積小,大量的土地已被開墾,加上槽谷區坡度較大,極易發生水土流失,造成石漠化。
2 研究方法
2.1 水土流失監測徑流小區的設置
根據研究區的人類活動的差異性和地質特點,在2017年,選擇4個典型的土地利用方式(耕地、林地、果園、竹林地),在坡度一致(20°)的坡面修建了4個5 m×20 m的水土流失監測徑流小區(見表1)。小區四周下挖到基巖,用磚塊和混泥土堆砌至地表以上20 cm,以防止與外部的徑流和泥沙發生交換。徑流小區下方設有50 cm×40 cm×30 cm的集水池,集水池排出口裝不銹鋼三角堰,用于計算流量。4個徑流小區的物理性質較為一致(表2)。根據當地耕作習慣,本研究中的耕地春季種植西紅柿、夏季種植包菜和花椰菜、秋季種植白菜、冬至種植蘿卜。上述幾種作物都需要占據較大的面積,在種植時采用與當地種植習慣保持一致,采用成行種植。果園地在橘子樹開花前進行除草,后期不定期進行除草。

表1 徑流小區基本信息

表2 徑流小區土壤物理性質
2.2 數據采集
(1) 降雨監測。監測時段為2018年,降雨量數據用天津氣象儀器廠有限公司生產的DAVIS Vantage Pro2型自動氣象監測站進行實時監測,精度為0.1 mm,測量間隔為15 min。
(2) 產流監測。每個收集池內安裝有自動水位記錄儀(美國HOBO公司,U20-001-04),采用壓力測量原理,每15 min記錄一次數據。
(3) 產沙監測。每場降雨后采集泥沙,帶回室內用燒杯進行靜置沉淀3~5 d左右,隨后倒掉上層清液,靜置風干后稱重,得到坡面產沙量。
2.3 數據分析方法
利用spss22.0軟件研究次降雨特征(次降雨量、降雨歷時、30 min最大雨強、平均雨強、降雨侵蝕力)對產流量和產沙量的影響。其中降雨侵蝕力[22]由公式(1)—(3) 計算得出。
R=EI30
(1)
Ek=0.119+0.873lgIk
(2)
(3)
式中:R為降雨侵蝕力〔MJ ·mm/(hm2·h)〕;I30為30 min最大雨強(mm /h);Ek為k時段的降雨動能〔MJ/(hm2·mm)〕;Ik為k時段的降雨強度(mm/h),在計算中去自然對數;Pk為k時段的降雨量(mm)。
3 結果與分析
3.1 降雨特征
在試驗(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監測時段內,總降雨量為1 009.8 mm(圖1),雨量豐富。降雨主要集中于4—10月,占全年降雨量的83.58%,9月降雨量最高為157.9 mm,最低值為1月的16.9 mm。

圖1 研究區2018年各月降雨量
由表3可知,觀測期間共有131場降雨(根據實測產流特點,將降水過程中時間間隔超過6 h定義為兩次降水過程,其中,有效降水(即每個徑流小區均有產流產沙發生)18場,雖然僅占總降雨場次的13.53%,但占降雨總量的51.58 %。按照氣象部門對降雨的劃分,全年暴雨(≥50 mm)2次,大雨(25~49.9 mm)7次,中雨(10~24.9 mm)9次,其余場次為小雨(0.1~9.9 mm)。根據徑流的小區的降雨量和產流產沙的監測數據,當降雨量達14.3 mm,各徑流小區都有地表徑流產生,降雨雖然是導致產流產沙的主要因素,但是并非每場降雨都會導致水土流失。

表3 研究區觀測期間降雨事件
3.2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產流產沙特征
在相同的降水條件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坡面產流量差異顯著(表4)。各徑流小區的地表總產流量均呈現為:耕地(35.35 mm)>果園地(31.51 mm)>竹林地(2 348 mm)>林地(19.57 mm)。4個徑流小區的物理性質較為一致(表2),但土地利用方式不同。這說明在相同的降雨條件下,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由于受人類活動的差異,導致植被和土壤狀況的不同,其蓄水保土的能力也存在差異。耕地由于擾動頻繁且植被覆蓋度低,對雨水的調控能力弱,徑流量對降雨量的響應最敏感;果園地中雖種植柑橘樹,但由于株距過大,相比較林地和竹林地減少雨滴動能的能力較弱,所以對降雨量的響應較為敏感。肖金強等人研究表明林地植被可對地表徑流的消減率高達89.3 %[23],研究區林地的植被覆蓋高達80%,樹木枝葉繁茂,必然導致林冠截留增大從而減少到達地表的降水量,短時強降雨的影響被削弱,但降水總量到達一定程度,才能形成地表徑流。

表4 研究區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坡面產流產沙
4個徑流小區中,徑流系數在3.12%~5.70%之間,與彭韜等人基于典型巖溶區陳旗河流域6類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徑流小區觀測的地表徑流系數(0.01%~12.81%)相近[24]。然而,與非巖溶區相比,徑流系數遠低于非巖溶區(20%)[25-26]。巖溶區由于特殊的地上地下二元結構,到達地面的降水并非全部轉變為地表徑流,絕大部分降水進入土壤層后,經裂隙,管道等進入地下河網[27],而非巖溶區,到達地面的降水幾部轉變為地表徑流,因此,巖溶區的徑流系數明顯小于非巖溶區。
在相同的降雨條件下,坡面產沙量表現為:耕地>果園地>林地>竹林地。耕地的侵蝕模數是果園地、林地和竹林地的2.10,1.30,2.35倍。表明耕地是研究區水土流失的主要土地利用類型。耕地的植被覆蓋率最低為15%,且經過一系列的田間管理措施(整地、翻耕和除草等),土壤擾動頻繁,產流產沙量最高。相對比與受人類活動干擾強烈的耕地,林地的植被覆蓋率高達70%,一方面由于植被的冠層對雨滴濺蝕具有截留和緩沖作用[28],降低了侵蝕動能,另一方面植物的根系深扎土壤,可以降低坡面徑流的侵蝕能力[29],其豐富的有機質還有利于雨水滲漏,植物根系和低等草本植物在降雨過程中阻礙了坡面徑流攜帶的泥沙[30],最終造成坡面產流產沙量遠低于耕地和果園。巖溶槽谷區的土壤侵蝕模數明顯低于黃土高原地區(400~10 000 t·km2/a)。巖溶區的土壤侵蝕模數小,但波動變化范圍較大,這與彭韜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24]。土壤的形成過程是極其緩慢的,尤其是巖溶地區,形成1 cm的土壤需要上千年的時間,加之,巖溶區土壤土層薄,分布不連續,裸露的巖石與土壤交錯分布,盡管巖溶區的土壤侵蝕模數低,土壤允許流失量小,且巖溶地區還存在泥沙隨著壤中流和裂隙流的地下漏失,同等的土壤侵蝕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巖溶槽谷區由于其特殊的地形(陡坡和谷地),貧瘠的、較薄的土壤分布在四周的坡面上,當地居民為了滿足生活需要,不得不陡坡開墾。因此,在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應結合區域特點,因地制宜綜合治理。
3.3 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對次降雨產流產沙的響應
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表覆蓋度下,坡面產流產沙對次降雨的響應存在明顯不同,受地表覆蓋物、植被生長狀況等因素綜合影響[31]。為了進一步了解土地利用類型對坡面產流產沙的響應,分析了18場有效降雨下的坡面產流產沙(圖2)。通過對比相同降雨場次下,不同土地利用的產流產沙量的變化可知,二者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即在同一降雨場次中,4中土地利用類型的產流量增加,產沙量也隨之響應的增加,且耕地的產流量和產沙量在不同有效降雨場次中最大;果園地的產流量和產沙量次之;竹林地和林地的產流產沙在不同降雨場次中差異較小。以9月24日的暴雨為例,在相同的降雨條件下,竹林地的土壤侵蝕模數比林地的產沙量少0.24 t km2/a,竹作為一種特殊的森林資源,具有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圖2 2018年研究區有效降雨條件下坡面產流產沙特征
由圖2可知,在有效降雨條件下,耕地和果園地的產流產沙量遠大于其他兩種土地利用類型。耕地經過一系列的田間管理措施(整地、翻耕和除草等),土壤擾動頻繁,在相同的降雨場次中,耕地的產流產沙量最高。果園在橘子樹的栽培過程中,按照株行距2 m×3 m挖定植坑,株距較大,且還要保證樹盤底部無雜草,土壤擾動較為頻繁,產流產沙量次之。
人為擾動較多的坡面土壤侵蝕模數較高,故產流輸沙量較大,水土保持效果不佳[32]。因此,在安排農事活動時,盡量避開高強度降雨,減少嚴重侵蝕事件的發生。與農作物的經濟效益相比,果園收益相對較好,但水土保持效果相對較差,因此,在巖溶區種植柑橘是建議輔助修建魚鱗坑、套種等整地方式以蓄水保土。
3.4 降雨等級對坡面產流產沙的影響
不同降雨等級下坡面徑流量占比不同,在中雨條件下,產流量最大的是耕地,其次是竹林地、果園和林地;在大雨條件下,徑流量最大的是竹林地,其次是林地、果園和耕地;在暴雨條件下,徑流量最大的是果園,其次是耕地、林地和竹林地(圖3a)。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不同降雨等級產生的土壤流失存在較大差異(圖3b)。耕地由大雨和暴雨產生的侵蝕量占年總侵蝕量的79.99%,其中僅5月2日和9月24日2場降雨產生的侵蝕量占耕地全年侵蝕量的32.26%,表明坡耕地坡面侵蝕主要大雨和暴雨引起的。徑流量和產沙量與高強度降雨緊密相關,雖然暴雨占總降雨場次的1.53%,降雨量占年降雨總量的11.03%,但產流量占年產量量的42.28%,產沙量占年總產沙量的33.42%。在中雨類型下,雖然中雨造成的坡面徑流量、產沙量占年總徑流量、產沙量的比重較小(占年徑流總量的16.61%,產沙量占年總產沙量的20.47%),但是由于中雨的降雨次數多,其造成的泥沙流失也不可忽視。

圖3 降雨等級與產流產沙的關系
3.5 次降雨特征與產流產沙相關性分析
降水是坡面水力侵蝕的動力來源,也是誘發喀斯特坡地土壤侵蝕的主要驅動力,各降雨特征對產流產沙產生一定的影響[33]。因此,本文將不同土地利用下的坡面產流產沙與次降雨特征進行相關性分析(表5)。對于耕地而言,坡面徑流量、產沙量與降雨量均表現為極顯著相關(0.940,0.809,p<0.01),產沙量與I30表現為極顯著相關(0.886,p<0.01);林地和竹林地的徑流量和產沙量與降雨量表現為極顯著相關,與I30表現為顯著相關;果園的徑流量與降雨量和I30表現為極顯著相關,產沙量與降雨量表現為極顯著相關,與降雨強度和I30表現為相關。將降雨侵蝕力與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產流、產沙量分別進行了相關性分析。降雨侵蝕力與耕地、果園、林地和竹林地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67,0.649,0.566,0.451,表明坡面徑流量隨著降雨侵蝕力的增大而增加,除與耕地的徑流量呈現顯著正相關外,與其他3種土地利用方式的坡面徑流的相關性不顯著;降雨侵蝕力與坡面產沙量的相關性與徑流量一致,但二者的相關性不顯著。降雨量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坡面徑流的影響最大,是坡面產流的主要影響因素。I30對耕地和果園產沙量的影響最大,降雨量對林地和果園產沙量的影響最大。

表5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坡面產流產沙與降雨特征相關分析
4 結 論
(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徑流小區坡地徑流量為:耕地(35.35 mm)>果園地(31.51 mm)>竹林地(23.48 mm)>林地(19.57 mm);地表產沙量耕地(3.37 kg)>果園地(2.60 kg)>林地(1.60 kg)>竹林地(1.43 kg)。耕地的坡面產流產沙量最大,果園次之,竹林地的水土保持效果較好。
(2) 徑流量和產沙量與高強度降雨緊密相關,雖然暴雨占總降雨場次的1.53%,降雨量占年降雨總量的11.03%,但產流量占年產量量的42.28%,產沙量占年總產沙量的33.42%。中雨占年產流總量的16.61%,產沙量占年總產沙量的20.47%,但是由于中雨的降雨次數多,其造成的泥沙流失也不可忽視。
(3) 降雨量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坡面徑流的影響最大,是坡面產流的主要影響因素。I30對耕地和果園產沙量的影響最大,降雨量對林地和果園產沙量的影響最大。此外,不同土地利用下的產流產沙與降雨歷時的相關性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