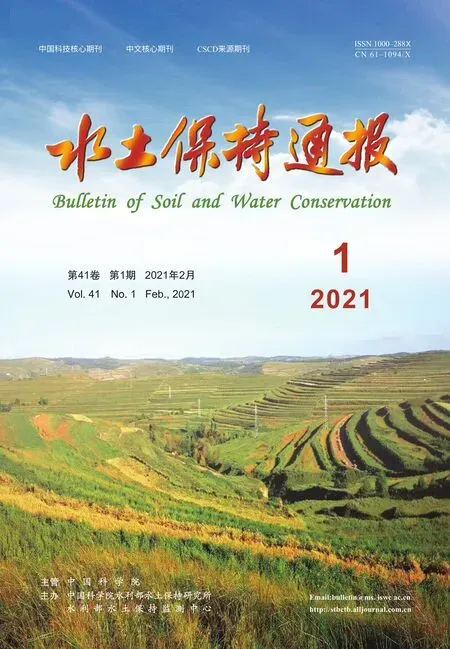基于公平視角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量化研究
崔寧波, 生世玉
(東北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隨著農業活動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粗放的糧食生產方式和對農作物產量的過度追求,導致中國耕地數量和質量急劇下降,威脅農業生產的經濟生態平衡。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立耕地保護生態補償機制是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十九大報告又指明,健全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全面實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事實上,確保耕地生態安全是耕地保護最為重要的內容,耕地生態補償遵循耕地生態安全的理念指引,在制度上為耕地生態安全提供了保障[1],其中補償標準測算的科學性直接決定了補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補償機制建立的核心[2]。
近年來國內外關于耕地生態補償標準的研究逐步成為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熱點。最早的科斯理論和庇古理論分別指出通過市場價格機制或稅收等政府干預行為,使產生外部性問題的生產經營者對總成本收益與私人成本收益間的差額進行補償[3],其內涵是通過賠償產生生態負外部性的行為或獎勵產生生態正外部性的行為,來實現生態保護的外部性內部化。但耕地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必然存在過度使用、主動保護意識淡薄、無人監督等通有的屬性問題。因此,在賠償耕地負外部性上,國家和各地方政府主要通過法律或條例形式提高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行為的成本;在獎勵耕地正外部性上,生態系統服務理論的代表學者Costanz等[4]、Pagiola等[5]認為可以借助政府轉移支付等手段,對水源涵養、凈化空氣、維持生物多樣性等耕地生態功能外部效益進行補償。伴隨理論研究的深入,補償標準的實際測算也分為兩類,一類以治理耕地生態負外部性所付出的成本為依據,包括耕地產出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直接成本等[6-8]。然而這類測算方法往往忽略了耕地資源的稀缺性與其創造的生態價值,導致測算出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不能反映其提供生態服務的邊際成本。另一類以獎勵耕地資源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為依據,1997年,Costanza等[4]提出將生態系統的17種服務功能分成4類,謝高地等[9]在此基礎上引入生態功能的市場價格作為生態補償標準,提出了“中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任平等[10]、蘇浩等[11]、Xie等[12]進一步利用當量因子法分別測算了四川省、河南省及中國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確定了相應的補償標準;柯新利等[13]、趙青等[14]基于糧食安全視角,通過計算糧食安全價值、耕地生態服務價值等確定了糧食耕地的生態補償系數及標準。這類將耕地資源創造的生態價值作為補償標準,并能據此確定其補償優先等級的測算方法,在日漸成熟和完善后,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主流方法。
現有耕地生態補償的研究已經頗為豐富,但在運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測算補償標準時,將耕地資源本身創造的生態價值或非市場價值作為補償標準,往往忽略了耕地經營者的自身生態消費,難以兼顧補償主體和受體的公平性。為此,本文首先對耕地生態補償行為和標準的理論依據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利用當量因子和水足跡模型評估剔除耕地經營者自身消費的生態系統服務非市場價值,并基于不同經濟支付能力進行修正,得到東北三省區耕地生態補償的最終標準和迫切程度,以期為東北地區耕地生態保護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本文選取包括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在內的東北三省區為研究對象。研究區域總面積約1.52×106km2,總人口約1.17×108人,氣候類型屬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寒冷漫長,夏季溫熱多雨,從東南向西北年降水量和平均氣溫逐漸遞減,地貌以平原、丘陵和山地為主,地形三面環山,平原居中,耕地總面積約2.71×107hm2,占全國耕地面積的10%,其中黑龍江省約1.59×107hm2,吉林省約7.00×105hm2,遼寧省約4.10×105hm2。區域條件特殊,作為全國最大的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占全國20%以上,擁有稀缺黑土地資源約1.85×107hm2。但近60 a來,對耕地資源的不斷開發和化肥農藥等農資的過度使用,土地耕作層土壤有機質含量平均下降1/3,部分地區下降50%[15],土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后勁不足等問題對耕地的可持續利用造成較大影響。為保障東北地區耕地資源的持續利用及耕地保護者的切身利益,引導各方進行耕地生態環境建設,需要對耕地經營者所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非市場價值部分進行相應補償。
1.2 數據來源
本文參照2012—2019年的《黑龍江省統計年鑒》《吉林省統計年鑒》《遼寧省統計年鑒》《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國水資源公報》《中國農村水利資源》、東北三省政府工作報告等,得到東北三省區的經濟發展、耕地利用及農業生產相關數據作為耕地生態補償標準模型計算源數據,具體包括東北三省區耕地面積,人口,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產量、價格,地區生產總值,主要食品消費量,水資源供需情況,城鎮化水平及恩格爾系數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機理
多數現有補償標準測算的研究之所以忽略對補償主體和受體的公平性,主要還是對耕地生態補償的本質內涵不清。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由于私人邊際成本和收益與社會邊際成本和收益并非等同,依靠自有競爭很難達到整個社會空間的福利最大化,當出現外部性時,需要政府部門對二者差額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償,以實現其外部效應的內部化。耕地作為農業生產最基礎的物質載體,不僅對維持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還能夠提供調節、供給、支持、文化服務等多種生態服務功能。從這些生態服務供給和需求的角度來分析(見圖1),僅考慮農民進行耕地生態保護的邊際私人收益(耕地生態服務需求),其與保護成本(耕地生態服務供給)的均衡點為M;而同時考慮到耕地資源的生態社會效益,則均衡點為N。而M點的耕地生態服務供給和需求均小于N點,在耕地公共物品外部性存在的情況下,根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效用最大化原則,實際供給的生態服務會小于社會需求,要想增加供給服務,就要對耕地的生態外部性進行補償,使邊際私人收益曲線上移,不斷接近邊際社會收益,達到N點的供需平衡。

圖1 耕地生態補償的經濟學分析
將耕地所提供的生態服務貨幣化,區域a為農民進行耕地保護自身消費的生態服務價值,b為整個社會消費的耕地生態服務價值,b—a為農民在剔除自身消費后向社會所提供的剩余生態服務價值。從公平視角出發,為激勵耕地生態服務供給方的保護行為,應當對其遭受的損失部分進行補償,但原材料供給、食物生產等生態服務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其經濟價值,不應算作補償的內容。因此,綜合考慮,首先運用當量因子法測算研究區總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非市場價值,再構建水足跡模型測算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的自身消費系數及非市場價值消費,最終得到耕地生態系統服務非市場價值的剩余部分即為補償標準。
2.2 耕地生態服務價值測算
本文借鑒謝高地等[16]學者在該領域已取得的相關研究成果,根據研究區不同省份主要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單產、價格水平等求得單位生態系統當量因子的價值量(Ea),然后結合當量因子權重,計算耕地生態服務價值和非市場價值(Ae),具體公式見田義超等[17]研究。
2.3 供給方自身消費的耕地生態服務價值
由于耕地這一公共物品正外部性的存在,從公平視角出發,應當對耕地生態服務供給方遭受損失的部分進行補償,即剔除自身消費后的外溢價值。本文構建基于水足跡的耕地生態服務價值自身消費模型,通過將農村水資源需求(水足跡)和水資源供給水資源可利用量)相比較得到生態服務價值消費系數,進而得到耕地經營者自身消費的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
(1)
式中:Am代表供給方自身消費的耕地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元);Dw代表農村水資源需求(水足跡);Sw代表農村水資源供給(水資源可利用量);Ae代表耕地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元)。
剔除供給方自身消費后的耕地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An(元)為:
(2)
式中:An代表剔除供給方自身消費后的耕地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元)。
2.4 基于支付能力的生態補償標準修正
生態系統服務的外溢價值是在考慮公平性基礎上得到的理論生態補償額度,但是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力度、環保意識及對生態的保護能力不同,其對耕地生態補償的支付能力也不同。借助S型皮爾生長曲線,并采用恩格爾系數來量化研究區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計算公式為:
(3)
最終耕地生態補償的標準C(元):
C=An×r
(4)
式中:C為最終耕地生態補償標準;r為耕地生態修正補償系數;En為城鎮恩格爾系數(代替非農業人口生活水平)。
2.5 生態補償優先級的確定
生態補償優先級是用來量化不同區際間補償的迫切程度,考慮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差距,避免生態補償資金在個別地區過于集中。生態補償優先級越高,說明該區域為了提供優良的生態服務,使得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應該優先得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較低地區所支付的生態補償;生態補償優先級低,則說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區域生態服務功能較低,應當率先向生態補償優先級較高的地區支付生態補償。整體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區域耕地補償迫切程度相對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要高[18],因此,本文依據GDP這種最直觀的方法來量化不同空間耕地生態補償的迫切程度。具體公式參考孟雅麗等[18]研究。
3 結果與分析
3.1 東北地區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根據東北地區2011—2018年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相關數據,選取玉米、水稻、大豆3種主要糧食作物計算東北三省單位耕地當量因子價值量。在此基礎上,結合不同生態功能的當量因子權重,測算出東北三省區2011—2018年單位耕地當量因子和生態服務價值如表1和圖2所示。

表1 東北三省區2011-2018年單位耕地當量因子價值量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測算

圖2 東北三省區2011-2018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量變化
由圖2和表1可知,東北地區各省份單位耕地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以吉林省最高,其耕地生態破壞程度相對其余兩省較低。但綜合考慮耕地面積、利用狀況和生態保護策略的實施成效,整體來看,各省份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量差距較大,呈現由東向西遞減的特點,以黑龍江省最高,吉林省次之,遼寧省最低。2011—2018年,三省區的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趨勢大體相同,處于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階段,2018年分別達到1.80×1011,8.60×1010,5.70×1010元。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建立耕地生態保護機制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采取一系列耕地環境修復和污染控制措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所提高,2016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下降主要由于當年東北地區的糧食作物產值較低,導致單位當量因子價值量下降,而后中央政府在東北地區加大專項資金投入,擴大黑土地保護試點工作,耕地環境的修復逐漸見效,且隨著試點面積和保護性耕作的不斷推廣以及相應政策的密集發布,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又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
3.2 東北地區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自身消費的生態服務價值
對于農村水足跡的核算從農業、居民生活、工業及生態環境4個方面。其中,農業用水量最大,約占80%,各類食物或產品中存在大量的虛擬水,采用單位產品虛擬水含量與各類食物或產品消費量的乘積作為農業虛擬水量[19],再按照地區農業用水總量與農村居民、城鎮居民的加權比例計算;工業用水量本身較少,且農村的工業企業少,規模也小,從實際耗水量來看予以忽略不計;居民生活用水按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單位標準計算;生態用水及水資源可利用量按總用水量的農村人口比例計算。根據公式(1)可求得東北地區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自身消費的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見表2。

表2 東北三省區2011-2018年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的自身消費情況
東北地區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的自身消費系數約在20%~40%之間,說明絕大部分的耕地生態社會效益未能轉化為經濟價值為經營者自身所用。省際間差異較大,2018年黑龍江省、吉林省和遼寧省的消費系數分別為0.33,0.23,0.49,對應消費的生態服務非市場價值分別為5.00×1010,1.66×1010,2.21×1010元,這主要由東北地區水資源的供需不平衡導致的,黑龍江省為農業大省,水資源消耗量約為另外兩省份的3倍,農業用水量占比近90%,且水資源可利用量也較為豐富,約為吉林省的2倍、遼寧省的5倍;遼寧省的農村水資源消耗量較低,地理環境原因農村水資源的可利用量更低,說明農村自身消耗耕地生態服務價值的比重較大;吉林省的消費系數最低,說明耕地供給的生態服務價值約有77%被城鎮居民所無償消費。在時間上來看,剔除2013年的水資源供給量突然增多的特殊情況(2013年,東北地區洪澇、臺風災害頻發重發,黑龍江、嫩江、松花江發生流域性大洪水,其中黑龍江下游洪水超百年一遇),東北地區各省份耕地供給者自身消費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趨勢與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變化趨勢基本相同,這說明耕地利用者為了自身經濟收益加大對耕地的利用,而后在政策號召下又實施了一定的保護措施。
3.3 東北地區生態補償標準
依照第二部分理論依據的分析,東北地區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應為耕地生態服務供給主體在剔除自身消費后,還可向其他地區提供的剩余耕地生態服務的非市場價值部分。再結合各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服務外溢地區居民的支付能力,根據上述公式(2)—(4)計算可以得出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見表3。由于各年份經濟發展水平和支付能力差距,2011—2018年東北地區補償標準總額波動較為頻繁,近幾年相對較低,2018年相比最高年份相差35%以上。說明耕地帶來的生態外部效益下降較大,為了保證耕地供給者有足夠能力進行耕地生態環境保護,實現整個社會空間的生態社會效益最大化,從公平和效率角度出發,應當對其供給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給予足夠的補償。

表3 東北三省區2011-2018年耕地生態補償標準C
3.4 東北地區生態補償優先級
考慮到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依照GDP來量化2018年東北三省區的補償迫切程度,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單位面積的生產總值分別為40 529.1,80 440.9,171 050元/hm2,對應的生態補償優先級為0.234,0.127,0.064。黑龍江省的生態補償優先級遠高于吉林省和遼寧省,這一方面是由于黑龍江省的耕地生態保護行動對于提高耕地生態功能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還遠遠不夠,另一方面黑龍江省域面積較大且經濟發展處于相對落后狀態;吉林省處于中等水平,其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經濟發展水平均較高;遼寧省最低,主要在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高而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較低。因此,應當率先向生態補償優先級高的黑龍江省支付耕地生態補償。
4 討論與結論
本文以耕地外部效應和生態系統服務理論為基礎,引入基于公平角度和支付能力的生態補償模型,量化東北地區耕地生態補償額度。首先,利用當量因子法測算了三省區2011—2018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變化,發現單位耕地生態服務價值量以吉林省最高,由于耕地數量、利用狀況和保護策略的差異,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總量由高到低依次為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且三省份的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隨時間變化均出現先“上升—下降—上升”的趨勢。其次,構建評估耕地生態服務供給者自身消費的水足跡模型,發現除極端水資源供給量突增外,三省區耕地經營者自身消費的生態服務價值約在20%~40%之間,說明絕大部分的生態服務功能被無償消費,要積極探索各種補償方式,使城鎮居民等有相應的支付平臺為自身消費的生態功能買單。最后,在剔除耕地經營者自身消費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結合不同地區支付能力后得到三省份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2018年的額度分別為5.73×1010,3.13×1010,1.33×1010元,相較之前年份有所降低,進一步考慮各省份的經濟發展,確定生態補償優先級由高到低分別為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說明黑龍江省相對提供了更多的生態服務,經濟發展較為落后,要健全跨區域、跨產業協作的耕地生態補償機制,率先向其支付耕地生態補償。
相比于洋等[20]、張猛等[21]將求得的非市場價值部分作為吉林省和遼寧省的耕地生態補償標準,本文剔除了耕地經營者的自身消費和能夠通過市場交易彌補的市場價值部分,測算結果偏低,也更加公平,且通過支付能力和補償系數的修訂,更具有實際操作性。但前人研究中提到耕地生態補償的內容包括治理生態負外部性和獎勵生態正外部性兩方面,本文仍然是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的基礎上測算,未能對東北地區耕地資源的稀缺程度進行深入分析,且未考慮到提供同一種生態服務功能的旱田和水田所付出的成本差異,今后可在此基礎上探索構建一個“保護成本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一致”的補償標準模型,將耕地的投入產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對東北地區耕地資源的稀缺程度、均衡匹配性以及不同類型耕地的保護成本等方面做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