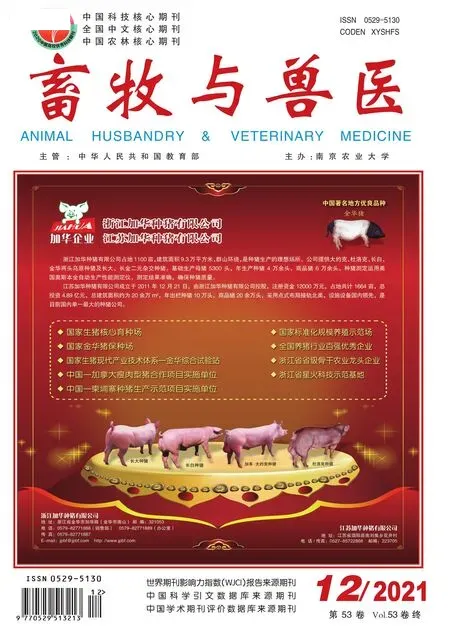動物機體對高原低氧環境適應性的研究進展
趙禹,張文才,劉成武,楊敏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警犬技術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低壓低氧、低溫和強紫外輻射是高原地區顯著的氣候特征,而低壓低氧是影響動物在高原地區生存最重要的氣候因素[1-2]。動物機體對高原環境適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動物細胞分子、生理生化、組織器官、神經內分泌各個層面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調動響應。高原土著動物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與進化,在動物外形、組織器官形態結構和生理生化調節上獲得了穩定的適應高原環境的遺傳學特征。而居住在平原環境下的動物從低海拔常氧地區進入高海拔低氧環境,機體也會發生一系列的代償適應性變化來適應高原低氧環境。一些動物能夠通過機體代償獲得對高原環境的良好習服,一些動物機體代償適應性反應不足或過于強烈發生習服不良,會出現高原反應。本文從外觀及生長發育特點、組織器官形態結構、血液生理生化水平、細胞分子水平、動物腸道菌群、維生素及氨基酸、抗高原反應藥物7個方面論述了動物機體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1 外觀及生長發育特點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高原土著動物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進化,動物外形與平原地區生活的動物相比,皮毛較長且濃密,多為黑色或褐色[3]。
在高原環境對動物生長發育影響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認為體重和體尺的減小可能是動物對高海拔環境的適應之一[4]。張浩等[5]在研究海拔環境對雞生長發育影響中發現,藏雞(高原土著品種)和矮小隱性白肉雞(平原地區品種)高海拔時的絕對生長速度和相對生長速度均比低海拔時低。高海拔生態環境會抑制雞的生長速度,從而改變生長模式。在高原環境對人類生長發育影響的研究中,席煥久等[6]分析了海拔、年降水量、年均氣溫和年日照四種自然環境因素對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指標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隨著海拔升高,兒童青少年的生長發育指標逐步下降,得出的結論是海拔對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的影響最大。Weinstein[7]研究對比了古安第斯高原人類與低海拔地區人類骨骼結構。結果表明古安第斯高原人類的體型較小,肋骨粗大,得出高原低氧環境的自然選擇塑造了古安第斯高原人類的骨骼形態的結論。筆者所在研究團隊在對云貴高原地區馬里努阿犬(已在當地環境繁殖馴化20余年)與平原地區馬里努阿犬生長發育特點研究中也發現,云貴高原地區馬里努阿犬體型有減小的趨勢。
2 組織器官形態結構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高原土著動物經過長期高原環境的自然選擇,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組織器官的形態結構進化出適應高原低氧環境生存的特點。賈榮莉[8]研究了高原地區藏羊和平原地區小尾寒羊肺組織形態學的差異。結果表明,藏羊單位面積的肺泡數量多,肺泡小,肺泡隔厚,肺泡隔中毛細血管的充盈程度高。張晨[9]研究表明,藏羊心肺較小尾寒羊產生了適應高原環境的結構變化。如較厚的心肌壁、更大的心腔面積和粗長的心肌纖維等;肺臟則出現末端支氣管分級豐富、發達的支氣管杯狀細胞以及更厚的支氣管平滑肌等現象。許永華等[10]在藏豬心臟、呼吸系統組織學觀察中發現,藏豬心臟壁和心外膜厚,心內膜附近浦肯野纖維粗,組織中束細胞明顯;同時,心肌纖維排列規則且粗大,肌間血管豐富。呼吸系統中,鼻黏膜較厚,氣管和支氣管纖毛排列緊密、粗而長;肺泡壁和肺間質毛細血管較豐富,并呈現擴張狀態。 周大鵬等[11]在對藏獒肺組織觀察中發現,藏獒的肺胸膜較厚,膠原纖維和彈性纖維含量豐富;肺呼吸部肺泡管寬大且數量多,形成許多高低不平的皺褶,相鄰肺泡間的肺泡隔內有著豐富的毛細血管和大量的紅細胞。陳秋生等[12]在對牦牛肺臟高原適應性的結構研究中發現,牦牛肺臟結構具有特異性。 具體表現為牦牛的肺小葉結構明顯,肺泡I型上皮薄,小葉間隔、肺泡隔和各級支氣管管壁等結構內含有豐富的彈性纖維,可維持肺良好的伸縮狀態。另外,肺毛細血管末端的氣-血屏障的平均厚度較薄,有利于氣體交換。Zhang等[13]研究結果表明,藏雞的肺臟器官中肺泡體積小,總肺泡面積大,單位面積內肺泡數目和毛細血管多,并且肺泡隔厚。李雙等[14]研究了高原鼠兔低氧性肺血管收縮反應鈍化(bHPV)的組織學基礎,研究結果表明,導致高原鼠兔bHPV發生的組織學基礎可能是其肺組織中直徑10~50 μm微血管平滑肌細胞數量少。
當平原動物進后入高原,平原動物一般在整體水平上進行代償調節以適應高原低氧環境。如加快呼吸頻率,增加肺通氣量,加速肺泡—血液—組織的氣體彌散,加強毛細血管持久性,加強心泵功能,代償性心肌肥厚等,這些反應會增加動物機體組織供氧量。有些動物由于低壓低氧的刺激,會引起肺動脈壓力升高。長期的肺動脈高壓導致右心肥厚,發生高原性心臟病等疾病。所以,動物對高原低氧的適應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高原環境中是否會出現肺動脈高壓及出現肺動脈高壓的程度。Tucker等[15]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哺乳動物對低氧引起的肺動脈高壓反應差異顯著;試驗比較了牛、綿羊、犬、豬、兔、大鼠和豚鼠7種動物,牛和豬對低氧最敏感,大鼠和兔對低氧中度敏感動物,綿羊、豚鼠和犬對低氧輕度敏感,其中犬最不敏感;試驗證明,造成動物對低氧敏感的種間差異的主要決定因素是肺血管平滑肌數量。平滑肌數量越多,對低氧越敏感,越容易造成動物肺動脈高壓。而賈寧等[16]研究結果表明,藏獒的肺小動脈平滑肌數量相對較多,這與Tucker等[15]的結論并不一致,需要進一步研究論證。
3 血液生理生化指標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血液生理生化水平是反映動物機體生理機能的重要指標。受高原低氧環境刺激,高原地區的土著動物和平原動物,血液生理生化水平都會隨著海拔高度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尤其是與氧氣運輸、利用密切相關的一些指標,如:紅細胞數量(RBC)、血紅蛋白濃度(HGB)等。
一些研究者針對不同海拔同一品種的動物血液生理生化指標變化開展了研究。王志敏等[17]研究了不同海拔高度對藏雞血液生理生化指標的影響,發現藏雞紅細胞數量、血液中血紅蛋白濃度及平均紅細胞體積(MCV)呈現出隨海拔高度升高而升高的趨勢。雷蕾等[18]對比了不同海拔地區牦牛血液生化指標差異,結果顯示,較高海拔地區牦牛血液生化指標中谷丙轉氨酶(ALT)、乳酸脫氫酶(LDH)、葡萄糖(GLU)等水平極顯著升高。兩個不同海拔地區的牦牛心肌酶活性、機體代謝功能及抗氧化能力存在一定差異。張春梅等[19]比較了3 200 m和1 500 m海拔的湖羊血液生理生化水平變化,結果表明,高海拔地區湖羊血液紅細胞數量、血紅蛋白濃度、紅細胞壓積、平均紅細胞體積顯著高于中海拔地區湖羊。蔣世海等[20]比較了不同海拔的白薩福克羊血液生理生化指標,結果表明,高海拔地區白薩福克羊的紅細胞數量和紅細胞比容等指標極顯著高于低海拔地區白薩福克羊。
有些研究者針對不同海拔同一種屬動物生理生化指標進行了比較。孔小艷等[21]比較了4個連續海拔分布豬種如藏豬(海拔3 700 m左右)、大河豬(海拔2 300 m左右)、明光小耳豬(海拔1 900 m左右)和滇南小耳豬(海拔550 m左右)血液生理指標,發現藏豬紅細胞、血紅蛋白和紅細胞壓積3個指標遠高于明光小耳豬和滇南小耳豬,說明與氧氣運輸相關血液生理指標隨海拔升高而升高,血紅蛋白濃度高是藏豬低氧適應的生理表征。趙雪等[22]檢測了4個連續海拔梯度上分布的德宏馬、昭通馬、麗江馬、藏馬,比較它們的氧氣結合與運輸相關血液生理指標、血液黏稠度。結果顯示,高海拔地區馬的血紅蛋白濃度、紅細胞壓積和體積、紅細胞血紅蛋白(MCH)和紅細胞平均血紅蛋白含量(MCMH)都極顯著高于低海拔地區。郭曉宇等[23]比較了來自高原的蕨麻小型豬與來自平原的巴馬小型豬的血液生理生化指標,發現高原蕨麻小型豬的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紅細胞壓積、紅細胞血紅蛋白、紅細胞平均血紅蛋白含量均極顯著高于巴馬小型豬;血液生化指標中高原蕨麻小型豬γ-谷氨酰基轉移酶(GGT)、葡萄糖、肌酐(CRE)均極顯著高于巴馬小型豬。
還有些研究者對相同海拔同一種屬動物生理生化指標進行了比較。徐躍進等[24]對高原環境下的藏豬和大約克豬血液生理生化指標進行了比較,發現藏豬的紅細胞、血小板數量(PLT)和血小板壓積(PCT)指標顯著低于同海拔的大約克豬。筆者認為,在同樣高海拔環境下,開展同一種屬動物生理生化指標比較研究,更有利于研究揭示高原土著動物的高原環境適應性進化機制,也更有利于選育適宜高原環境的動物新品系。
4 細胞分子水平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動物細胞分子水平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響應最主要是對低氧的響應。低氧適應相關基因是一類能夠接受低氧信號調節并參與低氧適應性反應的基因群,是低氧適應機制極為重要的分子基礎。研究發現,參與調控低氧適應性的大部分基因都集中在低氧誘導因子(HIF)通路,主要參與調控機體的RBC生成、血管舒縮、應激反應、糖代謝等生理過程[25]。HIF通路總共含有200多個相關基因,其中EPAS1和EGLN1基因最為關鍵。EPAS1與低氧誘導的正性調節有關,是慢性缺氧相關基因的關鍵調節因素,主要參與促紅細胞生成素(EPO)、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相關基因的上游調節;EGLN1作用剛好相反,它主要與正常氧分壓下HIF-1ɑ和EPAS1蛋白的降解有關;在缺氧時,EGLN1基因的改變導致降解能力下降,間接提高了EPAS1蛋白的表達水平,增加了與低氧調控有關物質的產量[26]。短期對高原環境的習服往往表現為較高的呼吸頻率與血紅蛋白濃度提升,機體通過增強無氧糖酵解能力緩解低氧低溫能量代謝壓力;而機體對高原環境長期適應性演化則通過基因型變化,增強氧氣運輸與有氧代謝能力,以應對長期低氧高海拔環境[27]。
近年來,研究者開展了藏雞、藏豬、牦牛、藏羊、藏馬和藏獒等多種高原土著動物基因組、轉錄組和蛋白質組層面的工作,挖掘到一系列高原土著動物環境適應性的關鍵候選基因[3]。與心血管系統有關的基因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EGF)、肌球蛋白輕鏈激酶(MLCK)等;與低氧應答反應有關的基因如:內皮PAS蛋白1(EPAS1)、缺氧誘導因子α(HIF-1ɑ)、一氧化氮合酶1(NOS1)、血紅蛋白β亞基(HBB)等。
近年來,研究者從表觀遺傳學層面開展動物或人類高原環境適應機制的探索。金龍[28]探索了藏豬高原適應性的表觀遺傳機制。首次構建了藏豬背最長肌的全基因組單堿基分辨率DNA甲基化圖譜。結果顯示,藏豬基因組中主要的甲基化位點為CpG二核苷酸,少量DNA甲基化發生在CHG和CHH序列環境下。平原藏豬與高原藏豬背最長肌之間的差異甲基化基因主要富集于代謝、轉運、氧化磷酸化等各種生物學過程,以及ATP結合、核苷酸合成、轉運酶等分子功能。這些通路與能量的代謝極其相關,該結果從基因甲基化層面印證了藏豬高原適應的獨特能量代謝過程。Childebayeva等[29]以不同海拔健康成年人唾液樣本為研究對象,研究了LINE-1, EPAS1, EPO, PPARa, 和RXRa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研究結果表明,逐漸暴露于缺氧環境會影響表觀基因組,表觀基因組的變化可能是高原適應過程的基礎。
也有研究者探究了小RNA在動物高海拔適應性中的作用。龍科任[30]研究繪制了雞、牛、羊和豬4種動物較為全面的miRNA表達譜,并分析了4個物種miRNA的進化情況。各個物種均鑒定出了大量參與血管生成、細胞凋亡等生物學過程的高海拔適應性相關的miRNA。Feng等[31]研究了高原應激對山羊miRNA表達的影響。對不同海拔高度(600 m和3 000 m)山羊群體的6種缺氧敏感組織(心、腎、肝、肺、骨骼肌和脾臟)進行了miRNA轉錄組比較分析。獲得了1 391個成熟的miRNAs,并鑒定了138個高海拔和低海拔地區差異表達的miRNA。揭示了miRNA不同海拔高度和不同組織間表達水平的變化,發現低氧習服存在著組織特異性和保守的機制。
熱休克蛋白是機體對應激反應產生的物質,熱休克反應中Hsp70的快速合成有利于維持應激時細胞的正常生理功能, 能促進機體對高海拔應激的適應。王曉臨等[32]選擇牦牛和家兔為試驗動物,用Hsp70探討哺乳動物對高海拔(缺氧)適應能力。結果表明高原土著哺乳動物和低海拔哺乳動物都具有熱休克反應的基因,Hsp70可被高海拔(缺氧)誘導產生,Hsp70的表達存在著閾值,海拔5 000 m是熱休克反應最佳的條件,超過海拔6 000 m時熱休克反應減弱; Hsp70生成量與細胞的耐缺氧能力成正比。李芳澤等[33]研究了人類Hsp70-1和Hsp70-2基因多態性與急性高原反應的關系。證明了攜帶Hsp70-2B/B基因型的機體應激能力較弱,易發生急性高原反應。
5 腸道菌群調控動物機體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動物腸道微生態菌群在宿主營養攝入、生長發育和疾病免疫等功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研究發現,動物腸道菌群不僅本身受高原環境的影響,還作為重要的調控因子調節動物機體對高原環境的適應及習服。
Zhang等[34]在研究高原土著動物牦牛和藏羊瘤胃微生物群落趨同進化中發現,這兩種高原反芻動物瘤胃甲烷含量顯著低于低海拔普通牛和羊,而揮發性脂肪酸(VFA)產量卻顯著高于低海拔普通牛和羊。高原土著動物腸道菌群中的如普氏菌屬等相關菌群種類和豐度顯著增加,能夠促進VFA生成,也能更好的利用VFA生成乙酸、丙酸等小分子代謝物為機體提供能量,能量利用更高效。通過瘤胃宏基因組測序,揭示了高原動物瘤胃內VFA形成通路基因富集,而平原動物甲烷形成通路基因富集;通過胃黏膜轉錄組研究揭示了牦牛VFA運輸和吸收基因顯著上調,這預示宿主和腸道微生物間可能存在協同進化。MA等[35]使用16SrRNA基因測序的方法,研究了3種高海拔(4 300 m)高原土著食草動物藏羚羊、藏野驢和藏綿羊腸道微生物群落組成及與低海拔藏綿羊(3 000 m)和普通綿羊(1 800 m)腸道微生物群落組成的區別。結果表明,瘤胃球菌屬 (Ruminococcus)、振蕩桿菌屬(Oscillospira)和梭狀芽胞桿菌屬(Clostridium)是3種高海拔高原土著動物共同的優勢菌群。藏羚羊(4 300 m)腸道微生物群中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梭菌目(Clostridiales)、梭狀芽孢桿菌屬(Clostridia)、厚壁菌門(Firmicutes)富集程度比低海拔的藏綿羊(3 000 m)和普通綿羊(1 800 m)更高;同時厚壁菌門(Firmicutes)與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的比值也更高。高海拔的藏羚羊和藏綿羊(4 300 m)腸道微生物群宏基因組功能注釋顯示超過80%的基因對代謝和遺傳信息加工途徑起作用。高海拔草食動物的腸道微生物組成相似,可以從食物中獲得更多的能量,腸道菌群自身合成的各種酶和代謝產物、分解宿主腸道物質所生成的各種小分子物質,均有可能通過各種信號通路影響機體對高原環境的反應程度[36]。研究高海拔高原土著動物胃腸道微生物菌群組成及參與高原土著動物對高海拔環境適應的機制對于制備適宜高原環境生活的動物胃腸道微生態制劑及高原地區引種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6 維生素及氨基酸調控動物機體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研究發現,某些種類的維生素具有改善機體低氧狀態下的物質代謝、減輕高原反應的作用[37]。陳東升等[38]在觀察大鼠在不同模擬高度微量營養素狀態的變化中發現,隨海拔高度上升,大鼠血清維生素C和維生素E有下降趨勢。說明低氧狀態下大鼠體內維生素C和維生素E的消耗量增加了。Goswami等[39-40]研究結果表明,補充合適劑量的維生素C和維生素E可阻止雄性大鼠由于高海拔低氧引起的免疫變化。白霜等[41]在綜述維生素影響人類高原習服的研究進展中得出:大劑量補充某些種類的維生素具有促進高原習服的作用,但作用機制尚不明確。
黃文等[42]研究了兩種含有氨基酸和維生素的復合制劑對高原官兵疲勞的預防和快速恢復作用,結果表明:氨基酸維生素制劑能明顯提升高原官兵軍事作業能力,有效對抗疲勞引起的彈跳力和握力下降,從而發揮預防和快速恢復疲勞的作用。王書祥[43]研究結果表明,給引入高原地區的荷斯坦奶牛飼喂含有N-氨甲酰谷氨酸的飼料,可以顯著降低高原地區荷斯坦奶牛肺動脈高壓的發病率,降低低氧對奶牛心血管系統造成的損傷。
開展維生素及氨基酸對動物機體適應習服高原環境中的作用及相關機制的研究,對于促進低海拔動物高原習服,預防或減輕高原反應具有重要意義,也為高原土著動物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7 抗高原反應藥物促進動物機體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
抗高原反應藥物一般分為化學合成類和中藥類。中藥由于效果好,不良反應小,在預防和治療高原反應中應用較為普遍。目前發現的具有潛在抗缺氧損傷的中藥有:紅景天、胡黃連、靈芝、黃芪、枸杞、黃芩等[44]。目前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對藥效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者開展了中藥在動物機體抗高原反應機理的研究。李文華等[45]研究發現,藏藥紅景天可提高對大鼠肺組織HIF-1a mRNA表達,有利于減輕大鼠低氧性高原肺水腫。李云虹[46]研究發現,西藏蕪菁塊莖提取物中的正丁醇相是其抗缺氧的有效活性部位,對香豆酸及其葡萄糖苷為主要功效成分之一。對香豆酸預防缺氧性腦水腫的主要作用機制涉及HIF-lα、VEGF、ET-1和AQP4 mRNA水平及蛋白表達的降低,進而降低了腦組織屏障通透性,緩解了缺氧造成的星形膠質細胞水腫,達到預防小鼠缺氧性腦水腫的作用。
8 結語
高原土著動物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從外觀、組織器官結構、生理生化水平到與高原低氧環境相適應的基因型,都發生了穩定的遺傳。而低海拔動物移居高原后會調動機體應對高原低氧應激發生反應。高原低氧環境會刺激動物機體呼吸心率等生理指標發生變化,并引起神經內分泌、組織器官結構、生理生化水平、細胞分子水平一系列的應答反應。目前,對于高原土著動物高海拔低氧適應性在生理結構特點、高原耐低氧候選基因挖掘、耐低氧的表觀遺傳學特點、胃腸微生物菌群特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進展,對低海拔動物高原低氧習服或引發的高原反應的生理特征及分子機理也有較深入的研究,但仍未系統性揭示高原土著動物對于高原低氧環境適應性的分子機制,高原地區引種及育種工作進展也較緩慢。結合低海拔動物移居高原后的機體應答機制研究發掘高原土著動物適應高原低氧環境的本質,利用現代基因組學技術,揭示高原土著動物對于高原低氧環境適應性的基因調控網絡,探究動物機體高原適應性的表觀遺傳機制,研究高海拔高原土著動物胃腸微生物群落參與宿主適應高原環境的作用機制,研究維生素、氨基酸及抗高原反應藥物促進動物高原環境適應性機制,可為高原地區引種及培育適應高原環境的動物新品種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