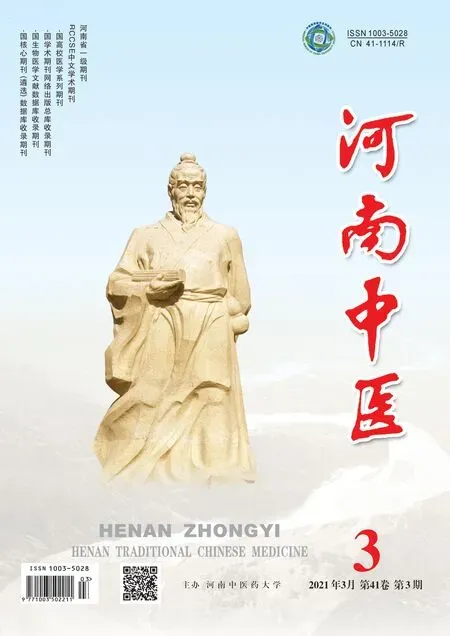《傷寒雜病論》消渴病機(jī)與辨治*
龍新勝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八十三集團(tuán)軍醫(yī)院,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0
許慎《說文解字》言消:“從水,指水將盡而未盡也;”渴:“水竭也。”消渴指的是缺水,水源不足;從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來講,它指的是一種以體液不足、自救飲水、多食易餓、身體消瘦為癥狀的疾病[1]。消渴病名始見于《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奇病論》載有口中發(fā)甜之病,取名“脾癉”,病機(jī)為過食膏粱厚味,損傷脾胃,脾失健運(yùn),不能輸布精微,反而釀濕生痰,則形體多肥壅,脂膏阻遏中焦氣機(jī),內(nèi)生濕熱,耗傷津液,而生消渴之疾[2]。消渴在《黃帝內(nèi)經(jīng)》中的病名有“消渴、消癉、脾癉、煩渴”等。癉,有“勞”之意,又有“體瘦弱”“內(nèi)生熱”之意。如王冰注《素問》:“癉,熱也,極熱為之也。”此處“癉”應(yīng)取“疾病”和“勞苦”之意。消癉中的“消”指消瘦,“癉”指內(nèi)熱和衰弱,消癉是指以身體衰弱為主癥的一類疾病,胃火盛是其核心病機(jī)。消渴之“消”當(dāng)為消耗之義,其病機(jī)為津液不足、陰虛火旺,“渴”指口干,因津液被消耗而干渴。脾癉為消渴的前一階段,均屬于“虛損”范疇。《難經(jīng)》云:“治損之法奈何?損其脾者,調(diào)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提出了虛損病的治療法則。
1 病因病機(jī)
1.1 消渴源自正氣虛《黃帝內(nèi)經(jīng)》認(rèn)為,百病皆生于氣,氣虛是消渴發(fā)生的內(nèi)在基礎(chǔ)。中醫(yī)認(rèn)為:“正氣存內(nèi),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消渴是勞逸失度,氣血不調(diào),正氣不足,臟腑元真不暢,津液輸布障礙所致的津液代謝性疾病。《靈樞·五變》言:“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先天稟賦不足,后天脾胃失調(diào),失于濡養(yǎng),氣血不足,是消渴發(fā)生的根本病機(j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