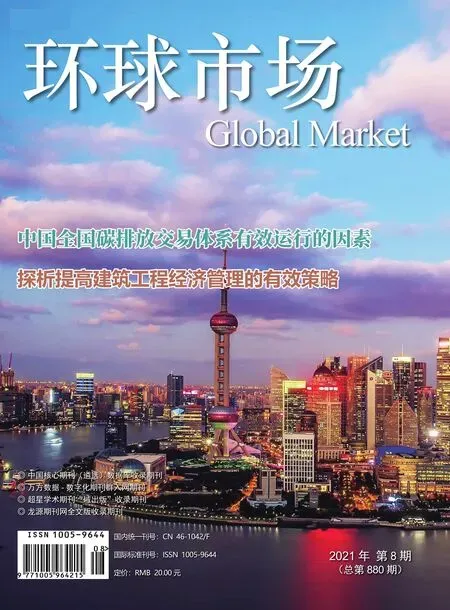地方政府財政環保支出競爭的演化博弈
陳業中 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
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的問題比較突出。在世界能源統計年鑒中,我國已經是全世界范圍內全球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和能源消費量最大的國家,是全球的平均水平的2.3 倍。為更好地解決環境問題,我國地方政府應當增加財政環保支出[1]。但是出現了一個典型問題,那就是地方官員晉升和當地的經濟產生密切聯系,官員為晉升,提升政治地位,則出現“為增長而競爭”的問題。這種問題會引發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地方財政支出側重基礎設施建設,而忽視環保方面的支出,環境治理不如經濟增長重要[2]。
一、地方政府財政環保支出研究的方向
當前,學術界已經在地方政府的環保行為方面開展了非常多的研究,可是有三個方面需要進行深入探討。其一,地方政府財政在環保方面的支出,有助于環境質量提升,還是強化了環境環境污染,這個問題一直沒能得到解決。其二,一些學者關注到地方政府對于財政環保的支出有競爭,而處在國家非常重視生態文明的建設中,以及強調環保問責的時候,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環保支出的競爭形式有什么樣的變化。其三,運用演化博弈的理論進行分析,當下研究中更側重污染協同治理以及環境規則執行的方向,去分析政府行為,很少聚焦地方政府的財政環保的支出競爭的演化博弈。
基于此,下面內容重點就演化博弈進行分析,著手于地方政府的財政環保的支出競爭具體行為,設定中央政府所使用的約束機制指標,包括環保績效考核、環境問責,從而構建出相應的支出競爭的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期望收益以及穩定策略,從而更深度地解析地方政府的環保支出競爭的博弈行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財政環保的支出競爭會影響到區域環境質量哪些方面,從而不斷豐富已經存在的問題,以提高研究的現實意義。

表1 兩個政府間的收益矩陣
二、基本假設與模型構建
(一)基本假設
假設一:地方政府會運用吸引社會環保資金、提高財政環保支出的方式,開展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以改善環境的質量。
假設二:因為環境污染具有一定跨區域性和流動性,所以,地方政府之間以財政的環保支出開展環境治理工作所產生的影響有著“部分排他性”和“同向外部性”的特點。
假設三:博弈雙方的地方政府分別是A與B(以下簡稱A、B),均設定成有限理性人,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設四:A 在縮減了財政環保支出時,管轄區域內的污染的排放增加量是P1;A在污染方面的治理成本是C1;A 在提高財政環保支出時,管轄區域內的污染的排放減少量是H1。B 在縮減了財政環保支出時,管轄區域內的污染的排放增加量是P2;A在污染方面的治理成本是C2;B 在提高財政環保支出時,管轄區域內的污染的排放減少量是H2。A 對應的B 的污染治理或者污染增加外部效應的系數為δ1;B 對應的A的污染治理或者污染增加外部效應的系數為δ2;A 選取“增加財政環保支出”策略的比例是x,B 選取“增加財政環保支出”策略的比例是y。
假設五:在博弈模型中,將環境績效考核以及環境問責設定成中央約束機制。A 提高環保支出,B 縮減環保支出,B 接受的中央政府環境問責是F;B 提高環保支出,A縮減環保支出,A 接受的中央政府環境問責是F。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包括環境質量評價,如果λ 是環境評價占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權重系數,λ 大表示所占比重則越大。
(二)構建模型
基于地方政府之間會受“部分排他性”和“同步外部性”的影響,所以博弈雙方選取策略不同時,收益也不同,最終兩個政府間的收益矩陣為表1。
三、演化博弈的分析結果
在博弈主體有限理性為基礎的前提下,采納中央政府的約束機制,建立了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環保支出的競爭演化博弈模型,以此研究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環保支出競爭的行為、主要影響因素,得出以下幾方面的結論:
(1)不同的地方政府會有財政環保支出的競爭行為。治理環境污染的時候,地方政府在財政環保的支出競爭中,主要影響因素包含幾個方面,分別是外部效應、污染的排放量、環境治理效果、治理成本、中央政府環境問責、環保績效考核。受以上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財政環保支出方面,一定是動態化地選擇策略,不斷調整策略,環保支出的競爭總是存在。
(2)基于中央政府約束機制,以不受到環境問責,達到環保績效考核的標準為目的,地方政府在財政環保支出方面的競爭表現為“逐頂競爭”。因為中國傳統政治競爭機制、財政分權體制,誘發了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如果地方政府為獲取短期經濟效益增長,則會選擇忽略生態保護及環境治理,現存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政府之間的環境規制是“逐底競爭”,可對此結論給予支持的競爭動機,也就是傳統GDP 政績觀,逐漸在改變。在環境問責制度廣泛應用、環保績效評價體系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必須平衡好經濟效益和環境治理間的關系。就地方政府來說,環境保護不能同其他公共物品一樣被忽視。受到中央政府約束機制壓力的影響,地方政府必須重視環境保護與治理,因此,地方政府在財政環保支出的競爭中,策略變成了“逐頂競爭”。
(3)當環保支出的競爭策略是“逐頂競爭”時,有利于改善本區域內環境質量。考量環境污染具有跨區域性和流動性,還有不同地方政府的環境污染治理有著“部分排他性”及“同向外不性”特點,如果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環境治理,則一定會強化財政環保支出“逐頂競爭”的策略,這樣的優點分成兩方面,一方面能改善區域內環境質量,另一方面會加強環境污染的協同治理,最終初始整體環境的改善。
四、政策建議
(一)增加地方收入以提高環保支出
想要讓環境污染降低,需要一定財政環保的支出,而想要讓地方政府高質量開展環境治理工作,就需要增加本地區的地方收入,健全地方的稅收體系,拓展節能環保的財政資源來源渠道。第一點,清晰規定出環保稅中應稅污染物的適用范圍,征收范圍中包括灘涂、草場、森林等自然資源,從而健全地方稅系。第二點,當下,國內的稅收征管權利和立法權力均由中央掌握,地方并不能依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權宜,所以,可以在不違背國家的主稅法基礎上,給予地方政府部分稅收的管理權[3]。第三點,將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完善,促使轉移支付的結構更加優化,縮減專項的轉移支付比例,增加一般性的轉移支付比例,提高地方政府在統籌應用資金方面的能力,努力建立區域間的生態補償制度,使得區域之間的生態環境補償系統更健全,將補償的標準、對象、方式、范圍明確出來,建立一種生態補償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二)構建環保考核和問責機制
地方政府對于環保支出進行“逐頂競爭”,其主要的動力就是中央政府的環保考核問責機制,如果想要達成綠色發展目標,一定要保證環保考核問責制的長效化及常態化。中央開展的環保監督,在提高環境質量發揮著積極作用,可是環保監督僅僅是中央政府使用強制力促進運動的治理模式,當下的《中央環保督察方案(試行)》僅僅是行動方案,應當把督察方案提升成有著法律約束力的督察條例,進而能促使環保督察長久有效,利用法律的力量,強調地方政府強化環保支出,提高環境治理的力度。除此之外,就公眾監督機制進行完善,不斷提升考核透明公開度。當下,用于地方政府環保考核的綠色考核有著量化指標,可是從經驗以及教訓中發現,所用的量化考核的指標隱藏“數字游戲”的風險,所以必須強化環保信息的公開,加快關于環境信息方面的決策和執行自己結果的公開,群眾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得到尊重,在考核范圍中,需要納入公眾以及環保組織給出的意見,進而促使地方政府關注環保支出投入,提升生態環境的質量。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利用演化博弈理論為基點,著手于地方政府的財政環保的支出競爭具體行為的分析,設定中央政府所使用的約束機制指標,包括環保績效考核、環境問責,從而構建出相應的支出競爭的博弈模型。分析出地方政府對于環保支出進行“逐頂競爭”,其主要的動力就是中央政府的環保考核問責機制;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地方政府的財政環保支出保持著負相關;地方政府提高環保支出,提高污染治理力度,這些同外部效應系數表現為負相關。